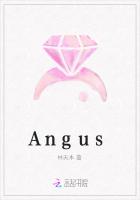我们航行了几乎整整三天,整个白天航行,夜里找村庄休息,一切都很顺利。不能加速,我们慢慢航行,发动机也工作得很好。还没有看到主河道,不过见到的船开始慢慢变多了,也有更多快速的现代船经过,我知道我们离主河道越来越近了。有几次,我们身边经过高速船,留下的噪音几乎是在水面上滚动,浪和水花溅到我的身上。在第二个河汊,我们甚至遇到了满满一艘小游船的美国游客,我们的独木舟和游船并排航行了十几分钟,在转弯的时候,一个穿粉红色花布长裙少妇和一个中年男人站在船舷边低头看着我们。
少妇小声说,“看,三个树林里的土人,开着木船,不过长的好奇怪。”
中年男人拿出他的眼镜,戴上说,“书上说巴西是个多民族国家,有些丛林里的土著和亚洲人很像,有些更像葡萄牙和印第安人的混合,有些则是欧洲移民的后代。”
我抬头对他们笑笑,亚洲血统的丛林土著在香草海中学学过英文,笑的时候有着一张咧开的大嘴。
少妇,中年人和他们的高速船超过了我们,我看到少妇跑到船的后面对着我们举起了相机,相机的镜头反射着阳光。
“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皮肤颜色,几乎已经晒的成快要和我一样的深色。”罗比尼奥说。
“喔,是啊,我希望这黑色的皮肤永不褪去。”我回忆起我在上海时皮肤的苍白。
其实,已经在雨林里旅行了足够久,我开始意识到雨林和上海相同的地方:它们都难以想象的大,没有边际。在丛林里旅行,就像在上海的地铁里穿梭,外面的灯光和黑暗交错,永远也不会停下,那些快速一闪而过又被拉长模糊的灯光,变成了时间留在记忆中片段流逝的另一种形式,在这个快速移动时间空间的维度里,没有人知道城市的边缘在什么地方结束。
地铁,我对面坐着一个长发漂亮女孩子,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毛衣,低头看电话。
地铁出口,有个白色的自动饮料售货机。
人行道。
电梯,二十五层。
星期五早上我是第一个到办公室,依旧坐在会议室的大窗户前。
做清洁的阿姨正在擦公司会议室的桌子,那个桌子很长很大,开会的时候,老板坐在东边的顶端,员工坐在两边。每天清晨我一个人在公司的会议室,我就坐在老板的椅子上,那张椅子有柔软的羊皮靠背,转过身,背对着桌子,透过会议室的窗户里望着佛光普照下的马路商场商业楼麦当劳红灯黄灯绿灯车停车来车往。我再次转身,回头看看正在檫桌子的阿姨,她姓张,五十多岁,穿的总是很整洁,以前是上海闸北区一个购物中心的员工,失业后在这个商业楼的十八到二十五层做清洁。我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叫张姨。在过去的十四个月里,早上如果来得早,就会遇到她在办公室做清洁。除了对她说“早上好”,我不记得和她有过其它的任何交谈。她的名字是什么,有几个孩子,是儿子还是女儿,儿子女儿在哪里读书,从未想过自己是否有兴趣知道。严格地说,“从未想过”这个词和“完全没兴趣”其实并不等同,从未想过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想过,可能是没时间想,也可能是没机会想,也可能是没有想到过去想。总之,突然想到,对我,从未想过的事情很多,如果有人把它们都一一列出,里面大概会有我很感兴趣的事。
我看着张姨低头擦桌子,她擦得很认真,桌子擦得很干净,如果一个人可以每周五天都早起如此认真地做一件事,公司应该给她加工资。我扭头看了看着窗外的阳光。一天又要开始,八小时,然后又是地铁,公交车,太阳落下,回家,吃饭,出去走走,在某个地方喝点东西,回家看会儿电视,可能是篮球比赛,可能不是,睡觉,如果不是雨天,太阳会再次在昏睡中升起,新的一天又会开始。
“张姨”,我突然叫她。
她抬头看着我,有点惊讶,大概是第一次听我说“早上好”以外的词,也有可能是突然意识到我除了说“早上好”,也还会叫她的名字。准确地说,是张姨,不是她的名字。
她还是抬头看着我,“哦”,她说。
“你,”我停了六七秒,问,“你,有没有坐过牢?”
她看着我,眼睛慢慢睁大,带着震惊,就像我不是人类,是昨天夜里从浦东野生动物园中逃走的那只黑色大猩猩,穿上了偷来的白色衬衫,顺着城市中的钢筋混凝土和灰尘爬到这里。
我看着她,我觉得我的脸上毫无表情,我感觉不到我脸上的表情。
在某个时刻她开始说话,她说得很快,一下子说了很多,她对着我一直说,越说越快,她说的时候很生气的样子。我木然,其实我一句也没听懂她说了什么,我听不懂上海话。
其实我甚至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问她这个问题,和问陈定松一样,张姨可以是任何人,我只是想在此时此刻问这个问题,而她在此时此刻在这里。如果她此时此刻不在这里,我至少还有机会知道我是不是会拿这个问题问自己。
我看着张姨,她一直在对我说,说上海话,说得很快,说的很激动。上海闸北区1949年以后所有的罪恶在此时此刻集中在我身上。
楼下交通银行存款的利率在屏幕上飞快的变化。
那天下午,我离开了上海,坐车向西,然后又向北,经过铁路高速破旧的公路和加油站,经过城市县城彩色的乡镇和农村。在第二天的太阳升起之后,我到了河北高碑店镇。我看到高碑店镇车站外面停了一排外拉客的白色面包车,吵吵嚷嚷,几个四十几的大叔穿着黑棉衣正在尝试拉着每一个经过的人上他们的车。
“小伙子,你去哪?”那个大叔戴着个灰色的线帽,司机从车窗伸出脑袋回头盯着我,是个光头,赤裸裸的对着河北秋天清晨寒冷的风。
“这里有没有一个有很多桃花的村庄。”
“我们这每个村庄都有桃花,小伙子,现在过了桃花开的季。”
“那个村庄除了桃花,附近还有个小学,有个桥,旁边还有两条河流。”
“什么名字?你不知道村子的名字?”大叔摇摇头。
“不知道,只知道哪儿有小学,桥,两条河流。”我说。
“不知名字谁知道地,没听说过。”大叔说。
“薛家营那片?”那光头司机朝地上吐了口唾沫,说,“那附近有个小学,桥,两条河流和桃花,我在那念的书。是不是薛家营?”
我呆看着他,没点头也没摇头。
“上车,坐着,我带你去,一会开。”光头司机指了指车门。
我坐着车,穿过了北方开阔平原上的杨树林和柏树林,后来到了一条黄土路,那的路边有一个拥挤的集市,两边都是小摊,蒸出的糕点包子馒头冒着热气,老人牵着小孩子们,小孩子们拿着红色的冰糖葫芦,烤出的红薯炸出的油条,星期六早上黄土路挤得水泄不通。那戴着个灰色线帽的中年大叔打开车门跳下车喊,“乡亲们啦,给条路,麻烦给让条路,麻烦移一移,让条路哈,都牵好孩子诶,路窄,怕撞着。”
一只黑狗叼着一个还在冒热气的包子从人群中走过,经过车窗,抬头看了一眼车窗后司机的光头。
我在一片桃树林环绕的小村下了车,桃树都掉光了叶子,我顺着桃树林中的小路对着阳光往里走,桃树枝和屋子的影子躺在土路的两边。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问“嘿,你认不认识郑佛爷?”
那年轻人说,“谁是郑佛爷?这村里,没佛爷。”
我说“就是在安城念过书,念过大学的,和我们年龄差不多大,二十三岁,叫郑大斌的。”
他说“郑大斌,在安城念过书的,我知道,他小名叫世杰,我们这村里都叫小名。”
我再次看到郑佛爷的时候,他正坐在厅里坐着喝茶,北方乡村里的厅宽敞明亮,那厅里空空荡荡,只放了一张深褐色的大木桌子,桌子后面的墙上贴着一幅水墨山水画,两把大木椅子,一边一把,郑佛爷就坐在左边的椅子上,端着一个青色的花瓷茶杯。阳光从南到北穿过他屋子的厅。
这场景我见过,在电影里,这和电影中旧社会地主家里大厅的场景几乎一样。
郑佛爷抬头,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他妈怎么在这里?****,你他妈从哪冒出来的?”
我说,“我来看你。”
郑佛爷说,“****,你怎么不先打个电话。我刚好今天周末没去市里的公司。”
我说,“我只是离开了上海,也不知道去哪里,就走到了河北,其实也没想过要走到河北,后来突然就到了,到了河北,其实也没想过要走到高碑店,后来又到了高碑店,到了高碑店就来看看你。”
郑佛爷说,“你怎么找到我的家?”
我说,“你大学时说过一次你家在河北高碑店镇旁的一个村,那里有两条河流,附近还有个小学,有个桥,开满一片桃花。就碰了下运气。”
郑佛爷笑,“我服了,你神啦,你才是真佛爷呢。”
郑佛爷的家在一片桃林之中,桃树密集,从桃林外面看去,不知道桃林深处有房子。
郑佛爷伸出他的脚,他的脚和大学时代一样,还是很臭。
“在上海过的**不**?”
“**个什么**,就是份工作,上班下班月底拿钱。大城市,车上地铁里街上人挺多。你呢?”
“回来市里,我开了个小软件公司,专做附近几个镇里乡里一些小公司和政府部门的信息系统,其实也就是建些网站。”
“创业了,还做政府部门的生意,以前躺在我下铺象团稀屎,你还真弄得人模狗样的。”
“创个蛋的业啊,我是被创业了。我们那个烂校,我的成绩单,北京就不谈了,保定都找不到工作。这都是吃饺子吃面长大的,总他妈得给条活路啊,我爸给我钱在市里开了这个小公司,给生意的都是我爸的朋友。我雇了两个JAVA和数据库工程师,加点简单的HTML,去年开发,今年继续开发,明年计划维护升级。一点点小生意,建网站也没什么很**的技术,每天也就吃吃喝喝和朋友们泡泡澡打打牌。比不了上海,但是生活安定。”
“上海,也没什么特殊的,每天都做一样的事,也看不到个前途,我总想出去走走。”
“想去哪里?”
“没想好,现在还不知道。大概先是欧洲,交通方便,适合旅行,总看到那里的照片,挺多古老的建筑和小镇。”
“嗯,是该去其它地方旅行看看。上个月我觉得无聊,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去了丽江。”
“我几年前去过云南一次,丽江感觉怎样?”
“那地方还能怎样,白天看看破砖烂瓦一大片,晚上在那些破砖烂瓦屋顶下酒吧约炮。没个女人,左手压力太大了。”
“约到没有啊?”
我看着他笑,每次看到佛爷我都会笑。
“能有那么好约到吗?回来后我妈就急着给我安排相亲了,我们这乡里都结婚特别早。我都相了八十多次亲了,有时一天上午相完了下午再相另外一个,都是镇上的女孩子,嘿还真邪门,不是我看不上别人就是别人看不上我。”
“别人看不上你有个什么邪门的。八十多次,你当你是皇帝选妃啊,那你现在在镇上是名人了,去次镇上,街上的女孩子都是熟人。”
郑佛爷大笑,“对啊,都是我佛爷相过的。不敢去了,怕被人追着要签名。上周又见了一个女孩子,个子挺高,苗条,长的真漂亮,我一眼就看中了,去年从保定一个什么学校毕业,现在在市里的卫生局工作,那女孩子和她家对我们家挺满意。这次相中了。”
我又笑,说,“听起来不错,这女孩子给你,真糟蹋了。”
“佛爷我,佛爷我通宵炼级杀小怪修来的,我通宵炼级杀小怪容易吗?我通宵炼级杀小怪容易吗?”
“你这个烂佛爷……”
他停了一会,端起青色的花瓷茶杯看了看又放下,说,“我这辈子算是定了,就在这里了,完了。”
佛爷比大学时胖了很多,他说的时候就这么坐着,像个电视剧里革命战争时期的土财主那么坐着,面对着他那大屋客厅的前门坐着,清晰温暖的光线从南面射到他的脸,他的脸上已无油光。
他说,“想不想叫上徐涛,他就在北京城里做事,南五环外面,开车离这就一个小时,叫上他,一起聚聚,毕业一年多了。”
徐涛工商管理毕业后回了北京,他上班的地方在城市南边的一个小游泳馆,在一个住宅区边的一条小路上。游泳馆外面墙上贴着白色的瓷砖,有了年代,有几块都掉了,露出灰色的水泥。游泳馆的门前有块水泥地,上面立了个简单的篮球架,篮圈上有点锈迹,水泥地上画了一圈白色的三分线。三分线外停着几辆黑色的轿车,有个小凳,坐着个看门的老大爷,穿着一件薄棉袄,在北方秋天的阳光下眯着眼,面对着小路对面的几个小杂货店。
我和郑佛爷进了游泳馆,就靠着游泳池边的墙站着。
徐涛在池里。他教十一二岁的小孩子们游泳,蛙泳,头一下子埋在水里,一下子在水面。中间休息,徐涛从游泳池里爬起,就像一只大的乌龟,他的背上胸前大腿小腿长满了黑毛,孩子们就在游泳池里光着上身趴着抬头看着他。
徐涛大声对仰头望着他看的那群孩子们问,“教练游的好不好?”
孩子们声音整齐的说,“好——”
徐涛又问,“教练游得快不快?”
孩子们又声音整齐的说,“快——”
徐涛再问,“你们长大了想不想和教练一样?”
孩子们再声音整齐说“想——”,那个想字的声音特别大拉的还特别长,游泳池外看门的大爷都可以听见。
徐涛对孩子们说,“你们要是长大了想和我一样,现在就好好学游泳,游得快,将来就能上大学,上了大学,就,就一定要学工商管理。”
我得承认,睡在一间房四年,我以前并不知道徐涛如此幽默。问这些小孩子话的时候,他身上的水珠从头顶肩膀顺着他背上胸前大腿小腿的黑毛流到游泳池地面瓷砖间的缝隙,又顺着那些缝隙流回水池。这时候看门的大爷就跑进游泳池,看着徐涛,看着从徐涛身上黑毛流下的水珠乐呵呵的笑。
徐涛的眼睛,明亮清澈矫捷,和他坐在安城风沙中烧烤摊和我们一起喝酒的那些夜晚一模一样。
那天,徐涛,郑佛爷和我一起站在街上,就像回到大学里那样,无忧无虑地等着被乌鸦吃剩下的柿子从天空落下的日子。那天天空晴朗,路边金黄的银杏树叶在风中缓缓飘下,带着随着阳光变化的影子,我听不到南五环汽车的声音。
徐涛说游泳馆马路对面右边的小杂货店是他开的,在游泳馆做教练只有每天下午两个小时课程,其它时间就租下这个小杂货店。那小店经历过北方城市的春夏秋冬,春季的风沙,冬季的雪暴,换更换过无数老板,卖过米粉豆皮油条盒饭刀削面,卖过书本文具礼品鲜花自行车,上一任做理发的师傅回到乡下后,这个店给徐涛包了下来,现在是个小的杂货店,也卖体育彩票。
店里有个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大的男孩子,徐涛说,“这我表弟徐慧智,在天津念医科,刚毕业还没找到工作,估计以后医人没希望就他妈只能去做兽医了。”
卖彩票的窗口上挂着三个玻璃框,里面裱了一副对联,红纸黑字,左边是“人无横财不富”,右边是“马无夜草不肥”,顶上的横批是“隔三差五”,那几个毛笔字写得乱七八糟,歪歪扭扭,有的字大,有的字小。
徐涛说对联是游泳池看门的大爷给他写的,那老大爷每天呆坐在大门边看着大门无事可干,每天就爱就读读书,上上网下下棋,玩玩牌,练练毛笔字。读的是易经八卦,左手右手,光明正道,旁门左道,经脉运势无一不知,无一不晓。毛笔写的是行书,天天练也算是有模有样,听说徐涛的小店开了张就给他写了副对联。
郑佛爷盯着看了一会说,“像鸡爪抓的,歪七竖八,这天天练字就写这样,还不如我给你写呢。你个****还真敢贴出来。”
徐涛说,“你知道个屁,这几个字的确是大爷的真迹,不过他是用左手写的。大爷说我经营的是旁门左道,对联要用左手写运势才能旺。”
徐涛说起毕业的这一年多。他说高中的时候,自己在南五环附近这片儿念的书,是个游泳的特长体育生,就是在这个游泳馆游泳,每学期代表学校参加比赛,为学校得过无数市里省里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评上了省里的二级运动员。后来高中毕业,按刘涛自己的话说就是其实除了游泳连个毛都不知道,用体育特长生的指标上了大学,就去了个干枯没水洗澡风沙大的安城,学了个工商管理,遇到了我和郑佛爷。后来在大学里还是游泳,在那个干枯没水洗澡风沙大的安城里游泳,在池子里游的象鱼像蛙一样,又得过无数市里省里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后来游着游着就工商管理毕了业。就回到这里,南五环附近这片儿,在这家游泳馆做了教练。
“大学毕业,还是除了游泳连个毛都不会。过了年,朋友介绍我去个中学,做体育老师。”徐涛坐在小店门前的凳子上,从裤子里掏出一包烟,“像我这个样子每天抽烟,肯定会得肺癌,是活不过七十岁了。昨天晚上看了一个电视节目,说的是烟里的有害物质,我看到电视里面把从一包烟里提出的尼古丁注射到一只又大又肥的老鼠身体里,那只老鼠,那只老鼠真的,立刻就死了。”说着拿出三根烟,给了郑佛爷和我每人一根,一根叼在嘴里,点了,吸了,吐了一大口烟圈。
“滚蛋,活七十你还不够,”郑佛爷凑着徐涛的打火机点了烟。
我吸了口烟,又吐出来,“你每天抽烟,每天抽,每天享受自己喜欢的东西,到了七十岁得个肺癌,这叫死于自己喜欢做的事,一点都不怨。”
徐涛的小店里,电视机屏幕上是黄日华版的《天龙八部》,乔峰快马奔腾,和他在一起的是美丽女人阿朱。
徐涛说,“这些电视台通常在下午放一些前些年的老连续剧,不过,《天龙八部》我看了两遍,我还是不太明白?”
我说,“你不明白什么?为什乔峰非的要是个契丹人?为什么他用的降龙十八掌和郭靖的不一样?还是为什么一个契丹人长了香港人的样子?”
徐涛说,“狗屁的香港人。其实不只是天龙八部,所有的古代武侠剧都一样。这些人,成天没个正经工作,醒来就挺着肚子四处走来走去,走累了就上馆子喝酒吃肉,吃饱了就一定会找点闲事砍人,你说他们哪来的钱。”
我说,“我爸也这么说。”
郑佛爷说,“成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吃了累了睡醒了就咬人,我家的猫就是这样。捡来的,是只灰色的短毛,常常睁着眼在院子里晒太阳,眼睛比那个长头发的丐帮长老还圆。”
徐涛擦了一下他的那副对联上的灰,街上开过来一辆红色的出租车,缓缓停下,停好了,司机座位上走下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走来,对徐涛笑着说,“唉,涛哥,下午好,买彩票。”
“要几张?什么彩?”
“福彩两张。还有,涛哥,这个周末的CBA有没有什么推荐和盘口消息?”他斜着身依靠着徐涛卖彩票的窗口,他上身靠着的位置挡住了对联上“马无夜草不肥”的“草不肥”三个字。
电视机屏幕上,乔峰运功,发掌,聚贤庄的游氏双雄死掉了。
“盘口让七分,内幕消息,水很深啦,就押一千吧,别玩大了。开车赚的那点都是辛苦钱。”说这句话的时候,徐涛的胳膊从卷起的衬衣袖子伸出来,上面满是浓密的黑毛。
出租车开走了,快到下班时间,进出住宅区的人开始多起来。
电视机屏幕上,乔峰飞起,消失在他来的方向,美丽女人阿朱看着他,地上留着游氏双雄的尸体。
“唉,”徐涛看着电视机,叹了口气说,“乔峰要是我们********就好了。”
然后弯腰从小杂货店里拿起一个篮球,叼着烟,走到那块水泥地上。
水泥地和带着锈迹的篮球筐在北方秋天的下午显得有些萧条,阳光并非那样的温暖。
徐涛,郑佛爷,和我,三个人站在水泥地上。
徐涛拍拍篮球,走到三分线外,阳光穿过路边的树叶照到他身上的李宁运动夹克。
我记起在安城念大学的时候的时候徐涛,郑佛爷,和我打篮球的球场,那里有个自来水管;还有棵大柿子树,要一个人才能抱住;渴了我们就对着水管喝水,急了我们就对着柿子树撒尿。那棵树,它在安城的风沙中这么多年,经历了无数大学生,像我们,入大学,大学毕业,象种谷收稻,枯了的,死了的,活着被磨成面粉的,四年一茬,一茬过了又一茬,每个人都会有离去的那天。现在唯有那棵大柿子树还留在安城,看着风沙,听够了古塔上的铃声,吸足了尿液,更加枝叶茂盛,英气挺拔。
徐涛投出三分球,球弹在篮筐上,弹出一道弧线,就像当年我们的尿液,飞出去很远。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吃了几斤涮羊肉,喝了红星二锅头,我喝了很多,他们也喝了很多。到了夜里,郑佛爷半睁着眼抱着我说,“我们四年都住一个屋,睡一张床,上铺下铺,我们大学就喝红星二锅头,今天你来,我们还喝红星二锅头,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大学,大盘鸡,啤酒,二锅头,通宵打游戏,看日本片,经济系的女孩子,回不去啦呀,回不去啦呀,回不去啦呀。”
我没说话,就让他这么抱着。
其实,我只有回去,除了回去,除了回到上海我无处可去。
那个夜晚,从乡村回到县城回到城市再到另外一个城市,透过火车的车窗,那些远处村庄中模糊的灯光被吞噬在黑暗中。郑佛爷是个有趣的名字,他是个冒牌的佛爷,但是冒牌的佛爷也是佛爷,我每次见到他都笑,数千年来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刻笑着哭着在佛爷面前遗留下一些东西,真佛爷或假佛爷,自愿或被动,重要或琐碎,自己也不曾知觉。
二十三岁那年的秋天,我漫无目的离开了上海,又发现自己只能回到上海。如果三牙叔还在身边就好了,他是不是还会坐在我对面,那样平静地说:孩子,不要担心,你会看看这个世界的样子,你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二十三岁那年的秋天,无法后退,只能向前,我只想知道可以去哪里,在那里,宿命是每一个人找寻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