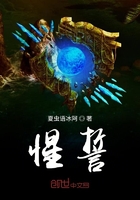村长走了。肥鸡说,这已是半个小时之后。
谢天谢地。姬铭跪在地上,——不,简直是匍匐在地上,心中充满了感恩。
村长说了一些怪话。肥鸡说。
说我吗?姬铭的心又悬起来了。
肥鸡点点头,没错。
都……都说了些什么?
真要听?
要听……姬铭的底气很虚,好像有秋风在他胸膛里萧萧地吹,一天一地都是纷扬的落叶,状若冥币。
他说你这个贼骨头。肥鸡盯着姬铭,不动声色地说。
我是贼骨头。姬铭颓唐地坐下来,打从生下来我就是贼骨头了……有时候什么都是天生的,你没的选择,不是吗?
肥鸡说有点道理。
姬铭说别的人好多不敢走夜路,我敢,天越黑别人越看不见我我就越胆大,我能在坟园子里睡觉,我敢跟猫头鹰聊天……可白天我一上路就心慌,脖子发软,脑袋耷拉着,不做贼就跟做贼一样了。我知道我这是贼性不改,不是贼骨头是什么。
肥鸡说不说我还不知道,你贼得很啊。
姬铭咬咬牙,村长还说我什么了?
肥鸡说他骂你什么崽子来着?
哦。姬铭点点头,他骂的对。我们好多人都是崽子,崽子跟孩子不一样,听着就不一样,对吧?甭管你是地主崽子汉奸崽子狗崽子兔崽子……反正你就是崽子了。俺爹老早就被镇压了,扔下我这个崽子不要了。人家都说俺爹一辈子吃得满嘴流油、肥头大耳,结果他把自己吃到枪眼里了,撇下我这个崽子挨饿,饿了几十年……
姬铭的眼里就有了泪。泪光一晃,姬铭看到过去了。小姬铭坐在岁月的深处,颧骨挺着,头发黄着,两只眼里全是食物的颜色。小姬铭说:我饿啊……小姬铭眼里食物的光色就渐渐暗淡成了两条森森鬼影,头慢慢钩下去,钩下去……有好心人偷偷掷来半块馍,小姬铭拼尽力气,狗一样叼进嘴里,狼吞虎咽,噎住了,脖子在灰色的岁月里越拉越长……终于,肚子里抑扬顿挫了一阵,小姬铭的眼里又恢复了食物的颜色……长大了,小姬铭依然瘦小,像一棵弱不禁风的马鞭草,眼珠左转右转,还是食物的颜色。无事时,小姬铭就蹲在房檐下,不想亲人,不想老婆,不想孩子,满脑子都是吃食。有人问:狗崽子,想什么呢?小姬铭便嗖嗖地从眼里射出两支利箭,翕动着干涩的嘴唇,声如裂竹:我——饿——啊——人就笑了,说你这个饿鬼,报应啊。……后来,姬铭岁数大起来了,弓下身,是鼠的脸,狗的形,眼里也还是食物的颜色,只是浑浊许多。
……老了,连头顶的岁月都老了,像灰黄的茅草,像哮喘似的风,帮孑然一身的姬铭数着余下的日子。岁月说,姬铭,你的饥饿把我的心掏去了,我是空心的了,也成空洞的了。姬铭说我没法啊,我饿啊……姬铭推着一辆破旧的手推车一如推着他破旧的生命,兜售些调味料之类的东西,都很贱,讨口饭吃吧。所幸人见他可怜,用得着的多买几包,用不上的买了备着,权当施舍。……房上的一只蜘蛛陪姬铭住了多年了,老态龙钟地趴在网上,说姬铭啊,好歹现在你也有个小生意了,总该不那么挨饿了。姬铭靠在岁月干瘪的怀里,叹一声说不行啊,我还是饿,饿得像被掏空一样了……
姬铭这么把过去的年月浏览了一遍,胸腔里堵堵的。姬铭说肥鸡啊,你又是谁的崽子,你知道吗?
肥鸡说不要往我身上掺和,反正我不是崽子。
姬铭说哦,你不是崽子。
过了会儿,姬铭挠了挠头,说没准谁都是崽子。
肥鸡说老姬,你怎么说没头没脑的话?
姬铭说只要你心里有个影子,你就是这个影子的崽子。你得不到什么,你就是什么的崽子。姬铭的嘴角泛出了腻白的泡沫,说你可能是政治的崽子,你也可能是钱的崽子,你还可能是道德的崽子……你什么崽子都可能是,当然,还有像你这样的,是崽子但又不知道是谁的崽子。
肥鸡眨眨眼,说老姬,你把我说糊涂了。
姬铭说,我也把自己说糊涂了。老了,脑子不清楚了。
肥鸡说不过也算一家之言吧。——是崽子就会感到饥饿吗?
姬铭说对呀。我能在每个晚上听到一些很秘密的声音,有月光的晚上我就听到月亮说,崽子们饿啊,那就星作芝麻天作饼吧。于是,月亮哗啦一声,碎了,天就变成了一张没边没沿的芝麻饼,香得连风都跑到树梢上呼哧呼哧大口闻味呐。逢着落雨的夜里,我就听到雨点嘁嘁嚓嚓地说,崽子们饿啊,那就泥土作面雨作浆吧。云彩咳嗽一声,雨就下来了,多好啊,到处是肥浆白面,热乎乎的暖饥肠啊……可是,我吞咽着它们,影子浮上来,我就更饿了,我饿得欲哭无泪欲叫不能,我疯了,饿疯了,然而我一看到那条影子,我就又清醒得很了,我就知道我饿呀我饿呀我饿呀……
肥鸡说玄,真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