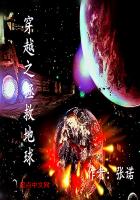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几个时辰匆匆而过,正鸾殿中,光色已经开始转暗,终于到后来黑呼呼的一片,虽然处在尸身遍地的空旷殿阁内,但四人均神色如常,丝毫没有惧怕,柳飞容与止憨自不用说,子驭棋道突破天元化境,而臻至一元复始后,距离上窥天道已是不远,此等惨象自然不能扰乱其心,而苏旷得到天地正气灌顶,气质上早已非昔日文弱书生,脸上亦是毫无异色,不过,大半日没有进食,众人的肚子却开始咕咕叫了,苏旷道:二弟,我们处此险恶之地,生死尚在度外,就不拘泥形式了,你将那具烤牛骨架拿来,刮矶刮矶,也可刮下二三十斤牛肉来,我们兄弟三个分来吃了,止憨才食得一只烤牛,想必不是很饿,再说,这三十斤牛肉给他塞牙缝也不够,止憨憨然一笑,柳飞容走过去,将那牛骨架提了过来,兄弟三人吃了个饱,柳飞容抹了抹嘴道:大哥,三弟,四弟,你们在此原地休息,我四周探查探查,苏旷道:不急,等子夜时分再去探查也不迟,那时候人最困乏,应是一周天中守备最为松懈的时间,柳飞容依言而坐,又过了良久,殿堂内的光线似乎更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四下里一片寂静,柳飞容猛地站起身来,我去探看。苏旷道:到子夜时分了吗,柳飞容道:嗯,刚才更鼓已然响过,已是三更时分,苏旷讶道:我怎么啥也没听见,柳飞容笑道:那是自然,这更鼓是自紫禁城外面的市街小巷中传来,离此地足有十里之遥,陡地一个轻跃,身子已经掠了出去,空中连续五个空心跟斗,最后一个猿猴攀枝,双腿稳稳倒勾于殿堂内的一根横梁上,伏低身子,将板木窗上的纱遮掏了个窟窿眼,向外望去,殿门前阔大的青石广场上,夜凉如水,空无一人,连街灯也无一个,一只不知何处行来的野猫正在殿外的围栏上觅食,整个显得萧瑟空冷,荒凉寒幽。
柳飞容左手向后一招道:兄弟们过来,现在没有人,我们敢紧伺机离开,苏旷,子驭,止憨跨过杂乱无章的考生尸体,来至殿门边,柳飞容在上面轻轻一推,门霍地开了,止憨当先一步,就要跨出殿门,后面的苏旷陡然地伸手,拉着止憨道,四弟回来,止憨回过头来道:大哥为何拉住我,苏旷自己也说不上原因,就在刚才那一刹那间,忽然有一丝不祥之感涌上他的心头,这种感觉好像是从胸口所佩的龙蕊玉匙上发出来的,苏旷定了定神,抬头望了出去,围栏上有只觅食的野猫,听得身后有动静后,不仅没有溜走,反面扭身跳下,一步步僵直地向门口爬行过来,这太不符合常理,苏旷心中打了个突,凝神看过去,那只行走有如僵尸的猫眼中,两颗眼珠在黑夜中竟闪着磷磷绿光,苏旷心中一紧,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他记得那日在赴考途中,在乘船夜经北氓山中一个深谷时,却被一群尸獐变化成妙龄女子所迷,当时幸亏酒仙前辈随行,给他,谢世荣,楚樵三人每人一张符录,勘破了尸獐们的障眼法,后来酒仙前辈并没有收回符录,而是送予了他们并告之,此符录可用三次,三次之后自动化为灰烬,此刻,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将之贴于额前,冥目半响,再睁开眼来时,陡地吸了一口凉气,幸亏换了此时的苏旷,要是以前,非给吓个半死不可,原本殿堂前空无一人的广场上,竟有无数幽灵鬼魂在游荡,有的披头散发,双眼无瞳,有的面目干脆就是一张白板,没有五官,整个身子仿佛一薄薄画皮在空中飘动,有的好似那大王洲上的无头女鬼,只剩下半截身子在地上蠕动,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幽灵,根本不像人类,似狐非狐,似獍非獍,恐怖至极,这哪里像是皇家内苑中应有的景象,分明置身于一个荒山野岭间的坟场鬼窝。更可怕的是,此刻的殿门外,走廊之上,四个吊死鬼鬼魂正一字排开,伸着长长的腥红舌头,堵在门口,狰狞无比的神情,正望着将从殿门内走出的止憨,苏旷抹了一把冷汗,幸亏自己及时拉住止憨,否则这一脚踏实,后果不堪设想。苏旷抓紧子驭和止憨的手,抬头对梁上的柳飞容道:二弟,此刻尤其危险,外面诸多鬼魂邪物盘布,你还是下来罢,我们另商对策,柳飞容讶道:不会吧,我明明望过去空空如也啊,什么也没有,一把跳下来,苏旷把额前符录摘下,贴于其额头上道:你再看看,柳飞容睁开眼来一瞧,哎哟,我滴个娘呢,这么多奇形怪状的鬼,夏华皇宫几时变成鬼窝了,现在你相信了吧,苏旷道。走,我们回去再细细商量,几兄弟怏怏回至原处,谁也没有心情说话,相互间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却是都没有好的办法。
时间一点点流逝,转眼间天就亮了,外面人声嘈杂,柳飞容上前打探一番回来,苦笑道:又回复到昨日那警戒森严的局面。众兄弟没有什么办法可想,而时间仍在一分一秒地走着……,殿堂内的光线黑了又亮,亮了又黑,苏旷四兄弟挨着围坐,相对无语,苏旷道:这已是第三日的晚上了,如果我们今晚还想不出办法,明天天一亮,就只能坐以待毙了。子驭道:我有个主意不知行不行,三弟你说,苏旷道:我们不如将自己装扮成鬼的模样,走出去混淆那些鬼物的视线,苏旷摇头道:这个可能不行,不要说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鬼物是靠触觉,视觉或是其他方式感知同类与异类的存在,就算是我们要将自己装扮,也要有相应的道具才行呐。你看这里,除了满殿的尸体,哪有什么道具呢。子驭道:死马当作活马医,不试试怎么知道成与不成,要说装扮道具,这里不是有现成的吗,那些考生尸体血肉模糊,衣衫凌乱,我们一人拉一具掩在身前,不就是最好的道具扮相吗。苏旷苦笑道:这不是要和那些鬼物玩捉迷藏,过家家吗,也亏你想得出,也罢,反正没有其他法子可想,试一试也好。几人遂开始挑拣尸体起来,这时,柳飞容忽然指着台上某处道,噫,那里有具尸体,衣裳看上去比较干净,我去挑来,总是比这些血迹不堪的尸体污秽我衣服要强。苏旷,子驭,止憨没有柳飞容神目如电,自然是瞧不见,苏旷心中突然一动,不对呀,且慢二弟,台上面怎会有尸体呢,我们三日两夜都呆在此处,殿堂内的物什位置都记得清清楚楚,那台上除了那夏华皇帝曾坐过的鸾椅外别无他物,莫不是外面的鬼物冲了进来,又或是某位枉死考生含怨诈尸不成,柳飞容艺高人胆大,我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大步向前走去,苏旷三人不放心,紧紧跟随,临到近前,那一直蜷伏于鸾椅上的尸身突然动了,抬起头来,朝着众人咧嘴一笑,随即站起身,双足双手在台上乱舞乱蹈,嘴中却念着一些幽瑟难懂的话语:‘黄泉大道西又东,包复惊,九曲星河现啊,天雷炸我八嘎’。好似一个疯子在那胡言乱语,当尸身站起来的一刻,四兄弟同时觉得脑袋一轰,原来,这竟是一个他们都认识的人,一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是他的人,苏旷内心的震骇实是难以言表,他倒宁愿台上是一具真正的诈尸或是鬼魅亦好,虽然看上去恐怖,心头却是明澈。哪像此刻,心里却是一片压抑的恐慌。前面的柳飞容冷冷道:我们兄弟四人已是插翅难飞,靖执流陛下又何必如此下作,在此装疯卖傻,愚弄我等,莫非这又是陛下即兴而发的一个新的游戏玩法,抱歉,我们兄弟恕不奉陪。谁知那陛下竟然充耳不闻,双目失神间,尤自一个人在那疯言疯语地念叨不休,四兄弟听得面面相觑,苏旷道:难道是其前日与三弟下棋,用脑过度,精神真的出了问题么。子驭断然否决,这不可能,此人棋力之高,我连望其项背的资格也没有,和我下棋,他根本不用耗费一丝精神力,柳飞容道:管他是真疯还是假疯,既然人在这里,我们将其制住,挟在手中作为人质,明日必死之局说不定还有那么一丝希望,苏旷点头道:这却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