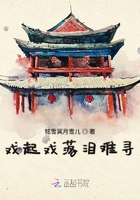瞿南乔是那日在九重天里遇到的蒋大公子。
他叼一根烟,坐在楼上的雅间里,就看到蒋大公子在舞池里,一双手在他舞伴的身上游走,嘴边还含了一股笑意,形容之猥琐只叫生子都皱起眉,呸了一口,“这个乌龟王八贱货!”
“你去把他带上来。”瞿二爷冷冷道。
生子自是兴冲冲就去了,不一刻,蒋大公子便就一脸不耐的,叫生子给揪了上来,一进到这雅间,顿时就傻了眼,吞吞吐吐道,“妹,妹夫,你怎么在这里?”
“这不是来找您来了。”瞿南乔道,边就手一指对面的沙发,“坐吧。大舅爷,茶都给您砌好了,您请用。”
“哟……”蒋大公子见他面色冰凉,一时心中不免拿捏不准。自己的这个妹夫,他是见识过的,何时对自己这样和颜悦色过?就缓缓的,挨着沙发边坐了下来,“南,南乔,你找我,是有事呀?”
“有事啊。”瞿二爷就看了他一眼,“昨天下午,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说说。”
“什,什么呀……”
瞿南乔就望着他,并不说话,他就笑着挠挠头,“你是说沈公馆里的事吧?”
“果然是你干的!”瞿南乔大怒,猛的就冲了上来,一只手就抓着他的衣襟,咬着牙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们两姐妹哪里得罪你了?沈云汀不过是一个七岁的孩子,你下这样的手,也不怕吓着了她。”
“妹夫。”蒋公子嘿嘿笑了两声,“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冷静点啊。”
见瞿南乔仍旧咬牙切齿望着自己,脸色也冷了下来,哼一声道,“看来你果然还爱着那个女人啊。”
这话如一记闷雷,猛然就击在瞿南乔脑中,“你胡说什么。”
“胡说?”蒋公子拍拍他的手,“当着你这么多手下的面。我会胡说?即然你不爱她了,我做了些什么,又碍着你什么事了?我不过跟沈小姐开个玩笑而已,你这么激动,真的很难叫我不联想其他地方去啊。瞿二爷,你娶的人可是我妹妹!”
瞿南乔见他模样猖狂,一时竟是拿他无法,哼了一声,到底是松开了他的衣襟,他就也哼笑了一声,抹了抹自己的衣服,“妹夫,我可是早就提醒过你,叫你好生待我妹妹。可是你就是不听,你不听,那也别怪我做出什么更过份的事来。”
“你到底想怎么样?”瞿南乔道。
“我想怎么样你不知道?”蒋公子道,“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她嫁给了你,你却不善待她……”
“废话少说。”瞿南乔道。
“你去蒋家她把她接回去,省得她天天在家里跟我闹。”
“叫她向我娘道歉。我就去接她。我说过的。”
“好,我叫她道歉。”蒋公子道,言罢就起了身,“明天就来啊,你要是食言。你知道我什么都干得出。”
瞿南乔冷冷盯着他的背影,“你要是敢再动她们俩姐妹一根汗毛,我的手段,大舅爷你是知道的。”
蒋公子的身形就顿了一顿,还是缓缓转过头来,见瞿南乔的面上无一丝玩笑之意,一时又是恼又是气,“你,你只要好好对我妹妹,我保证不去招惹她们。”
如此一来,接连几日,沈公馆却是风平浪静,再也不曾发生任何事,倒是瞿南乔因是担心她们两个,沈公馆占地这样广,统共就四个人,难免不安全,于是便就叫生子出面,给沈家请了两个护院,专作平日里保卫一事。
沈云慢原意是关乎瞿南乔的事,全部拒绝,耐何是生子出的面,加之对于安全一事,的确是心有余悸,也就听之任之,不做多言。原本担心着的沈云汀,也不知是护身符的缘故,还是那夜喊魂成功,过了几日,竟是如同没事人一般,又恢复起往日里的活泼来。
于是瞿二爷那天接了因赌气回娘家近月余的蒋小姐回到瞿公馆,蒋含烟自是低眉顺眼的,向许氏看茶认错后,这才娇嫡嫡的回到瞿南乔身旁来示好。
瞿二爷亦自知理亏,那心里头,却是又放不下沈云慢其人,一时心中痛楚,竟是无处宣泻,忍耐了一两日,耐何蒋含烟其人,许是自幼在家中泼嚣惯了的,人若对其好,她竟是不由自主变本加厉,又寻着个事端与他吵了两次。
以至他愈发难以自制的,仍是隔个一两日,便要来沈公馆坐上一坐,却是也不久坐,只是与沈云慢客气的寒喧的几句,点到即走,尚在心中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个之形像,在沈小姐心中大有改观。
于是这一日,却是个星期日,沈氏姐妹两个将将只起了床,洗衣漱完了,下得楼来,便见瞿二爷兴致勃勃坐在沙发里,一见她们两个,就笑着站了起来,手一指,还躬了躬身,笑着道,“二位小姐,请用早膳。”
沈云慢眼眸一睃,便见餐桌之上,摆了满满一桌的西式早点,看他满眼都是期盼之意,眉头就皱了一皱,其实想一想,这段时日以来,这人为她姐妹两个做的事,也的确,叫她心下不忍来对他冷眼以对。
那头沈云汀却已经惊呼一声,就冲到餐厅去了,他眼里满满都是笑意,又回过头来看沈云慢,“去吃吧。”
她的原本一张冰冷的脸,不由自主却是暖了几分,也不说话,低着头,到底是进到餐厅里去了。
他跟在后头,行至餐桌旁,就从醒酒器中,倒了一杯红酒给她,还柔声道,“偿偿。”
彼时正是夏日里的清晨,晨曦从窗口柔和的撒进来,照在这姐妹两个的身上,顿时生了一股柔和之意,她端着那杯子,缓缓缀饮了一口,看到杯中光影晃动,一时整个人竟是恍惚起来。
听到瞿南乔在那边道,“云慢,我这里有一首诗,念给你听听,好不好?”
沈云慢就怔了一怔,望向他,极是诧异的,笑了一笑,“瞿先生要念什么诗?”
瞿南乔就正了下神,一本正经的,从衣兜里翻出一张纸来,铺在桌上,咳了一咳,念起来,连沈云汀都放下了手中的吃食,扑闪着眼睛听他轻念: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温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甜美是梦里的光辉。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负心,我的伤悲。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他的声音极是温柔,那字一颗颗直朝她心房砸过来,次次都轰鸣阵阵,一时间叫她自觉无处可逃,仍是极力坐在那,一动不动的,听着他念完了,待他念完了。她笑起来,“是徐志摩的诗啊。”
瞿南乔微低着头,左手捏着那纸,到这时,竟是觉出恐惧来,恐惧她是又要退了,好不容易她前进了一步,因着这诗,是又要退回去了。悔意一层层漫延开来,果然听到她轻声笑着说,“‘她的负心,我的伤悲’…..瞿先生是似有所指?怎么了瞿先生,跟夫人吵架了么?”
她虽是笑着的,那话中的清冷之意,只叫沈云汀都放下了手中的刀叉,睁着眼看着这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