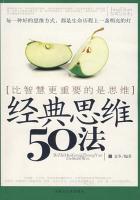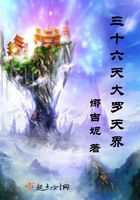恩格斯在晚年见证了这些变化,并从中作出了某些新的结论。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承认,他在1845年对英国的描写,“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剥削的最残酷恶劣的手段有许多已经消失了。工人阶级的状况有了某些好转,例如卫生条件有了改善;罢工不仅被资产阶级承认了,而且有时简直被工厂主们“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以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观点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被废除了;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法律;普选权正在实现……凡此种种,都给劳资关系以重大影响,使得“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就工联工人而言,恩格斯用颇含讥讽的笔调写道:“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15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这些描写是非常贴切的。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实践一旦具有长期持续性,就必定会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培育起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它会促使工人阶级群众在心理上潜移默化地由倾向于革命转移到追求改良,从而使改良主义情绪大面积地蔓延起来。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19、20世纪之交,在西欧主要工业化国家里,随着工人运动不断取得成就,工人阶级运动中普遍滋生起改良主义。普通工人乃至社会主义者日益沉湎于琐碎的工会日常活动中,对革命之类的概念失去了兴趣,他们越来越专注于互助、济贫、发展社会保险等日常事务,对于争取工资的提高和工时的缩短,比对于了解资本主义以上引文均见该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剥削的政治经济学实质更为关心。工会的领导人们不但惧怕革命,甚至回避罢工。当1905年俄国革命的浪潮波及西欧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发起了关于总罢工的热烈讨论,工会方面却抱之以强烈反感,一位支持工会改良主义的领导人愤怒地喊道:“总罢工等于总胡闹!”相应地,在政治运动中,西欧社会主义者越来越热衷于纯粹的议会选举活动,他们对拥有多少议席和选票的关心,远过于对通过议会进行革命宣传的关心,先前为人们所鄙视讥讽的“议会主义”、“议会迷”,现在逐渐蔓延起来,潜移默化地侵蚀掉了革命的精神。
来自运动下层基础的这种变化必然给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带来深刻的矛盾,引发尖锐的争论和冲突,一批反映和代表改良主义情绪的理论出现了。
在英国,有崇尚“缓进”的费边主义;在法国,有社会党人米勒兰的“入阁”事件;在德国,有党的理论家之一伯恩施坦对正统学说的挑战。伯恩施坦事件特别出名,竟引起了一场国际争论,暴露出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深刻的思想分歧。
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崩溃必然性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明出了问题。资本主义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大大进步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阶级斗争的残酷性等等都日益减少,利用资本主义内部的改革来谋取社会主义进步的可能性则与日俱增。所以,他主张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应作重大修正。他宣布:“按照我的意见,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我认为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赋予它以纯粹物质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现在只能转移到伦理道德上来,社会主义者只能把资本主义当作不公正、不道德的现象去反对,一部分一部分地改变其弊病,通过渐进的方式去接近社会主义的胜利。伯恩施坦的这一整套修正主义理论激起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愤怒,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大理论权威卡尔·考茨基到左派的激进代表罗莎·卢森堡,都起来对伯恩施坦进行批判;从西欧中心城市到偏远的西伯利亚流放地,到处都听得到社会主义者对伯恩施坦的抗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上专门对修正主义进行了谴责。然而,伯恩施坦的思想挑战拥有深厚的改良主义思潮的基础,以致他本人虽然受到了严厉批判,他所代表的思想情绪却在继续发展扩大。多年后,他颇为自豪地宣称,他的主张虽然在代表大会上被击败了,但在实践中却胜利地前进着。这种说法并非自我吹嘘。20世纪头10多年中,德国乃至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越来越脱节了,正式的理论宣传虽然还在坚持革命主张,但运动在实践中却愈益朝着改良主义倾斜。在一次次的争论中,坚持革命的左派日益缩小为少数,改良主义实际上不可阻挡地进军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到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这一趋势终于全面显现出了后果:尽管战争的破坏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在西欧各国引发了动荡,但少数左派社会主义者的革命号召无法激发起整个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革命的鼓动不久就到处被改良主义所淹没,资本主义在自己的中心地区遭遇了一次不小的政治危机之后,很快又重归稳定了。
上面所描述的这些现象,还只是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历史发展行程的先声而已。20世纪,资本主义尽管危机重重,其间还经历过像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空前灾难,但总的看来,它不断在自我调整中完善发展着自己。与此相伴随,工人们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持认同态度,他们的运动被逐步整合进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过程,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反馈、纠错和修复功能。这一事实反映在左派理论家的头脑中,便有当年列宁、布哈林等人所谴责的“上层工人的贵族化”、卢卡奇所抱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被迫变成了资产阶级意识的从属的受束缚的角色”、葛兰西所分析的“屈从于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以及后来马尔库塞所称的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体化”。从一部分工人的“贵族化”到整个工人阶级的“一体化”,左派思想家的这类批评确实反映出了西方工人阶级与现存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变路径。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动荡,危机频仍,西欧工人阶级还部分保留了先前阶级斗争的传统,临到历史的紧急时刻,他们中至少还有一批人揭竿而起,愤而战斗,用英勇行动演出几幕与资本主义抗争的悲壮史剧。在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也还有相当影响。决定性的时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来了。此时,西方社会在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社会生活、文化心理诸领域的变化,把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置于委靡无力甚至日益萎缩的境地。由于战后新的科技革命成果的广泛应用,传统的工业部门大大衰落,一系列对知识技能有更高要求的新兴产业相应兴起;现代银行信贷、股份公司在满足生产高度社会化的要求时,使得货币资本与职能资本、所有权与管理权完全分离开来……所有这些造成了一种新的趋势,使得“管理资本主义”逐渐取代了早先个人或家族统治的资本主义,并导致传统工业无产阶级的衰落;与此同时,一个以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白领”为主的新中产阶级日益壮大起来。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最终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走向政治上的完全的改良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伦理主义和思想上的多元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欧洲各国社会党纷纷入阁执政,全面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有效地促进了混合经济、福利国家的建设。在此期间,劳动者普遍中产阶级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已经通过民主选举影响国家政治,通过“三高”政策部分参加资本利润再分配。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能指望他们超越自己的日常经验范围去响应革命的号召的。
到20世纪末叶,这个过程更加加强,在前苏联“现实社会主义”解体和资本全球化的压力下,社会民主主义进一步自由主义化,不但完全放弃了根本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旨,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彻底摆脱传统左派政策”的主张,只满足于尽量在现有的政党政治框架中维持优势地位,仅仅通过实施具有中左倾向的政策保留一些自己的“身份特征”。在这种情况下,那种由具有理想目标的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大规模工人运动早已不存在了。老实说,在现时期的西方,只有针对某届政府、某一政策或某一事件的偶尔的、小规模的下层即时抗议活动(所谓新社会运动多半即属此类),而没有以往人们所期望的那种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广泛群众性政治运动。马克思主义目前固然还在一部分左派知识分子的学院式探讨中保持着活跃的势头,然而这些探讨在形式上固然可以非常尖锐激进,充满了对社会的批判性,却往往只是纠缠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矛盾,这与当初马克思、恩格斯紧紧抓住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根本问题穷根问底,在深度和高度上都是无法比拟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发展并一直保持其“文化领导权”,其秘密不在思想文化而在经济,从根本说,在于它能够在经济领域不断克服自身的矛盾,使矛盾转化为发展的必要动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保证其社会成员的较为满意的生活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活动的高质量高水平,因此才能获得社会的文化认同。而资本主义最终能否存在,也要取决于这种经济发展能力是否会达到自己的极限。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则思想文化批判哪怕再尖锐、再机巧,也是不深刻的,无济于事的。而这种理论上的退步,又从根本上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具有强大的延续能力,以至足以抑制针对它的思想批判这个事实。在这样的“社会存在”中,是不可能产生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的资本主义批判大师的。托洛茨基曾经有一句话说得很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只能在社会动乱、与传统习惯彻底决裂的时代形成。”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以上这种情况,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有根本改观。
我们决不要再用虚构出来的乐观景象欺骗自己,而要敢于承认客观的事实。
马克思主义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未能得到它所指望的阶级的响应,这对它自己当然不能算做令人愉快的事情。然而,对此也可以用马克思的方法解释清楚。归根结底,这种情况是资本主义进入自己的成熟阶段,自调节能力加强,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宽广发展余地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有一句著马克思学说与资本主义的演进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180名的话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根据这个“原理”,只要资本主义社会还能为它内部的生产力的提高提供余裕,马克思学说所预言的那种革命时代就不会来到。
那么,资本主义究竟能否达到和何时达到自己的极限,以致再也不能满足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了呢?这是一个不能靠空话,而要随着现实发展进程不断观察并通过缜密的经济—社会分析去研究的课题。目前,只能做到从逻辑上大致推论:要么,资本主义终将达到一个无法逾越的极限,于是迎来社会革命的时代;要么,资本主义通过持续的自我改良在无意中实现自我否定,以至像顾准所断言的那样,“在批判—改良中一点一点灭亡掉”。前一种趋势从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似乎不容易得到证明,后一种趋势则越来越具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因为它在过去的100年中已经得到了清晰的验证。尽管当今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但早已不是19世纪的私人资本主义了;尽管20世纪晚期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重新泛滥,但是谁也不可能把资本主义100多年来已经达到的高度社会化成果彻底消灭掉,退回到19世纪的粗陋资本主义去。也许,沿着这个趋势走下去,社会的发展最后将不是通过阶级决战,而是通过自然的演变而达到未来的高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