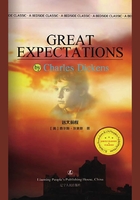想到这儿,男人将女人那早已挺立起来的乳头含进嘴里,一边呼出热乎乎的气息,一边用舌尖裹住乳头画圆圈,同时将另一只手伸向她的私密处边沿,轻轻拨开花蕾,若即若离地缓慢振动花蕾的顶点。
就这样保持一定的频率反复时,女人的乳头和私密处就像银铃般发出了共振,女人愉悦的呻吟声越来越大,然后双手抱住了吸吮自己乳头的男人的头。
看上去,就好像男人黑色的脑袋被涂着淡粉色指甲油的手指紧紧按住了一样,但男人却不以为然地继续着舌头和手指的移动。反复不断地进行着这种说不上是折磨还是服务的爱抚,女人渐渐挺起下身,终于说出“不行了……”,接着又哀求着“求你了……”,很快伴随着一阵轻微的痉挛达到了高潮,于是男人得到片刻的休养生息。
但是对于不断追求着永远的愉悦的女性而言,这不过是刚刚开了个头儿。女人为了寻求更强的快感轻轻侧过上身,与他配合着,男人也大幅度移动自己的位置,将自己的脸埋入刚刚达到过高潮的女人的私密处。
男人以这种匍匐的姿势,继续运用自己的双唇和舌头为女人奉献着,直到女人再次无法忍受,不断哀求之后,男人才踌躇满志地将自己送了进去。
这虽然是男人期待已久的挺进,但是,男人操纵、控制女人的优势也到此为止了。
结合之后,男人的献身将面临更高的要求。
久木此刻完全将自己深深埋入了凛子体内,可是一旦被她那柔软的皱褶捕获,那么无论前进还是后退,都必须得到她的许诺和同意才行。
男人已预见到了前面等待他的遥远的旅程。他首先采用侧卧位将下体贴紧,然后再用腿紧紧勾住对方,固定好位置后,再用左手扶住女人的腰,右手则伸到女人的前胸揉捏着她的乳房。这种姿势虽然需要四肢并用,但从持久性这一点来说,这种姿势最易采取主动,而且能够准确刺激女人的敏感部位。
男人一进一退,一退一进,看起来动作千篇一律,实际上,即使同样的动作,如果时而抬高女人的腰部,就可以令男人热辣的武器扫过那敏感的皱褶表面,女人会因这种微微刺痛的酥痒感觉而呼吸急促起来。当男人稍稍松开那紧贴的秘处,将腰后撤,只用顶端轻轻点触入口处时,那种渐行渐远的焦躁感会使女人更加方寸大乱。
不用说,男人的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使女人得到满足和快感。
到底能撑到什么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就在他奋力拼搏中,伴随着一声深沉悠长的呻吟,女人到达了高潮,那一瞬间,男人屏住呼吸,横眉立目地忍着不发。
如果这时候一起到达高潮,就违背了女王“不要停下来”的命令。忘记了这命令的一刹那,男人将丧失作为雄性的身份与骄傲,化成一片褴褛被葬送。
感觉到女王已达到高潮后,男人像条忠实的狗一般喘息着静等女王放他自由的赦免令,但是,无情的女王不会因为他奉献到这种程度,就给予他自由。
为获取更多的愉悦,她马上又命令男人开始行动。不得作任何抵抗的男人像奴隶般的驯服,再度奋起,叱咤激励自己的雄性。
静谧的雨天清晨,男人从幸福的绝顶,转瞬间沦为被罚做苦役的囚犯,为女人的快乐而献身。
尽管被命令“一直做别停下来”,但男人的性能力毕竟有限,不可能无止无休。
在雨天的早晨,在这个与世隔绝般的静寂的密室中,虽然更煽动情欲,但经过一个小时的奋力拼搏后,男人终于折戟沉沙般瘫在余热犹存的女人身上,垂头丧气地撤退了。
女人仍旧发出恋恋不舍的呻吟,但男人至此已到达极限。虽然没有遵守当初的约定,但女人已经多次得到了飞翔于云端般的满足,应该给予适当赏赐才对。
男人满怀期待地躺着,女人渐渐恢复平静后,靠了过来,一边抚摸着他的下体,一边问:
“你还没有吧?”
男人吓了一跳,但是关键部位被抓着,想逃也没处逃。“每次都那个,怎么行……”
如果每次都按照女人的要求,释放出来的话,男人的身体可就完蛋了。
直到最近久木才掌握了一些既能保护身体又可以持久的技巧。“我可说了的,我想要。”“不过,还是细水长流吧……”
就算没有释放出来,但每次都使女人攀上快乐的巅峰,男人的精气也会逐渐丧失掉的。“今天晚上不是还得干吗?”
凛子这才没话可说了。突然,又认真地说:“你觉得我是色情狂吧?”“没有啊……”“我都觉得自己讨厌,可是没办法,那是我真正的感觉。”
凛子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摸了摸久木那东西,问他:“你怎么能那么冷静啊?”
突然被这么一问,久木稍稍躲开了一点说:“这可不是冷静的问题。”“可是你能忍得住呀!”
“那也是拼命控制的,为了让你高兴……”“为了我……”
“为了让你真正满足呀!”“我也是,我也想让你快乐得要死。”
尽管男人和女人感觉上有差异,只要和相爱的人交合,就会使双方都感到快乐无比。“你想要我为你做什么,尽管说。”“这就足够了,没有女人能超过你了。”
“真这么想?”凛子叮问道。
其实这是不言自明的。久木不讨厌和女人做爱,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这么充实、深刻。
以前他所感觉到的只是一般男人的普通的快感,自从和凛子认识以后,愉悦的感觉一下子增强了,加深了,也更持久了。
在这个意义上,久木也受到了凛子的刺激、引导和大大的启发。“我绝不让你离开我。”
“我也是,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凛子柔和的声音消失在清晨的细雨中,久木听着轻轻闭上了眼睛。
两人半睡半醒地又躺了好长时间,十点多才起了床。“到这儿来就是不一样,感觉特别好……”凛子在镜子前面挽着头发,说道。
不错,涩谷的屋子他们太熟悉了,不免渐渐流于惰性。而今早的欢爱,使久木感到新鲜而有活力。“看来总是千篇一律的,就是不行。”
这不仅仅指变更场所,也适用于男女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永远保持新鲜的状态。”凛子道。
可是究竟能保持到什么时候呢?惰性这个怪物或许已经悄悄潜入他们之间了吧?“我先去冲澡了。”
凛子说完,便下楼去洗澡间了。久木打开了卧室的窗户。
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好像比昨天夜里小了一些。已经快十一点了,四周很安静,从树叶上滴落的雨点不断地渗入布满青苔的地面。
在这静寂的雨天里,久木想起今天是自己五十五岁的生日。
到了这个岁数过不过生日都无所谓了。说是喜事亦是喜事,说是悲哀便是悲哀。最惊讶的是,自己居然一转眼活到了这把年纪。
久木忽然想起了家人。
如果没有和凛子陷得这么深而离开家的话,妻子一定会对自己说一句“祝你生日快乐”,女儿也会打来电话表示问候的。
在久木漫无边际地想着的时候,楼下传来了凛子的声音:“早饭吃面包行吗?”
久木下了楼,冲了个澡,坐到了餐桌旁。
早饭是凛子做的,很简单,有香肠、煎鸡蛋和生菜,还有面包和咖啡。
吃完饭已经十二点了。
凛子很快收拾完,穿了一身天蓝色的套裙,准备出发。
以前久木在出版社的时候,经常到轻井泽来搞采访,最近几年没有机会来了。久木一到这里便触景生情,轻井泽也是使他回忆起过去工作在第一线的怀旧之地。
所以当凛子问他“咱们到哪儿去”的时候,久木很自然地想到了和文学相关的地方。
“据说这附近有个有岛武郎2绝命之处。”久木说道。
凛子查了一下地图。“墓碑在三笠饭店附近,他的别墅应该在盐泽湖岸边。”
别墅好找,他们先去那儿看了看,湖畔有一座古香古色的和式别墅。
导游图上说,别墅名叫“净月斋”,由于长年无人居住,已破烂不堪。当地的人士重新翻盖后,迁移到此处来的。
现在的位置在湖边显眼的地方,不过既然到了这儿,应该去看看原来的所在地。
他们又开车循着地图折回轻井泽老街来,沿三笠大街的林荫路往北去,街两旁都是落叶松。从前田乡向右一拐,出现了一片树木繁茂的坡地。顺着泥泞的羊肠小道穿过去,就看到了杂草丛中竖着一块长方形墓碑,依稀可以辨认出上面刻着“有岛武郎绝命之地”的字迹。
一九二三年,当时的文坛宠儿有岛武郎和《妇人公论》的漂亮女记者波多野秋子,曾在这个地方的别墅里一起殉情。
当时有岛武郎四十五岁,妻子已经去世,留下三个幼子。秋子三十岁,没有孩子,是个有夫之妇。
两人并排上吊而死。从六月上旬到七月上旬,梅雨季节的一个月之久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被人发现。被发现时,两人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了。
发现尸体的人说:“他们全身都生了蛆,就好像从顶棚上流下来的两条蛆虫瀑布。”
有岛武郎和波多野秋子的情死事件,成为震撼当时文坛乃至整个社会的华丽丑闻。然而,当时他们的样子是相当凄惨的。
凛子听久木描述的那样,他们被发现时已全身腐烂生了蛆。她害怕地望了望四周,然后向石碑合十为他们祈祷。
在这大白天都觉得阴暗的灌木丛中淋着雨,真好像随时会被带到死亡的世界中去似的。“这回我带你去一个我喜欢的地方。”
凛子开着车沿三笠大街往南去,一进入鹿岛森林边上的小路,就看到一个池塘。这就是云场池,池塘不太大,呈狭长形状。“这个地方下雨也很有情趣的。”
正如凛子所说,茂密的树林环绕的水池,笼罩在雾蒙蒙的水汽里,就像暗沼一样飘散着妖气。“你看,那儿有一只白天鹅。”
顺着凛子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水面上漂浮着几只鸭子,其中有一只白天鹅。
“它老是单独待在这儿,不知道是为什么。”
凛子担心它没有伴儿,太孤单了,而白天鹅若无其事地浮在水面上,像雕塑一样。“也许它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孤独。”
久木给凛子打上伞,沿着池边继续往里走。
雨势虽小,却没有停的意思。除了他们,这静寂的池塘边一个人影也见不到。
路越来越泥泞难走,两人只好半路返回,到湖边一个餐厅去喝咖啡。“死了一个多月才被人发现,也太可怜了。”
凛子还在想着武郎和秋子情死的事。“那么长时间,就那么吊在空无一人的别墅里。”“大概谁也没想到他们会去别墅吧。”“就算两人一起死也不该选择上吊啊。”凛子望着烟雨蒙蒙的沼泽说道。
晚上久木和凛子在离别墅不远的饭店吃了晚饭。这是轻井泽一家历史悠久的饭店,白色的二层楼建筑,正面有一排木栅栏,与周围的绿树十分和谐,有着避暑地饭店所特有的闲静气氛。
天刚刚擦黑,两人面对面坐在看得见庭院的窗边。凛子穿着薄薄的真丝上衣,下着一条白色休闲裤,这身轻松的打扮,一看就是来避暑的。
凛子先提议要瓶香槟酒。服务生给他们的杯子里注入了琥珀色的液体后,凛子先拿起酒杯,和久木碰了一下杯。“祝你生日快乐。”
久木一怔,赶紧笑着点点头,说道:“你没忘?”“当然啦,你以为我给忘了?”
今天早上,久木想起了自己的生日,见凛子什么也没说,以为她没想起来。
“谢谢,没想到在这儿,有你为我庆祝生日。”“从东京出发的时候,我就想到了。”
这回久木又一次举杯,向凛子表示谢意。“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凛子说着从坤包里拿出一个小纸包,“给你,生日礼物。”
久木撕开包装纸,里面是个小黑盒,打开一看,是个白金戒指。“不知道合不合你的意,我想让你戴上。”
久木往左手的无名指上一戴,不大不小正合适。“我知道你手指的粗细,定做了一对儿。”
凛子说着伸出左手给他看,无名指上也戴着个一模一样的戒指。“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必须老戴着它。”
久木第一次戴戒指,有点不好意思,可又不敢不戴这么宝贵的礼物。
晚餐都是单点的。凛子点了沙拉和清炖肉汤,主菜是法式油煎虹鳟。
久木点了金枪鱼和西餐汤,主菜是香草烤小羊排。
喝了几杯香槟后,又要了瓶红葡萄酒,凛子的脸上起了红晕。“本想给你订个生日蛋糕,可是觉得这种场合不大合适。”
当着其他客人的面,是有点太张扬了。“我这岁数,吹灭五十五根蜡烛,要我的老命呢。”“你挺年轻的,一点都不显老。”“你是说,哪方面?”久木压低声音说。
凛子缩了一下脖子说:“别瞎说。”
凛子接着又说:“那是当然,你的头脑也比那些男人们灵活得多。”“多亏了你呀。”
“从一开始我就对你这点印象很深。比那个衣川有活力得多,又有幽默感……”
虽说受到了夸赞,但说显得年轻,久木觉得也没什么可高兴的。
“以前我采访过一位八十八岁的实业家。当时他对我感叹过,光长岁数,心情总也不见老,真是头痛。我现在好像能体会到了。”“总是显得年轻不好吗?”“不是不好,他的意思是光心理年轻,身体跟不上去这种难受的感觉。
倒不如心情也和年龄一样的衰老好受一点。”“那不就成了没用的人了吗?”“其实我现在在公司里也是没用的人。”久木用一种自嘲的语气说道。“那只是公司不用你,不是你的问题呀。这和在公司的地位没什么关系呀。”凛子鼓励道。
可是在公司里的地位会对男人的精神面貌产生微妙的影响。久木尽量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不过谁能保证以后会不会产生失落感呢?
久木品着葡萄酒,心情开朗起来,也感到肚子有点饿了。
久木觉得凛子点的虹鳟看着很好吃,分了一点来尝,又给凛子的盘子里放了一块自己的烤小羊排。“两个人能多吃几种,真不错。”“并不是谁都可以的吧?”“那当然,只有和你才行。”
男人和女人分着吃东西,是有肉体关系的证据。在这个餐厅里,也许就有人这么看他们,但现在的久木无心去遮遮掩掩了。
以前就连和凛子坐车去镰仓,都担心周围人的视线,现在完全没有了那种不安,被人看不看到全无所谓了。
事到如今还在乎别人的看法毫无意义。应该珍惜所剩无多的人生,做自己想做的事,实在不行的话就是死也无所谓。
久木心里渐渐萌生了一种满不在乎的想法,更确切地说,是某种决心或坚忍的意志。
人一旦改变了价值观,对生活的态度就会随之改变。以前觉得重要的东西不再那么重要了,觉得无聊的东西反而宝贵起来了。“我也该考虑退休了吧。”
久木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平时常常思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