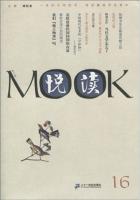robwooooo
一
好久没有这样了,摊开一张纸,想下笔却觉得笔头万分沉重,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被什么堵住了喉咙,其实之前,我几次都想动笔,却最终选择了这样一个对于北京来说很少见的下午——窗外飘着毛毛细雨,阴阴的天空,柔柔的雨声,湿湿的空气,这一切让我与她更近了,不论是心里的感觉还是外部的氛围——对于故乡,一个南方的小山城,绵绵阴雨的天气是极常见的。
在这样一个下午,我只想静悄悄的让时间往回倒流二三百年,去体味一段让我心动的历史,去聆听一声已渐消散的余韵,去捕捉一点暗淡逝去的星光。这,皆是因为我对那片土地爱得深沉。
群山环绕着几个小城,小盆地里沟渠密布,气候湿润,物产丰饶,民风淳朴。从外表看,这只是南方一个普通的山区,可在二三百年前,她却有一个在全国都响当当的名字——徽州。“欲识金锒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对徽州的赞叹,已让我依稀见到了故乡昨日的辉煌。而让故乡如此名震天下的则正是她养育的儿女——一支叫做徽商的强大商帮。
随手翻开明清的历史,随处可见关于徽州和徽商鼎盛富庶的记载。徽商自宋代以后逐渐形成,明清达至鼎盛,其经营活动前后绵延千载,主商界四百年,影响所及,“几遍宇内”。“无徽不成镇”即是徽商的写照……这简短的一段文字已经让我心潮澎湃,是啊,先人的业绩岂是我们这些儿孙所能评点,先人的荣耀又岂是我们这些儿孙所能想象。只是,两个世纪之后,当年的“无梦到徽州”对于我们,已经成了一场正在逝去的遥远的梦,我不愿让她永远就此尘封于历史的记忆中,因为我们还需要梦想,而重温旧梦,或许才能重新找回梦想。余秋雨先生在他的名作《怀愧山西》中说“本来徽商也是一只十分强大的商业力量,完全可与山西商人南北抗衡(由此我想到对安徽也一直有误会,把它看成是南方的贫困省份。荣以后有机会专门说说安徽的事)”,但直到今天,我仍未能读到他关于徽商的文字,我已等不及,只怕愿望拖得太旧也会成为一个梦。余先生描写晋商是出于他对山西现状与历史对比反差强烈的惊诧,而我,已顾不得在内心深处是否有着相同的情愫,也顾不得自己的才疏学浅,急匆匆地,怯生生地,准备提起笔,回顾过去的几百年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的一群神奇的人物,缔造的神奇的传说,以给自己留一个神奇的梦想。
二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并在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
徽商的强大,首先体现他涉足行业多,活动范围广。在明朝成化以前,徽商以经营“文房四宝”、漆、木、茶和稻谷为主;成化以后,经商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涉足的行业多种多样。从商业资本流向和从业人数看,盐、典当、茶叶、木器业为最著,其次是米、棉等,也有徽商从业于珠宝、古玩和人参等行业。徽商商德有八字真经:“货真”“价实”“量足”“守信”。在这种经营理念的主导下,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自明朝中叶到清朝中叶,徽商保持了三四百年的鼎盛辉煌时期。
徽商的商业资本十分雄厚,当时无论是哪一个商帮,都认为“富室称雄”者非徽商莫属。在宋朝在徽商中像“程十万”、“祝半州”的大贾,在明朝以前还是少数,而到了明清时期,这样的富商大贾则已经不足为奇了。当时的徽商许某,经营40余家当铺,雇工2000余人。后因故解散经营的当铺,发给雇工的遣散费平均每人1500两银子。在当时,拥有二三十万两银子的商人只能算是“小贾”。在清朝乾隆和嘉庆年间,徽商共向朝廷捐银2640万两(7次)。如果算上其他地方各种数目的捐银,数目非常巨大。乾隆年代,仅扬州盐业的徽商资本就达四五千万两,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徽商中的传奇人物胡雪岩最有钱时,其“阜康钱庄”在全国各地有20多处分支,资金达2000万两白银,拥有田地上万亩。这在当时意味着,清廷近三分之一的国力是在一位“红顶商人”的操控之下。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乾隆末,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大宗出口商品当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大商人江春、鲍蔌芳、胡天注、汪定贵、胡雪岩、程量越等名震南北,雄踞一方。
徽商的兴起,带动了很多城市的繁荣,正有前文“无徽不成镇”之说。现代学者曹聚仁说:“扬州成为世界城市,有一千五百年光辉的历史,比之巴黎、伦敦更早。它是我们艺术文化集大成的所在,比之希腊、罗马而无愧色。”支撑扬州繁华的基础是什么,是盐务和漕运,而这两项业务基本都由徽商垄断,“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直到现在,扬州的说书人还有“这扬州城原是徽州殖民地”的说辞,扬州人以自己祖籍徽州而引以为荣。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也曾“舟楫停阜,望之隐约城郭”。徽州大学者胡适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
三
然而,正是这执中国商界四百年牛耳,造就了中国一代商业史和经济史辉煌的徽商,其发源地——徽州,却是一个交通不便,偏居皖南山区一隅,面积不过一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充其量几十万的“角落之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一直在想象第一批徽州人从家乡的大山里走出,开始贩运第一批货物时是怎样一种情形,怎样一种心情,肯定没有乡里乡邻热情的欢送,肯定没有闯出一片天地的豪情壮志,也许只是几个毛头小伙,揣着一点干粮,衣衫褴褛的上路了——其实更应该是踏上一只简陋的竹排,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活下去,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一走能否回得了故乡,想再回头看一眼那清秀的山儿,清秀的水儿,清秀的人儿,无奈拂晓的霏霏细雨让眼前的故乡也是如此亦真亦幻,朦胧,阴郁,一如前方的路途。从这时开始,故乡已经成了他们的一个梦。
据史料记载,隋唐时期,由于北方的年年战乱,北方人口大量迁入战祸较少而景色宜人的徽州,致使原本就山水萦回,土瘠地狭,人口稠密的徽州到了农业不足以为生的地步,迫于人口的压力,大批徽州人不能安于本土而只能游走他乡谋生,“非经营四方绝无生治策”,于是“天下之民寄命於农,徽民寄命於商”。记得我上小学时就会背我们那一首很古老的民谣:“前世不休,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少小离家老大回”,寻找几十年不见的亲人的感人例子不胜枚举。同时,徽州本土有可供交换的独特而丰富的资源,木材、茶叶、陶土、墨、砚等等,为徽州人经商提供了便利。非常幸运的,徽州的山是封闭的,徽州的水却是开放的。主流新安江与率水、横江、练江相接直通杭州,秋浦河、清弋江等流入长江,婺水等流入鄱阳湖,这种发达的水系为徽州人的向外流动和货物运输提供了舟楫便利,将大山丛中的徽州同外部世界开放性地连接起来。山的封闭狭隘迫使徽州人走上一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求生之路,水的开放畅达却使徽州人的经商之路变得畅通无阻,最终使徽州的先民们义无返顾地走上漫漫天涯路。
徽商有着一个不同于其他商帮的鲜明特征:儒贾结合,官贾结合,这是研究徽商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先说徽商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传统。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珠算大师程大位兼商人学者于一身,他的学术成果流传海外。巨商鲍廷博经商不忘习儒,终成大藏书家,他获举人头衔时,已年逾八旬。历史上,徽商教子习儒,参加科举,十分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由于其资财雄厚,见多识广,平时督促子弟攻读儒家经典和诗文,一俟学成,即鼓励他们参加科举,跻身仕途。婺源人李大祈,早年学习诗文,后弃儒就贾,经营盐业,往返于淮、扬、荆、楚之间,腰包日渐隆起。可是,他每每想起少年学业未成,不免失落,于是掏钱办私塾,拜请名师教读,自己也每日督促,直至公子中举,才算了却心事。
徽州是程颐和朱熹的故乡,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有“东南邹鲁”之称。徽商重视教育,自古至今已成为习俗,纳入其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自古以来形成的重视教育的风气不仅造就了一大批缙绅官僚,也为徽商造就了大量具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商业人才,从而提高了徽商集团的文化品位和徽州人的整体素质。徽州人文化底蕴深厚,“富而教不可缓”是徽商笃信的信条,正是如此才“代不乏人”,使徽商几百年不衰,造就了一代徽商帝国。
他们在“振兴文教”上总是毫不吝惜地输金资助。为了让更多的子弟习儒就学,徽商积极捐资,广建书院。明清时期,“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在清初时,徽州书院多达54所。有的家族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的子弟,无力从师者,必须给予资助,并将此列入家典,世世遵行。徽州在这种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风气下,出现了大量人才。清代各省状元人数,安徽居第三位,有九人。安徽八府五州中徽州一府便占四人。黟县西递村在清道光年间,仅胡氏一族进入仕途者就有115人,廪生、贡生、监生共298人,可谓显赫一时。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徽州人中进士542人,举人多达1513人。“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父子宰相”,“四世一品”者并不鲜见。这样的沃土中还诞生了一代睿智的货币改革家——王茂荫,他是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徽商中以“业儒”出身者居多,由于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大都善于审时度势,决定取予,运以心计,精于筹算。这是徽州异于其他商帮之处,也是徽商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徽商和官场扯上关系,开始只是为了抵御各种恶势力的侵犯。歙商汪士明面对矿监税使的榨取,感慨地说:“吾辈守钱虏,不能为官家共缓急,故掾也鱼肉之。与其以是填掾之壑,孰若为太仓增粒米乎!”。他“应诏输粟实边过当”,被“授中书舍人”,社会地位大增,官吏也不敢“鱼肉”了。尝到权力的甜头进一步加深了徽商对官场和权术的迷恋。明清时期实儒商看重“利”,但同时也看重“义”、看重“名”。这种形态的商人,很符合中国传统的观念,本身客观上与封建社会易于融合,加之主观上利用各种手段寻求政治势力的庇护,便与封建统治势力结成了极紧密的联系。徽商利用金钱结交各级封建官员。“官以商之富而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而豢之,在京之缙绅,过往之名士,无不结纳,甚至联姻阁臣,排抑言路,占取鼎甲,凡力之能致此者,皆以贿之”。江春任总商40年,通过金钱和学识竟“以布衣交天子”。乾隆“御宇”50年,他送礼100万两;乾隆南巡扬州,“赐宴加级”,并“钦赏布政使秩”衔。徽商投资教育,造就了一大批徽籍官员。他们成为徽商的政治代言人。徽商世家出身的许承宣官工科掌印给事中时,“扬州五塘关政滋弊,承宣谓此关外之关,税外之税也。慷慨力陈,一方赖之”。官贾结合后,徽商获得了垄断商品的经营特权,诸如“漕运”“盐运”等“官商”“皇商”的美差,都牢牢掌握在徽商集团的手中,赚取了数倍甚至数十倍的高额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