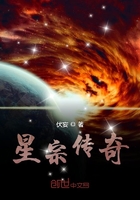摸着下巴:“况且,施此法,还需一僧一道一法师,均要精通命理,还需八字与她相合,与她有益方有可能施行转世重生之术……”
最后,脸露微笑,竟是一派神往之色:“虽然几乎不可能,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这转世重生之术,还真让他们办到了!也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惜哉妙哉,壮哉悲哉!”
“哎呀!贫僧生不逢时,不能亲眼得见此一壮举,实为生平憾事啊……”无言扼腕。
可他这边手舞足蹈,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萧绝只如泥朔木雕。
满脑子里只嗡嗡地响着一句话:她是皇后,二十五岁殁,育有一子,夭折……
“世子爷,非是贫僧不肯帮你。”无言说得口干舌燥,终于想起房里还有一人:“重生之后并非万事大吉,稍有行差踏错,便会香消玉殒。你看,二小姐的命盘里,处处凶险,危机四伏,说是命悬一线也不为过。贫僧劝世子爷还是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为好。”
萧绝一言不发,如灵魂出窍般越过他,飘然隐入夜空。
他不相信,阿蘅怎么可能是半人半鬼的重生之人?
眼前莫名地闪现出静安寺佛堂里,与顾氏灵位并排的无字小牌位。
他机灵灵打了个寒颤,刹那间如坠冰窖,手脚冰凉……
何婶等到天黑,也不见人来传饭,心中奇怪,打发了小丫头过来问:“这都什么时辰了,怎么还不摆饭?”
紫苏道:“小姐已经歇了,吩咐灶上不能熄火,饭菜随时热着。另外,让我娘再熬些白粥。”
“不用这么麻烦,摆饭吧。”杜蘅在屋里搭腔。
几个丫头皆是一怔,面面相觑了一会。
紫苏忙搁下手中针线,掀了帘子进去,见她除了眼皮略有些红肿,神色如常,越发心中揪得生疼,颇有些恨铁不成钢地埋怨:“这个时候,小姐还顾着体恤下人!若不是为随时有口热汤热饭吃,何必另备个小厨房?”
杜蘅哧地一笑:“怕别人不敬你这大丫头,也不必拿自家亲娘立威吧?”
紫苏很是伤心:“在我面前小姐也要演戏不成?明明心里不痛快……”
杜蘅微微一笑,道:“我有什么不痛快?不过是太阳底下晒久了,有些乏。”
“我,我去打水来。”紫苏叹了口气,认命地道。
白蔹早准备妥当,这时便撩了帘子进来伺候她梳洗了,那边饭菜也摆上来。
杜蘅胃口大开,破天荒添了半碗饭,笑:“何婶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这酱肘子做得真是好吃得不得了!可惜初……”
说到这,忽地语声一顿,眼神微黯,低了头扒饭再不做声了。
白蔹心知她必是想起了初七,再想到以后初七只怕再也不会来了,忍不住眼眶泛红,又怕她瞧见了添堵,快步出了饭厅躲在门外偷偷抹泪。
几个丫头见了,更是心中警惕,连走路都蹑手蹑脚,一点声音也不敢发出。
饭后,杜蘅便吩咐请聂宇平到花厅,劈头就道:“你帮我办件事……”
聂宇平越听越是诧异。
他是个谨慎而精细的人,萧绝来群房这么一闹,立刻便派人去调查了一遍,发现南宫宸去过大相国寺且曾与无言匆匆一晤。
但这并不能证明事情与南宫宸有关,尚没决定要不要禀报,杜蘅这里却来了这么个任务。
便想当然地以为办事的人嘴碎,越过自己直接先禀了她。
杜蘅恨南宫宸坏她姻缘,这才要挟私报复。
倘若对方是其他人倒也罢了,偏生是燕王,一旦消息走漏,后果不堪设想。
想了想,委婉劝道:“好事多磨,大小姐只管安心待嫁,一切自有七爷。”
杜蘅神情冷淡:“若先生认为我不够资格支使你,随时可以另谋高就,我不强留。”
一句话,将聂宇平堵得哑口无言。
半晌,讪讪道:“聂某受老爷子遗命,自该肝脑涂地,誓死追随大小姐。岂有中途改弦更张,一走了之之理?”
“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先生留下来只为报答外祖的恩慧,而不是真心为我办事,倚老卖老,质疑甚至妄想左右我的决定,不如乘早离开。”杜蘅盯着他,目光冷凝,话锋冰冷如刀:“我,不养无用之人。”
聂宇平额上淌汗,单膝跪地:“大小姐教训得是,聂某僭越了!”
“请先生记住今日之言,倘有再犯,休怪我无情!”杜蘅冷眼看着他,声音冷凝凝的,教人不敢轻忽。
“是。”
杜蘅便端了茶杯。
聂宇平起身,恭敬地施了一礼,匆匆出去布置。
杜蘅回了屋里,却吩咐紫苏开了箱子,左挑后选,最后挑了匹石青的暗纹宝相花的云罗出来,拿到东梢间,裁起了衣服。
瞧了尺寸,大家便都知道果然是替萧绝裁的,白前几个悄悄松了口气,七嘴八舌地讨论起京中流行的男装样式。各人争执不下,竟弄出了四五个样式来。
杜蘅也不恼,含了笑聆听,一副饶有兴趣的模样。
唯有紫苏,明白经无言这番预测后,她与萧绝算是走到头了,这样做分明是为了尽早与萧绝划清界限,心里酸楚难过,又不敢在脸上带出来,坏了大家的兴致。
萧绝从相国寺出来,再进到杨柳院,见到的就是这么一副其乐融融的场景。
隔着窗子,看她温婉微笑的模样,开始怀疑今日经历的不过是一场梦境……
不,他才不会上当!
一定是无言那贼秃,为了推卸责任,想出来这种荒谬的理由,用几句胡编乱造的所谓命理,就想蒙混过关。
可是,不管他如何说服自己,无言那段话却如梦靥般在脑海里回荡,挥之不去!
他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要相信无言那贼秃的胡言乱语,却又总也忍不住要去揣测,前一世她到底嫁了谁?
如果她二十五就殁了,那就只有二个可能――要么就是太康帝驾崩,她嫁了新皇;要么,她嫁了太康帝?
想着太康帝的年纪都已经可以做她的祖父了,他机灵灵打了个寒颤,马上把这个结论推翻。
那就只剩一下可能,她嫁了新皇。
新的问题又来了――几位皇子中,到底是谁登了基?
几乎是立刻,他想到了南宫宸。
想起了金蕊宴南宫宸对她的轻薄,阿蘅的愤怒和激烈的反应;想起明明是毫无交集的两个人,却总会莫名其妙地纠葛在一起;想起每当阿蘅与他在一起时,几乎是本能地散发出来的强烈排斥和隐隐的敌意……
那些往日不曾留意的小事,那些看似细微的变化,一下子如雨后春笋似地冒出来,曾经以为的偶然,今日怎么想怎么不舒服,再无法释怀!
比如,自顾氏葬礼之后,她做出的一系列漂亮的举措,干净利落的拔除了身边的钉子,架空柳氏,夺回家产……
虽然不能否认他做了帮凶,但主要出自她的授意,而他其实只想看看她到底想做什么,以及可以做到什么地步?结果,她令他眼前一亮的同时,成功地挑起了他对她的兴趣。
再比如,之前他总觉得阿蘅和南宫宸聚到一起,气氛很是诡异,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因此莫名地很是不快……
仔细想想才发觉,是因为阿蘅的态度。
她很会伪装自己,平静和坦然是她最常用的面具。
可只要面对南宫宸,她就会变得尖锐和易怒。
当然,现在的她变得越来越从容,已轻易不会在任何人面前失态。
但这不能解释,她对南宫宸那种莫名的熟悉和透彻的了解――似乎,总是能先一步预测到他的行动,有目的地进行布置,有针对地进行打击。
京中遍地都是神机营的密探,任何人想兴风做浪,都逃不过他的耳目。
既使不是有心刺探,聂宇平背后搞的那些小动作,自然瞒不过他。
可是,做出这样大的举动,事前竟然不通知他――不必问,定然是阿蘅授意。
她,竟这么快就开始与他划清界限。
胸口象压了块巨石,心里憋着一股气,照他往日的脾气,早就不顾一切地冲进杨柳院,找她问个明白!
可他却提不起勇气。
直到这一刻,才发现自己漫不经心的表象下竟然隐藏着一个胆小而又极度缺乏自信的自己!
曾经以为他已强大到足可睥睨一切!
天下再无任何人任何事可以令他畏惧,如今却在一座小小的院落前却步,被一个柔弱的女子击败!
他害怕无言所说的一切变成事实;害怕她会承认,她真正爱的是那个宁可舍弃了江山也要为她转世重生的男人!更害怕伴随着真相而来的,不得不面对的分手的结局。
如果不是心底早已驻着一个人,阿蘅又怎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他?
他自问已拿出了十分的耐心,百分的诚意,以及千分的真情,她始终坚定如磐石,毫不动摇!
之前还可以骗自己她是因为与夏风有婚约在身,可如今她恢复自由身已经大半年了,为什么还是不肯点头?
唯一的解释:她心里有人,她深爱着她前世的丈夫!
到底是怎样的爱,让她对他如此死心塌地,转世重生依然无法忘情?
虽然她表现出来的是强烈的恨――可是,若无爱,又哪来的恨?
现在才深刻地体会到,爱情果然是面双刃剑。
带给过他多少欢乐,就会带给他多少痛苦,曾经的甜蜜全都化为了苦涩!
曾经最痛恨拖泥带水的他,竟象个白痴似的变得患得患失!
萧绝喝得酩酊大醉,魅影怕萧乾责备,索性将他扛回了阅微堂。只派人送了封信回王府,说他最近有要事要处理,暂时得在外面住些日子。
知子莫若母,穆王妃知他必是为了杜蘅之事闹起了别扭。
她心里担忧着,又不敢将实话告诉萧乾,碾转了一夜,天不亮就起了床,略事梳洗了一番,急匆匆赶到阅微堂。
推开门的刹那,如同被施了定身法,僵在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