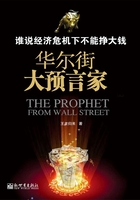张妈气得直翻白眼,用力一推:“走开!”
杜蘅使个眼色:“你出去做事吧。”
紫苏佯做愁眉苦脸地出了门:“我,我真不是故意的……”
张妈再也忍不住,大声抱怨:“也不知老太太怎么想的!给小姐选这么几个小丫头来!毛都没长齐,能做什么?”
杜蘅脸一沉:“张妈是在指责祖母吗?”
张妈发现失言,顿时尴尬起来:“我哪敢说老太太的不是?不过心疼小姐身边没个得力的人侍候罢了。”
杜蘅淡淡道:“规矩可以学,年纪小,学东西反倒快。”
张妈偷瞧她的脸色,半是抱怨,半是试探:“这个紫苏,性子野不说,做事又鲁莽,怕是难成大器!今儿幸亏是我,要换了别人,不知还要惹什么祸来!不知怎么入了小姐的眼……”
杜蘅笑道:“不知怎地,我一见紫苏,就觉得亲切。刚刚一问,才知她跟紫苑竟是沾了点亲。你瞧着,两人是不是有点象?”
张妈疑心尽去,撇了嘴道:“要我说,不如求下柳姨娘,把萱草和茜草讨过来……”
杜蘅睨了她一眼:“张妈可是得了萱草,茜草什么好处?”
张妈的脸,腾地一下涨得通红:“这是什么话?”
杜蘅打断她:“萱草,茜草都比我大,三年后我才出嫁,正是用人的时候,她们却到了该放出去的年纪。这几个小的,却正好得用。”
张妈张了张嘴,一时无话可驳,只好悻悻地出门。
隔天,郑妈妈果然又送了三个小丫头来,都是京中各个田庄上找来的家生子,年纪都在十二三岁。
杜蘅一并改了名,全都提做二等丫头,都交给紫苏管着。
张妈在一旁暗暗观察了两天,见紫苏年纪虽小,竟是颇有主见,做起事来更是有板有眼,教训起丫头,有模有样,府里的规章条程张嘴就来,比她还熟。
那几个小丫头,起初心中不服,再给她几句言词一挑唆,便有些跃跃欲试。
哪知两天下来,一个个给她治得服服帖帖,见了她比见小姐还怕,大气也不敢喘!
张妈越想越觉得可疑,终于憋不住,寻了个借口,出了门。
紫苏推门而入,轻声道:“张妈出了门,要不要派小丫头盯着?”
杜蘅淡淡道:“小丫头们还要再敲打敲打,先不忙着派出去做事。”
“可她成天在小姐眼前晃,让人看了就想狠揍一顿!”
“昨天那几脚,还没过够瘾?”杜蘅忍不住取笑。
“比起她做的那些缺德事,踢几脚哪里能解恨?说是利息,都算便宜她了!”紫苏握拳,做张牙舞爪状。
杜蘅轻笑:“张妈只是个小角色,等着吧,不用我们出手,自有人会收拾她。”
紫苏正要追问,忽听门外白前一路惊嚷着,咋咋乎乎地跑了过来:“出事了,出大事了……”
紫苏把帘一掀,眉一竖:“慌什么!”
白前猛地煞住脚,小脸涨得通红:“小姐,白前有事回禀。”
“进来。”杜蘅强忍了笑。
白前进了门,先规规矩矩给杜蘅行了一礼:“小姐,老爷回府了。”
偷瞄一眼紫苏的脸色,见她并无斥责阻止之意,这才大着胆子继续道:“听说,老爷怒冲冲地进了杨柳院,闹着要休掉柳姨娘呢。”
“老爷因何事发怒?”杜蘅吃了一惊,问。
白前口齿伶俐,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原来,昨日杜谦下值回府,见几个痞子模样的男子围在府前,吵着要见柳氏,见了他便一哄而散。今日回府,那几人又在门口闹事,还嚷着要柳氏交人。说什么大活人给她叫走,如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要讨个公道云云……
杜谦起了疑,找柳氏追问,两人吵了起来。
白前本是去厨房拿点心,远远瞧到杜谦怒冲冲的往杨柳院,便多了个心眼,悄悄跟过去,听了个大概。
“做得好。”杜蘅示意紫苏拿了五百钱,赏给白前。
白前得了赏,欢欢喜喜地走了。
紫苏按捺不住兴奋之情:“听到没有,柳氏要被休了!”
这实在,大大超过她们的预期。
杜蘅却极平静:“别高兴得太早,要这么容易就被扳倒,她就不是柳氏了!”
“咱们该怎么做?”
“这么好的戏文,只我一个看,未免可惜了。”杜蘅微微一笑。
如果不闹到老太太面前,以柳氏的能耐和杜谦的性格,这件事一定会悄无声息地掩盖住。
她,可不打算让柳氏如愿。
紫苏心领神会,叫来白前,附耳低语几句,白前眉眼弯弯,一溜烟地跑出去。
杜蘅带着紫苏进到瑞草堂,老太太歪在炕上小憩,福儿立在一旁打着扇。
锦绣一脸歉然,以嘴型示意她过会再来。
杜蘅笑了笑,也不吭声,接过福儿手中的扇子,闷声不响地打起了扇。
老太太象是有所感应,睁开眼见了她,微微一怔:“蘅丫头来了?”
“祖母可是夜里睡得不好?”杜蘅一脸关切。
老太太自嘲一笑:“最近常觉头晕目眩,神疲乏力,夜里醒来好几次,白天便时常感到精神不济,经常要打个小盹。怕是死期将至罗……”
杜蘅二指搭上她的脉门,笑道:“祖母才五十出头,哪里就说得上老?您只是近段时间劳心伤神,略有些气虚血亏。回头我给您开个方子,饮食上再稍加调理,必可恢复如常。”
老太太眼中闪过讶异,很快掩去,嘴里嗔道:“什么五十出头?明后年就六十了,一只脚踏进棺材里的人了,有点小毛病不算啥,何必浪费银子。”
顾老太爷终归还是留了一手,一个府里住着,竟不知她几时习了医术?
“别总歪着,容易犯悃。”杜蘅想了想,道:“我来时,瞧见园子里绣球花开得挺热闹,不如我们去摘几枝插瓶?”
“打发丫头去剪几枝就是,何必走这一趟?”
杜蘅不由分说,拖了老太太就走:“祖母,你就行行好,陪我去嘛……”
老太太半推半就,跟着她进了花园。
此时正值五月,花开如海,缤纷如画。
杜蘅挽着老太太的胳膊,一边赏花,一边说几句逗趣的话,惹得老太太不时会心一笑。
“呀,你听说没有?今日老爷回府时,有几个男子在大门外闹事呢!”隔着低矮的花墙,传来刻意压低的声音。
“切,”另一个满是不屑:“这几日街上几个混混天天来闹,就只差上房揭瓦了,你才知道?”
另一个大吃一惊:“我怎么听说,是柳姨娘打死了人,人家的兄弟上门来讨公道……”
杜蘅和老太太都是一惊,猛地顿住脚步。
郑妈妈心知要糟,忙提高了声音大喝:“什么人?不要命了,在这里混说?”
两个小丫头跳起来就跑,转眼没入花海。
老太太气得眼前发黑,颤了手喝道:“把人捉来!”
锦屏急忙追了过去。
可等她绕过短墙,却只见一片花草摇曳,哪里还有半个人影?
“祖母,”杜蘅扶着老太太的肘:“丫头们闲着没事,在这胡说八道,你可千万别当真。”
老太太面沉如水:“走,去杨柳院!”
一个十来岁的小丫头守在路口,远远见老太太一行人过来,扭头就朝院子里跑。
“反了!”老太太气得直打颤。
杜蘅心中有数,柔声劝道:“祖母不必恼,气坏了身子不值当。”
“站住,不许跑!”锦绣大喝一声,却哪里叫得住,反而跑得更快了。
哪知刚拐过弯,便听噗通一声响,接着便是“哎哟”一声叫。
锦屏追过去一瞧,不由又气又笑。
那小丫头摔在路中,抱着膝盖哀哀直叫。
老太太有了防备,命几个粗使的婆子打头阵,见了通风报信的,不由分说堵了嘴绑起来。
就这样,一路畅行无阻,到了主屋。
屋子是粉刷一新的,三间明晃晃的大瓦房,正中是客厅,西梢间做了卧室,东梢间布置成了书房的模样――显然,这是为了方便杜谦使用所设。
左右各有三间厢房,抱厦两边各设了两间耳房,就连后面的倒座厅都收拾了出来,做了库房。
这哪里是姨娘的居所,分明是按照正室的规格设计的!
杜蘅心中冰浸火焚,面上不动声色,搀着老太太缓缓踏入客厅。
厅里一个人也没有,地上满是零落的花瓣,流淌的污水,半人高的青花瓷美人耸肩大花瓶,横倒在地,满地都是碎瓷。
就连淡绿色的湘妃竹帘也被扯落下来,斜斜的挂在隔窗上,望去,一片狼籍!
“哭!做出这样的丑事,还有脸哭!”杜谦的怒吼声清晰入耳。
柳氏的低泣隐隐约约传来:“老爷……”
郑妈妈心中一紧,下意识地便住了脚。
锦锈,锦屏,紫苏也是伶俐的,谁也不敢跟入,都留在了院中。
杜谦在房里不停地踱步,显见胸中怒火尚未平息:“平时在府里嚣张跋扈,独断专行也就算了!如今竟然发展到买凶伤人,坏人贞节的地步!”
柳氏跪在地上,涕泪交流:“老爷怎能听那几个泼皮的一面之词,断定妾身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冤枉啊!妾身只是个深宅妇人,哪有什么机会去认识那些混混泼皮?这必是有人存心陷害,请老爷明察!”
“还敢喊冤!”杜谦骂道:“你敢不敢拿松儿的命起誓,说那日禅院进贼之事,真与你无关?”
杜松是她的心头肉,更是她在杜府立身的法宝,如何敢用他的命起誓?
柳氏一窒,一时竟无话可驳。
“贱妇!”杜谦本来抱着一丝的希翼,见此情形,心中一凉,手起掌落,啪地扇了她一记耳光:“你好大的胆子!竟然……真敢对蘅儿下手!你,你这个毒妇……”
老太太身子一晃,向后就倒。
“祖母!”杜蘅惊叫一声,忙用力抱住了她。
“我不碍事,别慌。”老太太稳住身形,缓缓推开杜蘅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