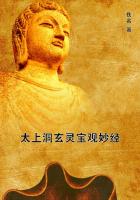她也不过是个厨娘的女儿,命好才被选来伺候小姐,也不过将将一年,就染了一身富贵气了?
紫苏涨红脸,讷讷道:“后来不是病得狠了么?”
白前更奇怪了:“眼瞅着要没气了,谁还花那个冤枉钱?”
紫苏很是狼狈:“只是觉得那孩子可怜。”
白前不以为然:“这年头,谁家没死过几个孩子?我娘先后生了七个,最后只剩我们兄妹三人。”
穷人的命,本就是天种天收,能活下来的多少要靠几分运气。
能够遇到杜蘅这样的主子,简直是鸿运当头,吉星高照了!
“尸体呢?”紫苏还是没能忍住。
白前看她的眼神,已经象在看怪物:“自然是草席一卷,往乱葬岗一扔了事。”
夭折的孩子,谁家不是这么处事,难不成还奢望给他一副棺材不成?
“啊,这如何使得,怎么不埋了!”紫苏惊呼。
这下不止白前奇怪,白蔹几个也都面露讶色。
“姐姐,你没病吧?”白前更是直言不讳。
“嘿嘿……”紫苏干笑两声。
“别人家的事我管不着,你们几个以后家里有人病了,一定要及时请医用药,千万别延误了。缺银子,到我这里拿。”杜蘅不动声色地把话题岔了开去。
“小姐真是菩萨心肠。”白前几个都很感激。
紫苏悄悄松了口气,心里却越发确定时疫将至,转过身去不声不响地在杜府的大门和角门处,又各设了个熏药房。
订了规矩,凡是出入府砥,都得打药熏房过,不可擅自经由别处出入。
杜谦下了衙回来,见了这个架式,心里便有些犯嘀咕。
他是大夫,自然明白杜蘅心里怕的是什么。
若是往年在清州,做了也就做了,可这里是京城,天子脚下,有些事即便心中见疑,嘴里也不得乱说,行动上更得万分小心。
否则,传扬出去,引起百姓恐慌,一顶妖言惑众,扰乱朝纲的大帽子压下来,立时便可以让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忙打发了厚朴去请杜蘅。
杜蘅并未隐瞒,理由也很堂皇:“这几日鹤年堂里病人激增,几个坐堂大夫都忙不过来,偶尔还得我过去帮忙。我看着,病人整天来来去去地穿梭,为防万一,这才设了个熏药房。”
这话自然是敷衍之词。
倘若只是防止鹤年堂的病人,只需把鹤年堂的前后门设熏药房便好,何必设在杜府的大门和角门处?出入皆要受制。
杜谦这时也顾不得挑刺,讶然问:“鹤年堂的病人也增多了吗?”
自鹤年堂移交到杜蘅手里之后,为避嫌疑,他便很少过问鹤年堂的事情了。
“我查过帐册,自三月末以来,病人激增了五倍以上。”杜蘅点头,又道:“听父亲的口气,朝中大人病倒的也不在少数了?”
杜谦定了定神,道:“眼下正值春夏之交,气候反常,时冷时热,体弱者受些影响也很正常。”
“是否正常,父亲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杜蘅淡淡道。
“我不反对你设熏药房,不过似乎往里挪挪更好。”杜谦想了想,道:“咱们家实再经不得任何风浪,行事更需小心谨慎。”
“是。”杜蘅也不得不承认,父亲入了太医院之后,眼界拓宽,说话做事都较以前有了章法。
“娘那里,先别乱说话,省得惊着她老人家反为不美。”杜谦又叮嘱。
杜蘅颌首:“我命人送了药丸去,只说是安神定惊,清火润肺的。若是祖母问起,父亲便也照这个话回吧。”
“嗯。”杜谦点头。
父女两个又谈了几例病例,发现病情都惊人相似。
先是着凉引发头疼,接着上吐下泄,之后开始发烧,用了药之后,稍好一些,又开始咳痰……
请医得早,用药得宜,病兴许就慢慢好了。
若是不幸,拖延了那么一二天,又或者请到一个庸医,用的药不对症,那就对不起,只好请你换个地方去感受感受另类人生疾苦了。
杜蘅还好,早有了心理准备,万事齐备,只等时疫暴发时,默默地施医赠药,以赎其罪。
杜谦却是胆颤心惊,一夜碾转犹疑着,到底还是没能下决心递折子,上达天听――与其做根出头的椽子,不如静观其变,随大流。
反正,出了事头上还有医正,左右院判顶着。至不济,还有十几个年龄资历比他老得多的太医国手在。
他一个新进的太医,又因杜蘅之婚事,多次被人言推上风口浪尖,何苦去出这个风头?
不过五日,白前家里传来噩耗,说是她娘殁了。
如同晴天霹雳,白前晕晕乎乎地,完全不敢相信:“不可能,我回的那天,娘明明大有起色,这些日子药又没断,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来接她的是许遥,哭道:“娘舍不得那些药,说已好得差不多,再不肯吃。还让爹把剩下的药材拿出去卖了,得了五十两银子……”
白前哭得昏过去:“娘,你好糊涂!”
白蔹心有不忍,几个人私下凑了份子钱,来向杜蘅告假,打算一起去白前家吊唁。
却被紫苏拦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可不能乱蹿,万一惹了病回来过给小姐,你们担待起吗?”
又取了五十两银子给白前:“我说话直,你别着恼。回去跟你老子哥哥们说,人已死了,该早些入土为安。不要停灵,赶紧买副棺材,送上山去,就算你们尽了孝了。”
紫苏表情严肃,颇有几分端凝之色。
白蔹几个听着有理,脸上便露出几分畏惧和羞愧,心里已生了退意。
白蔹把凑的唁金拢到一处,交到白前手中,委婉道:“是我的错,大伙都去了,小姐跟前只剩紫苏姐姐一个,怕是不方便……”
白前气得小脸煞白,截了她的话道:“不用说了,几位姐姐的好意心领了。我原也没脸因家事劳动各位姐妹,误了小姐的事,更不敢拿小姐的身子做赌注。只是我是个女子,家里还有老子兄弟,停灵多久何时上山却不是我能做得了主的。且,我虽比不得姐姐见多识广,可也没听说,有哪家娘死了不停灵,直接抬上山的。”
说完,银子也不要,扭身就往外走。
紫苏又气又急,追出去喝道:“我这也是替你着想,你咋不识好人心呢?”
白前只当没有听见,低了头往外疾走。
许遥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急得直冒汗。
正闹着呢,只见二门的小厮飞奔着进来报信:“燕王殿下来了!”
几个丫头唬了一跳,也不闹了。
紫苏问:“燕王为做什么,可有说?”
“不知道……”小厮跑得满头大汗:“突然就来了,在药熏房里研究了半天,抓了付强哥问东问西,又说有事要问二小姐。”
紫苏心里咚咚直跳,急匆匆回屋去禀杜蘅。
白前犹豫了一下,叫了许遥过来,塞了一包碎银给他:“二哥,你先回去支应着,等小姐这里事了了,我再回家。停灵的事,你跟爹和大哥商量着,也别太长,最多三天就上山罢。”
她虽年纪最小又是个女子,但一则素来聪慧机灵,二则她是杜蘅贴身的丫头。许家二个兄弟也是因了她才谋了份好差事,又因为她时常送些银子回家,家境渐渐有了起色,是以说起话来,就是许父也不敢不当回事。
许遥不敢多言,唯唯讷讷地去了。
这边紫苏几个紧赶慢赶地服侍着杜蘅换了衣裳,正梳着头呢,那边南宫宸已到了院中。
紫苏只好出去,请他到花厅坐了,又亲自沏了茶上来,杜蘅这才进来,屈膝下去:“给燕王请安。”
南宫宸摆了摆手:“虚礼免了,坐吧。”
“谢王爷赐座。”杜蘅也不问他来意,侧身坐了,一如既往地安静从容。
南宫宸一颗纷繁复杂的心,刹时便宁静下来。
似乎再大的麻烦,亦能迎刃而解。
美丽的幽瞳里微光一闪,略带着几分嘲弄之意:“二小姐果然沉得住气。”
“恕我愚鲁,不知王爷是何意思?”杜蘅不急不慌,淡淡反问。
南宫宸冷哼一声,眸光犀利,象是要把她的心剖开一样:“二小姐何必揣着明白装湖涂?本王且问你,无缘无故,杜府何以院中遍洒石灰,前后皆设熏药房,所有人等出入必得药熏?”
这段时间,他派了人对杜蘅明查暗访,又在杜府周边设了暗桩,想要查点蛛丝马迹。查来查去,没查到可疑之处,反而发现萧绝经常出入杜府内院后宅,与她过从甚密。
再后来,便发现端午未至,杜府上下不论老幼已提前佩了香囊,立夏之后更是院中四处洒石灰,前后门皆设了药熏房,府里上自杜谦下到小厮婆子,出入皆要艾叶,苍术,白芷等药熏一遍。
偏最近时有大臣因风寒请假不朝,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太医院空前忙碌,前几天肃亲王府一名小妾患病,差人拿了肃亲王的贴子来太医院请人,结果因太医院倾巢而出,硬生生让管家等了几个时辰……最终,那名小妾没能挨过去,殁了。
肃亲王大发雷霆,把钟翰林叫去,骂了个狗血淋头。
他是个心思灵敏之人,既动了疑,自然要去临安府查看死亡登记名录。
及到出了门,到了御街之上,却鬼使神差地拐了弯,等到他回过神来,人已坐到了杨柳院的花厅里……
到底为何要来,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哦……”杜蘅神情自若,漫声道:“入夏以来,鹤年堂病人激增,且家中老幼众多,现在又是春夏之交,为防患未然,做了些措施罢了。却不知触犯了大齐哪条律例?”
南宫宸脸色沉了下来,语气十分失望:“本王以为,至少你是个与众不同的,还懂得怜恤百姓疾苦,却原来也是个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
杜蘅目光冷凝,不闪不避,静静与他对视:“我本是个闺阁女子,所求的,唯阖家平安,一生顺遂而已。百姓疾苦,自有朝中百官忧心,他人瓦上是否有霜,又与我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