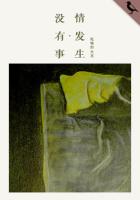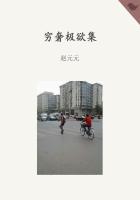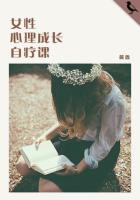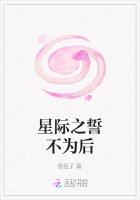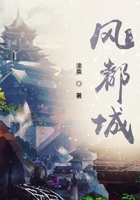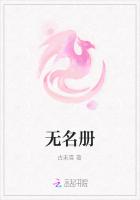帕斯卡·梅西耶的《里斯本夜车》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令人回味无穷。在作者笔下,戈列格里斯与普拉多是如此个性鲜明,在生命的长河中体味自己的人生,在他们的人生中,我们似乎也可以寻见自己的影子。《里斯本夜车》关于孤独、死亡、自由、逃离、人生、生命的探讨,无不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文辞优美,叙事朴实,是我的第一感觉。发人深省,驻足思量,使你不得不在阅读时停笔驻足,思考作者,思考自己。
“赖蒙德·戈列格里斯的生命出现巨变的那一天,开始时与其他无数的日子并无二致。”小说以这样的笔触开头,每天的七点四十五分,戈列格里斯都会踏上市中心通往菲尔德文理中学的科钦菲尔德大桥,可是这天,当他目睹一个行将跳河的葡萄牙女人时,他的生活开始出现了改变的痕迹。当他将女人带到中学里面后,他便发现自己与现在的世界有些不融洽了,一切都变得不是那么自然,他在学生们的惊讶之下走上讲台,让同学们更惊讶的是,这个“无所不知”的人居然也会出错。随着那个女人的离开,他的心出现了一瞬间的轻松,却又回味无穷,多么漂亮的葡萄牙女人,蓬乱的头发也掩盖不了她的气质。从这之后,戈列格里斯的生活开始发生了巨变,他本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有着规规矩矩的生活,才华横溢的他是这所中学的语言教师,精通希腊文、拉丁文甚至于希伯来文,超强的记忆力以及惊人的语言天赋使凯吉校长都自愧不如,他是“无所不知”,他过的古板生活是妻子弗洛伦萨所无法忍受的,这也导致了他们的离婚。这个“无所不知”的人啊,其实从这时在作者笔下,他就开始对自己缺乏了解了。于是,他匆忙形成计划,匆忙做出决定,在无人知晓的情形下离开伯恩,坐上火车,途径依伦、巴黎来到里斯本,寻访自己的心灵,在外人眼里,这似乎是一场逃离,希望隔绝自己熟悉的现实来找到自己的希望所在。
小说的主线似乎是戈列格里斯的寻找之旅,他找什么,开始会以为是那个在他心里留下剧烈波动的葡萄牙女人,然后紧接着是一场浪漫的爱情之旅,这可能是读者们一开始想见的结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全书的笔墨其实并不在于戈列格里斯,而在于普拉多,这个非凡的天才,这个与戈列格里斯其实有着相似的生活与命运的人,这个才华横溢,对于生命有着独特认识的人。戈列格里斯要寻找的,其实是与自己的生命,与自己的思想共鸣的一个人,一种思想。在一开始葡萄牙女人似乎是重大的切入点,在那个西班牙书商那里淘到的普拉多的《文字炼金师》似乎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或许当做慢车旅行的一本消遣读物,或是与同为吃“语言饭”的同行交流。然而,正是这本书,成为两人之间的纽带,成为两人心灵交流的媒介,翻开《文字炼金师》的导言,戈列格里斯即被震撼,这个年轻的才华横溢的少年,这本不知名的出版社“红雪杉”出版的旧书,居然有着如此深刻的魅力,与自己有着如此深刻的共鸣,自己的心灵似乎找到了寄托。“我们纵然经验数以千记,却至多只提其一,而且纯出于偶然,绝非因深思熟虑。在未被论及的经验里,隐藏着在潜移默化中赋予我们生活形态、色彩与旋律的经验”,“如果我们只能依赖内心的一小部分生活,剩余的该如何处置?”戈列格里斯回想买书时的坚决,不禁觉得这是自己做的最对的事了。
下了火车,来到里斯本,他不知所措,甚至于一时开始对自己的决定做出了怀疑,里斯本是他逃避自己的人生前来躲藏的城市。他呆在公寓里,不知其所,却因为眼镜损坏而开始了对于普拉多的寻求,从古书商尤利欧·西蒙斯到科蒂尼奥,他开始了探求与《文字炼金师》有关的作者信息,从女医生玛丽安娜·埃萨到反抗运动的战友凯吉·埃萨,从亲爱的小妹美洛蒂到对哥哥有着无限崇拜的安德里亚娜,从形影不离的朋友乔治到玛丽亚到“名字配不上她”的艾斯特方妮雅·艾斯平霍莎,从伯恩到里斯本到伊斯法罕再到菲尼斯特雷角,他寻找到了任何与普拉多相关的人,相关地点。在这些普拉多曾经最为亲密的人中,不断的普拉多的手稿笔记书信的出现,使得戈列格里斯对于这个自己心中逐渐形成的偶像有了更深的感觉,他似乎是在找自己与普拉多的共同点,又似乎是在找寻自己心灵的归宿。不断地探寻下去,戈列格里斯对于普拉多有了全局的认识,他年少时意气风发,素有反抗与批判精神,才华横溢,对于知识的渴望和非凡的天赋,对于老师们的百般刁难从容面对,后来成为以为拯救许多人的医生,救死扶伤。然而,这份风光背后掩藏着普拉多百般的无奈,从小威严的法官父亲与母亲甚至与全家族都给与了他过多的期望,一直活在重担下的他无疑不断滋生出反抗的情绪,父亲的期望是让他成为一个医生,他则幻想者成为一个神父。他想逃离这个世界,却又时常不得不屈服,学生时代的年少轻狂、毕业致辞时的对于神的蔑视,对于秘密警察门德斯的拯救,使他沦落到了道德的弱势地位;他时常孤独,真正的朋友只有乔治罢了;乔治在深夜睡不着时与他探讨死亡的话题;周围的每个人都爱他、尊敬他,但他却想逃,想从他人的期许中逃出,想从他人眼中的伟大形象中逃出,普拉多想活出自己,却在无能为力当中,意识到生命的局限性与无可奈何。他有着自己的哲学,走出生活的既定性的哲学。
同样,正是因为如此,因为普拉多的哲学,因为《文字炼金师》中华丽的辞藻与深刻的思想,戈列格里斯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他不是同样有着自我设限的生活吗?自己何尝不是被固化的生活所束缚?尽管自己对于虚荣名利看得如此之轻,却又时常为流露自己的对于语言的才华而愉悦,何尝不是为自己设限?他来自社会底层的家庭,对于语言有着惊人的天赋,他坚持不考国家教师执照,坚持不获取更高的学历,终身委身于高中教师的职位。他还拒绝听妻子芙罗伦斯的母语西班牙语,抗拒搭乘那只有起点和终点、但看不到过程的飞机。戈列格里斯借着对既有社会价值体系的抗争,来表彰对自我意识的坚持,然而他也发现,自己的这种抗争,是否已排斥了许多人,成为“纸莎草纸先生”,与社会的孤立,以致于一个红衣女子的出现就足以扰乱他的生活,足以破坏他长久以来建立的社会生活体系。他对于普拉多的探究,来自于心底的归属感,他起先为《文字炼金师》的优美而又富有哲理的文字所打动,后又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寻找自己。他找到了彼此之间的共同点,比如对待庸俗与名利的态度,“庸俗乃是所有牢狱中最歹毒的一个,是拿简化的不实情感黄金来包覆铁栅栏,让人们以为那是宫殿梁柱”,普拉多讨厌这种感觉,戈列格里斯同样也是这种情感的坚定反对者,从其对于职称考试与芙罗伦斯的朋友的态度便可见一斑。我们可以看出,戈列格里斯在里斯本通过对普拉多的探寻,也寻到了自己,他的生活开始丰富起来了,与各种与普拉多有关的人来往,和他们沟通心底的灵魂,帮助安德里亚娜面对哥哥的死,把墙上的挂钟重新启动,开始新的未来,他在离开里斯本之前,记起要用胶卷记下自己经过的风景,回到伯恩,同样在布本贝格广场留下回忆。
我们不禁可以发现普拉多与戈列格里斯的生命观,同样也是他们的自由观,“我们的生活不过是流沙,在一阵风吹下,短暂成形,下一阵风来时,又被吹散。一个徒劳的构成,在它尚未真的完成之前,便已被风吹散”,生活生命看来自由其必然性。就如普拉多一样,生在富贵之家,其实其性格与成长和父母的期望,在一开始就决定了,生命有其可悲的必然性,普拉多渴望改变这种必然性,然而在各种压力之下他又不得不屈服,尽管他有着丰厚的思想与超凡的才华,可又如何?戈列格里斯看似生命不具所说的必然性,生在贫苦之家,却能够有如此的才华,然而我们从他固化的性格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生命其实也是处处有必然性的影子。但是,相对而言,生活其实也有其偶然性,一个红衣女子的出现,就彻底改变了戈列格里斯的生活;也可以说是各种偶然,才促使戈列格里斯不断地探寻普拉多的踪迹。“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如何生活,而在于如何设想生活”,《文字炼金师》中如此写道,生命没有所谓的终极意义,生活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各人自有其不同与玄妙之处。苦苦追寻意义和答案的旅程,注定通向流沙般的泄落。所以当戈列格里斯一边欣赏伊斯法罕的景色时,心底会冒出伯恩和里斯本其实都拒绝了他的想法,当他生命列车途中回到伯恩的一段小插曲出现时,他感到熟悉的布本贝格广场已不同往日了。如普拉多所说,生命的意义便不在于如何活,而在于我们感悟生命、设想生活的一个过程。生活有其既定性,我们的任务便是在既定性的条件下,运用生活的元素来设想我们的生活,不管其会有多少成果,是好是坏。
在生命的探讨之外,其实作者还探讨了许多问题,比如独裁下的自由问题,“当独裁成为了事实,反抗便成为了义务”,普拉多对于父亲的隔阂其实也在于此,他认为父亲在帮着阿尔法尔审判,对于萨拉查的独裁却无动于衷,所以做出了许多反抗法官父亲的事;在尽医生的义务救了秘密警察门德斯受到所有人的敌视之后,加入了反抗运动,殊不知,自己的对于自由的追求其实已经在这种压力之下进入坟墓了,如我们所说,生命具有既定性。比如关于死亡的探讨,当乔治在深夜中惊醒,与戈列格里斯通话述说着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从自己买的史坦威钢琴联想到自己的对于死亡的恐惧来源于自己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将不完整,支离破碎,得不到指望的和谐。这种恐惧,在普拉多的帮助下予以化解,“你到底是从哪个立场抱怨无法企及的完整人生?你惧怕的又是何物?何不从人生每一刻皆川流不息出发,缺欠的完整并非不幸,而当成对生命力的鼓舞和标志”,普拉多对于乔治的劝解,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哲理。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我们对于人生不完整的担忧,来源于我们还身在阅历人生的阶段,却预先望向了未来,站在了还未出现的终点之上,对我们还有所欠缺的人生产生了绝望,而我们不知道的是,路需要我们一步步走,终点正在等着我们一步步走过去。比如关于孤独的问题,普拉多提到了唾弃的孤独,我们可以想到,时常我们一个人独处,却丝毫不感到孤独,但也可以身在人群之中,却依旧感到孤独,孤独似乎与他人是否在场无关,与他人正在做什么事情无关,所有的一切,其实根源于我们的主观感受,所以深陷孤独之时,我们可以对外界的褒贬、爱憎都淡然视之……
这是一次布满困惑与悬疑的列车旅行,这是一段充盈感悟与省思的生命探访。“假使我们终于明白了,在我们面前,以及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所有体验,不过像是流沙一样……”戈列格里斯坐上太迦河渡船回到里斯本时,心中如此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