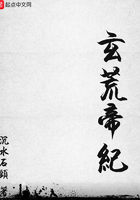当一个人彻底绝望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回想,自己一生究竟做过什么事情。而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也莫过于此,因为仔细想想,你什么也没做过。现在我满脑子里唯一有印象的,就是刚才和紫做爱未遂。而如果真的有所谓来世今生,我到了阎王殿里,阎王问我是否为党和国家做出过某些贡献,我也只能支支吾吾地,头脑里也只是这些事情(所以讲“色是刮骨钢刀”么)。
我是做鬼也不会放过杨海诚的,真的。他既拿了我的五百块钱,有让我落得如今这个下场:要想一个异装癖的变态一样死去,而死了还要被世俗误解。
人生原来就是这般荒唐呢——我忽而想起我老爹往日里常教育我的:不要老是人为地妄图延长自己的性命,做这些东西干嘛呢?(前提是:这些都是我爹反驳我妈不叫他抽烟的借口。)就像你活得久了,还能为社会做什么贡献似得。既然这一生的烂肉无益于社会,那何不一死了之呢?有何必忝列于世浪费粮食?
“母亲给我以智力,而父亲赐予于智慧。”我想,我老爹给了我这般的金玉良言,就比当个什么省长、书记之类的有用的多。如今公然拼爹(比如“我爸是局长”一类的)就相当于坑爹,不便讲出自己老爹又怎样的成就;而我是倒可以自豪地把我老爹这句话讲出来给大家听,并四处炫耀。Personally,我觉得我老爹这句话很有智慧,而且也很实用:我相信人之所以会感到苦恼,归根到底是终有一死;而我老爹这句话表明,人就是该死的,不死反而对不起国家,那也就无所谓了。推而广之,所以的苦恼也就烟消云散了。
只可惜柚子姐把我的嘴堵住了,我没法把我老爸的至理名言讲给细竹姐听。
而即便没有这等般若加护,细竹姐仍旧不屈不饶,还打算跟柚子姐讲道理。血和唾液混合的呼噜声,以及大概是牙齿被敲掉后有缺陷的发音,都没有阻止细竹姐讲话。她说,自己如何真是无所谓的——既没有父母要孝顺,更没有伟大的理想要实现,所以要杀要剐随她便。然而我呢,(细竹姐往我这里看了看,much more concerned about)和这件事情没有半点儿关系:
“我吧,贱命一条,就像你每(们)整天踩死的蟑螂别(般),死则死矣,吴硕为(无所谓)……”细竹姐含糊不清地讲,“这世上,只有你是我追号(最好)的朋友了……你要是也不管是阴(关心)我,那也只有(就)没人在乎我了……可是放了他……他跟这件事儿额米(没)关系。是啊(杀)了我,吴硕为(无所谓);而他要是有个山(三)长两短,你……”
细竹姐!我感动得要哭了。就凭你的这些话,我再也不说你和什么苍蝇啊、蟑螂啊,有半毛钱关系!你之前对我说的那些过分话,我日后决不再计较了,看在一切生物之母,the most ancient, most essential, most sacred form of all creatures, under whose blessing that makes us what we suppose to be,的份儿上,我再也不对你说过分的话了!
(然而想到这些,说实话我内心很凄凉——难道人就是这样的生物?越是在紧要的关头就越是没有廉耻?)
“你说,她(我认为柚子姐的意思就是这个)——?”柚子姐夸张地拉长了语气,脑子转向我,看着我笑了,“归根到底,你应该是在嫉妒吧……嗯?嫉妒我如今抛弃了你,而又和她在一起?哈哈哈,你应该嫉妒:因为你知道么?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把你当成朋友、爱人、情人的,只有我而已。而一旦我抛弃了你,那么你就只能在孤独和痛苦里自生自灭,我说的没错吧?可是如今我就是要抛弃你!”
唉,这是我所听过最自恋的话,没有之一。
“还不之一(知)道是谁抛弃了谁……”
细竹姐还是笑着,露出了一口被打断的牙齿,和满嘴混着唾液黏糊糊的血。
“这样啊,你知道么,我一直都觉得,你的嘴挺硬——”柚子姐一棍子摔在细竹姐嘴上,我大概是听到了啪嚓样牙齿折断的声音,“嘴硬的人总是在不经意中伤人,嘛(她学着细竹姐的口气),没办法的事情,不是么?我也只好用别的法子让你明白咯……”
柚子姐把本要用来割我蛋的手术刀拿起来,架在细竹姐脖子上,“啊咧咧,人们一只以为,把气管割断人就会死。我现在澄清,这是个误解:呼吸不是用鼻子吸的,实际上是用隔膜的运动来实现。而之所以古人自刎而死,主要是因为血液进入了气管,人窒息而亡。又何况人脖子上还有三叉神经、迷走神经一类重要的神经组织。不过放心吧,我是学医的,我只会切开你的气管,我知道并非是有意讲出这些伤人的话,是吧……”
讲着讲着,柚子姐忽然脸一沉。
“算了,我还是杀了你得了。”
(我倒是觉得,这仅仅是她学医不精的体现。毕竟自从Freud the Great之后,又有哪个所谓的心理医生还有外科方面的功夫?)
当柚子姐把手术刀(她是从哪搞来的?)插进细竹姐的脖子,不知是我的神经敏感,还是被她打了一棍子出了错觉。我只是觉得,地板、天花板、墙上夹缝里,总之如果把这栋建筑物比作是人体,那么她的每一根血管便都开始震动起来。不知道的以为这是细竹姐发动了何等的神力,而像我这样知道的,便明白是所有寄生在这里的蟑螂,都出来保护她的女王了。
当然,我觉得这不过是出自本能的行为,大概类似于汽车迎面冲来的时候还要用手挡一下般。反正那些冲上前来的蟑螂,无一不被柚子姐轻轻地踩扁——所谓螳臂当车就是这个道理吧?
显然,细竹姐还想继续讲点儿什么,然而无一不被迸出的血水给呛了回去。况且,所谓的什么“三叉神经”或是“迷走神经”都被切断了。她只能低着头,看自己的血以及沉没在其中,正绝望翻滚的蟑螂。
我不知道柚子姐算不算那种,“见过大场面的人”。Looking at such a big scene which was made by herself,柚子姐多少有点儿慌了。手术刀掉到地上,就如她的理智完全陨落了一般。她面无表情地蹲下来,差点儿在血水里滑到,勉强捡起手术刀。发觉我在看她,她勉强地挤出一点儿笑容,(大概,杀死了自己最好得朋友,她还是有点儿于心不忍吧?大概。)搞得像是我在关心她似得。
“好了……碍事儿的人,都没了……现在是只属于我们相处的时光……”
哦,是么,细竹姐就这么完蛋了?我还指望她能救救我。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相信什么神灵了。我倒不是质疑他们的存在——事实已经告诉我,比如什么Teufel呀,或者是哈牛这些的,纵然都是活生生超自然的存在;而我之所以丧失了信仰,是发现他们和我一样,关键时刻根本就派不上啥用场——细竹姐不是所有蟑螂或者害虫之类的女王么?到头来被人打断了牙,塞了一嘴钉子,最后还被放了血。
所以说么,人类对蟑螂的制裁完全就是出于对一种施虐的热情。
啊对了,说到哈牛,她跑哪儿去了?大概一开始就逃命去了吧……尽管她应该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命”。
而如果她还有心(有也是木制的),去叫人来忙帮,便算是我命好;至于等人赶来,我是男是女,就看我命大小了。
看着柚子姐很专业地拿着手术刀,(到了现在这份儿上,又何必是手术刀呢?水果刀、美工刀、双刃大砍刀什么的都可以,哪怕是豁鱼的大号剪子也无所谓。人为刀俎,我乃鱼肉,又何必正儿八经地摆出一副对待病人的态度呢?)沉着地走来,先是托起我的下巴看看,又摸了摸脖子,对我耳语:
“心跳得这么快……你是不是也很期待……呢?”
我之前说很多人“快感错位”,如今觉得如今没有所谓“错位”这件事儿了。心跳么,高兴了也心跳,害怕了也心跳,谈了恋爱更是心跳。(有游戏叫“心跳回忆”,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喜欢吃辣椒,可是辣椒本质上就是灼伤舌头而已。吃得一个个呲牙咧嘴,完全就是被折磨的样子,然而却又直呼“过瘾”。就更不用说那些玩SM,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之人。
为了安慰自己,我这样想:就权当这是一次玩过火的SM事故吧。我想年年都有这样的人,因SM一类的事情丧命。他们算是花了钱,没了命;而我不用分文,也没了命,大概也值得吧?虽然我明白这念头很傻,傻到自己也觉得好笑。只是命运如此残酷,不想些安慰人心的,比如天堂地狱一类的概念,又该怎么活下去呢?
因此,当柚子姐冰冷的手术刀碰触到我那private part,我多少还是感觉到一点兴奋了。我想,反正也是死定了,(即便不死,我也不怎么想活了。)不如先让柚子姐帮我……
猥琐的念头在我头脑里闪过,我便想起了杨海诚,本该在我身边的紫,以及更要命的,我那五百块钱。
所以说到底,我到头来和花钱找死的人也没区别。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之前设想的一切自我安慰的话,天堂也好,地狱也罢,都玩完了。
真要命,都快死的人了,还是……
……还是死吧……
(人临死之前,多想想一生中那些讲出来就羞得遍地打滚的耻辱,到也是可以慷慨赴死了。)
然而正所谓,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让你五更亡,and vice versa。我已经体会到冰冷手术刀即将刺进我那“肾囊(文雅一点儿)”这一“包孕时刻”之动作(如果要画插图,自然这一刻为妙。)之时。便听得有人大喊,“住手!”
可当我发现,门口站得却是双目异色的大木偶哈牛,难免有点儿失望。
“你要找的人是我!”哈牛语气坚定,大概是做过思想斗争,认定自己到头来仍是没生命的木头疙瘩,便战胜了心中的cowardice,挺身而出。“我就是你说的,被他们所藏匿的神灵!我知道你信奉科学,而科学家的职责便是把人的想象拉下神坛。我就在这里,你冲我来,不要把没关系的人扯进去!”
实际上不是这样……我是另一回事儿。不管柚子姐对神灵报以怎样的态度,我的肾囊还是要被她割的,这是两码事儿。
“你听见我说话了么?放了他……们……”
虽然是木偶,或者某种意义上的什么神灵,看到了满地的血,语气不由得颤抖起来。当她发觉,那个低着头,shedding with blood and cockroach throughout的家伙便是细竹姐,瞬间就崩溃了。就像赶来救场的小弟,发现老大早就被干掉了一般。她慌忙跑去,在血水里摔了一跤,跪在细竹姐面前,那叫一个撕心裂肺。
“如果你真的是什么神灵,那就引发个奇迹给我看看吧……”柚子姐晃晃悠悠站起来,就像英雄史诗里所谓的“Drunk with blood”般,对徒劳喊着细竹姐的哈牛傲慢地说:“就比如,把你眼前的人复活吧?”
哈牛扭过头,用她那张木偶脸盯着柚子姐,一字一顿地讲:“你,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哈牛虽然没有表情,然而我觉得,她此刻的表情很不错。冷漠,淡然,略带几分残酷。倒是很像所谓“神明”的样子。
那么,就引发奇迹……
然而也不过是有个样子罢了,柚子姐飞起一脚踢在哈牛胸口。大概木头也是空心的,哈牛直接飞了出去,靠在墙上坐着。只是表情还是那般坚定,淡然地说:“你将会付出代价……”
“代价?哈哈哈!”柚子姐又仰着脖子狂笑了,“难道如今的神灵都是这般匮乏么?到头来,也只能用什么代价、宿命来恐吓世人?那我问你,为什么那些人如今还在社会上横行,我可没见过他们付出了什么代……”
“价”字还没讲出来,奇迹就发生了,(尽管我认为和哈牛没太大关系)且看:
随着我背后一声巨响,巨大的身影,随纷飞的碎玻璃在我头上掠过,从背后扑倒柚子姐。乌黑秀美的长发(就是我爱说的什么“濡鸦”),包裹着线条清晰的金属轮廓。而那寒冷的金属光泽顺着下颚,蔓延至结实的手臂,在指尖发出逼人冷光。怒吼同金属的摩擦,气体压缩和爆裂之声混合,尖锐的钢牙张开,死死咬住柚子姐肩膀。血色一闪,柚子姐的哀嚎和血水四处喷溅。充满野性的咀嚼声,高傲扬起的脖颈,被血光擦亮的金属。
An enormous but elegant wild beast embroidered with gleaming metallic refinement.
我认定,这便是现代神灵应有的姿态。
“Er nennt es Vernunft und braucht es allein—”
伴随着眼前这although fulfilled with blood and violence, but sill magnificent的场景,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却也不详的声音。
“Nur tierischer als jedes Tier zu sein!”
如果没有这两句大概是咒语,柚子姐的脑袋就会被那口金属巨齿咬得粉碎。而当神圣的言语一说出口,尖锐的指爪便停下,缓缓向其主人脚下走去,所谓“虎踞”般地坐在他身边。在昏暗中,金属面罩下一双巨大的眼睛发出绿色的冷光,狂躁不安地垂涎于遍地的血迹。
我定下神来,仔细端详食肉动物特有的倒三角般健硕身材,倒觉得有几分似曾相识。
而她所谓的主人,便是我亲爱的杨海诚同学了。如此说来,便是他救了我的命。我很感激,但还是觉得有点儿不靠谱。
海诚,或者说Teufel,打开自己的手提箱,从里面拿出血淋淋的包装袋。小心地撕开,大概是怕血水溅在身上,两只手指掐着往空中一丢,金属碰撞的声音一响。
“乖,吃了这个就别打她主意了,听话!”
Teufel爱怜地摸摸她的头,(即便是狮子,吃饱了也似家猫一般乖巧——不知道是谁说得来着。)把摊在墙上的哈牛扶起来,彼此交换了几句话,看样子在安慰她。嗯,毕竟细竹姐都那样了。哈牛又朝我这里指了指,杨海诚的目光便一转。先是惊奇了片刻,随后是一脸痛苦的表情。
人生中最痛苦的,莫非是不该笑时突然想笑;本想强忍住不笑,却莫名觉得越来越好笑。
最后没办法,他还是捧着肚子笑出声来,结合着遍地鲜血的场景,我倒觉得他此刻的确很像一个Teufel——尽管我是主要诱因。
“同学,你这样子倒让我想起一些不好的……哈哈哈……抱歉我不是要笑话你,你这一身真的很漂亮,我只是……哎呀……哈哈哈……话说回来这身衣服是紫的吧?妈呀,哈牛你愣着干嘛?快把紫松开,什么衣服也不穿会感冒的……”
说着,海诚把外套脱下,罩在紫身上,转过身来对我说:
“虽然你……”我听得出来,他是强忍着笑的,“……这幅样子,但毕竟还是男生吧?灾难还尚未发生吧?”他低头看了看,“好,那你就先忍一会儿吧,我这里还有些事情处理,女士优先对吧?”
他拍拍我脑后,那大概正是柚子姐击打之处。顿时感觉a thread of tenderness and consolation running down through my spine。我方才意识到,一切都过去了,我大概算是安全了吧?一股昏昏欲睡的感觉油然而生。
海诚走到柚子姐面前,(而之前他还很嘲讽地走到细竹姐那里,得意地拍两下她的脸。算是对平日里无礼的报复?算了,毕竟他是Teufel,做出怎样过分的行为也不足为奇。)蹲下,打开手提箱,瓶瓶罐罐啥的摆了一地,也不知道要干嘛。
“看样子你是搞砸了,不然他怎么在这里?”
一扫平日里cynical且奔放的语气,海诚便摆弄着手头的事儿,便用少有的温柔对哈牛讲。
“其实主要怪细竹姐……她大概看不下去,半路杀出来把我们揪走了……”
“哦……”海诚拿出塑料针管,就是平日里瘾君子常用的那种。开封,组装,抽着柚子姐的血,“以后得跟老爹讲讲,她还真不能老和咱们黏在一块……一方面,她真的和我们不是一路人,她和我们做的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两码事儿……另一方面,她也是太好心了,说到底只能给自己找麻烦,就像今天这样……”
看着一针管血,Teufel难得地叹口气,很沧桑的样子。
“我打赌,直到最后她还是一心想把这女人劝回来吧?”
“嗯,不然也不会变成这样子……”
“但是她这样脾气,怎么能劝人?不过火上浇油罢了。难不成老爹让她和我们一起,是做催化剂用的?天哪,你看,这是一点火就着的呢……也难怪今天她这么激动……啊,嘘~嘘~,乖,好姑娘,mein liebe。我没叫你,你继续放风……最近她也是闲得发慌,没事儿就跟我闹脾气,你看她今天晚上吃饭时候……哎呀,最近找个机会带她溜溜吧……”
“那她肯定会惹麻烦……”
“呵呵……”
还未等弄明白,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我就沉沉地睡去。依稀感觉眼前似乎有火光,有交谈,但至于那是梦境还是现实,我也搞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