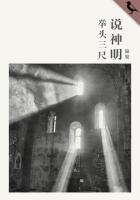史载:厘王五年秋八月,彭使大夫浈远族五卿。
我们站在那座神秘的建筑前面,侧对着黑洞洞的大门,正打算离开,突然马匹嘶叫一声,掉头就跑。不仅仅是我们的坐骑,连驮着干粮的那两匹马也发疯一样远远离开。这几个畜牲,刚才还有气无力地不肯快奔,此刻哪里来的这种精力?!
我和彻辅追出了十数步,就知道根本于事无补了。我们瘫软在沙地上,浑身的骨节像要散开一样,而心情更是沉入了谷底。
“这……没有办法……”彻辅哭丧着脸,“连马也没有了,难道我们就要这样死在荒漠中吗?”
“若注定必死,有马也是逃不了的,”我安慰他,“若上天尚肯眷顾,总会有一线生机。”说着,回过头来望着那座神秘的建筑,淡淡地笑道:“似乎……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希望里面有可以帮助我们前进的事物吧。”
我拉着彻辅站起身来,警惕地慢慢向那座建筑走去。“我把火石都留在马背上了,”彻辅似乎并未能因为我的话而振作起来,“里面漆黑一片,就算有什么事物,我们也很难发现呀。”
我笑着瞥他一眼:“就算把火石留在身边,沙漠中没有植物,找不到干柴,你又能引燃什么东西?”
“起码咱们还有衣服……”还好,看起来这小子虽然绝望、惊恐,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我们各挺着铁剑,并排走到那座建筑前面。我伸手推开半掩的房门,腥气越发重了。
“我先进去,你在后面保护我。”这样说着,我大着胆子,慢慢迈进建筑里去。
这是一座纯粹的石制建筑,连地上都铺着方石,但也许是风沙的侵蚀,也许是年代久远,到处高低坑洼不平。刚进去的时候,还有阳光从门口照入,勉强可以看清四周的情况。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厅堂,没有任何装饰和家具,左右两边有一扇木门——和大门一样,都虚掩着——厅堂的尽头却是一道蜿蜒向上的石阶。
我转过身,用目光询问彻辅。彻辅舔着干裂的嘴唇:“弟、弟子不知……师父决定先往哪里走吧。”我点点头,大步向那石阶走去。
这个时候,四周已经很昏暗了,才走上七八级石阶,双目已经难以视物,连上阶都要靠脚尖的触觉。我正在犹豫,突然想到一个妙计,连忙从怀里掏出那方丝绢来并且打开。五方神器就都安然平躺在丝绢里,其中只有有圭在散发着淡淡的黄光。虽然这光茫非常微薄,但总比漆黑一片要好。
我把其余四方神器重新包好,藏入怀中,然后右手持剑,左手高举有圭,慢慢向石阶上走去。不知道为什么,心中突然产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个地方,我很久以前似乎来过……
石阶上面,恍惚又是一个大厅,但四周昏濛一片,看不清究竟有多大。摸索着慢慢向前走去,终于摸到了墙壁,靠着墙壁慢慢移动,脚下却碰不到别的什么东西。黑暗是很令人恐惧的,如果不是有圭的黄光存在——其实靠它也看不清什么东西,那只是心灵的一种慰藉罢了——几乎要疑心自己置身在梦魇当中。
就在这个时候,“喀”的一声,一道猛烈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晃得我两眼一花,刹那间仍然什么也看不见。耳边听到彻辅的欢呼,定神望去,只见他站在墙边,身侧的墙上开了一个大洞——那像是扇窗户。
“这里有窗户!”彻辅欢叫道,“不过都是无孔的死窗,并且都关闭了。”说着话,他游目四顾,看到一扇窗户就冲过去,用铁剑把它劈开。厅中的光线越发强烈了,恐惧随着黑暗的逐渐消逝而终于飘散无踪。我仔细观察这个大厅,和楼下一样,也没有任何装饰与家具,一侧是上来的石阶,一侧多窗,左右两侧却各有一扇半掩的门户,和楼下一样。
熟悉的感觉越来越是强烈,我一定曾经来过这个地方。我仔细回忆着,有什么建筑是通体石制的,并且毫无家具与装饰?不,我以前来到的时候,这里或许还有一些装饰和家具,那么它……
在脑海里添加上家具以后,一个模糊的印象逐渐成形。我悚然一惊,想了起来,后背的冷汗不由涔涔而下!
是的,这确实是我熟悉的地方,世界上如此大型的石制建筑只有两处,一是王京的檀宫,一是彭国的石宫。檀宫我没有去过,石宫却是上上代彭先君涵公在位时,用淄邑外西山中盛产的一种坚固的白石修建的,广五百丈,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常去父亲监督的工地上玩。我记得很清楚,父亲曾经因为我拿着小刀在石头上刻字而责打过我。孩子总有一种叛逆心理,你越是责打,我越要犯错,当时我曾悄悄地在已经筑好的大门旁一个角落里,刻下过自己的名字。
是的,就是这个建筑,这正是石宫的主体建筑,从它还是图样的时候,我就见到过。彻辅大概因为我的面色非常难看而惊愕地望着我,我不在意他的眼神,迈开大步向楼下走去,直冲到门边,蹲下身来,寻找刻字的部位。长年侵蚀,石墙已经斑驳损朽了,早看不清我的名字,但可以明显辨认出曾经刻过字的痕迹。
这真的是石宫吗?它怎么会到大荒之野中来的?它怎么会朽败成这样?难道,这又是一个虚幻的未来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苦苦地思索着。
彻辅来到我的身边,关切地问道:“师父,您怎么了?”
我摆摆手,示意彻辅安静下来。我是又堕入了虚幻中吗?怎么丝毫也没有征兆?这时候,突然想起在寒所祈祷的梦中,燃对自己说过的话:“这河是阴阳的分界,你既然已经坠入河中,怎样证明自己还活着呢……下愚五千万天地十万万万缤纷世界,表里、昨今、反正……表里是宇,昨今是宙,而反正就是阴阳。阴阳的分界,就是反正的分界,你在阴阳的边界上徘徊,在反正中游荡,自己还不知道啊!”
虚幻,和真实,真的有所区别吗?有无限关联相牵的这两个世界,仿佛真实的自己与镜中的自己,是这样相像,又相隔遥远。有无,故有有,有虚幻,才有真实,反之亦然,既然如此,抛弃了虚幻,真实是不是也就不存在了?
千年以后,沧海桑田,彭国会变成一片沙漠吗?石宫会毁败腐朽,变成现在所见到的这个样子吗?如果那样的话,它不过是未来的真实反映,而未来的真实,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正是虚幻的吗?真实,虚幻,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低下头,发现有圭还在手中,散发出淡淡的黄色的光芒。有圭是真实的吗?神器是真实的吗?我是真实的吗?大劫是真实的吗?也许必须对应虚幻,这些才是真实的,而对应真实,它们反倒是虚幻的呢。真的很可笑,原来我一直在阴阳的分界徘徊,在反正中游荡,但直到今日,才知道反正间的相同与相异啊!
想到这里,我猛然站起身来,倒吓了彻辅一跳。我没有对他说明这里就是彭国的石宫——说了他也不会理解——我只是似乎若无其事地对他说:“终点,已经很近了。咱们顺着那腥味去找找看吧。”
彻辅听不懂我前半句话,但却明白我的后半句话,他急忙说道:“我估计,那腥味是从左侧的门内传来的。”
我仍然一手持着铁剑,一手握着有圭,大步向那扇门走去。
“师父小心,还是让弟子走在前面吧!”彻辅劝我,我却摇了摇头,并没有放慢速度。
推开门,更浓厚的腥味扑面而来。我毫无畏惧地走了进去,凭记忆找到窗户的位置,用剑劈开,迎进了阳光。这里也是空荡荡的没有一物。我感觉到,腥味传来的方向,一定就是西侧宫门。
遥远的过去仿佛一个梦境,想当年彭的先君就是从这西宫门逃出,结果被秩宇一剑刺死的。就在那场伏击中,我被手持雨璧的彭角长老施法所伤,生命中一切诡奇莫测、一切峰回路转,就正是由此为开端……
穿过重重门户,我大步向西宫门方向走去。彻辅跟在我的后面,想必对我如此熟悉屋中通路而感到奇怪吧,但我现在并不想向他解释,而即便真的解释了,他也未必会明白。
终于,我们来到了宫门的位置,我用铁剑在石墙上戳了几下,找到了石门的缝隙。门外应该就是当初我们埋伏的庭院了,那里曾经密植着繁花,还有一口甘甜的水井,不知道如今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是否和我们进来前一样,是铺满了厚重的沙砾呢?论起情理该当如此,但此时所见本不合情理——不管门外有些什么,我似乎都不会感到惊讶。
我推开了斑驳厚重的石门,随着刺眼的阳光,一股腥味也扑面而来。但这腥味却与适才室内所闻不尽相同,不再恶臭到令人欲呕,如同食人野兽的气息,反而在浓浓的腥味中还夹杂着若有若无的淡香。我很熟悉这种腥味,那是浓浓的血腥!
回头望一眼彻辅,他的脸上同样露出了惊愕之色——他也闻到了吗?他也分辨出来了吗?门外究竟有些什么?我转回头,警惕地挺起铁剑,小心地迈出了第一步。
于是,我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
石宫的西门外,仍然绿草如茵、繁花盛开,但给我视觉造成巨大冲击的并不是这些,而是满地的尸体,重重叠叠,满地的污血,纵横流淌。这究竟是什么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又迈出了第二步,于是眼前一阵恍惚,猛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就在那尸山血海中傲然挺立着。
那是远啊!那正是我亲爱的弟弟远啊!
但这不是现实中的远,而是未来的远,是我曾在空汤所赋予的虚幻的未来所见过的远。他高高的帽子,朴素但整洁的上衣下裳,腰系宽大的玉带,面孔瘦长,黑须如漆。
我看到了远,但他似乎并没有看到我。他就手按长剑,昂然矗立在那里,顾盼自雄,有一霎那,他的视线似乎从我身上掠过,但那阴狠且得意的目光并无丝毫改变——我低头看看自己,褴褛的衣衫,手持的长剑,似乎并无异样,然而……他真的看不到我吗?
正在疑惑间,抬眼又见一人披甲顶胄,手持长戈,匆匆而来,到了远的面前单膝跪倒——虽然此人五十多岁年纪,鬓边已有白发,但我还是可以一眼就分辨出,那是革高!
“禀报家主,弓、腾二氏拒守石宫者,无论妇孺都已杀绝。”
“很好,”远发出了冷冷地一笑,“如此五卿俱灭,我可以前往宗庙去向太夫人和国君禀报了。二十多年,终于大仇得雪!”
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吗?远还是无法摆脱内心的仇恨,苦心孤诣,直到和王姬玉檀合谋,族灭了彭国的世卿吗?此时此刻,我已经可以认定了,眼前所见的定是未来。至于是否虚幻的未来,还是真实的未来,两者其实又有什么区别呢?
不过,等一等,他刚才说“五卿”而非“六卿”?啊,对了,峰氏已经因为秩宇的叛乱而被革去了世卿的职位。那么,远有没有同时杀尽峰氏呢?我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突然间,已经垂垂老矣的明暮蹒跚着走了过来。他并没有如革高一般全身甲胄,而只是穿着长袍、戴着高冠,他向远深深地一鞠,禀报说:“峰氏已经应允了,将峰序之子过继,以延峰扬大夫之嗣。臣因此撤了包围峰氏的兵马。”
原来如此啊,原来远终究还是看在我的面子上,饶过了已经日薄西山的峰氏啊。我从明暮口中听到自己的名字,不自禁地就回过头去望一眼彻辅,然而……我身后是辉煌而洁白的石宫,毫无残朽痕迹,西侧宫门洞开,里面也是重叠的尸体和纵横的污血,却并没有看到任何站立的、熟悉的人影。是这样啊,来到这个似真似假的未来的,仍然只有我一个人,或者不如说,只有我无法为他人所察觉的魂魄。
这难道又是空汤的法术吗?沉寂了那么久,他终于肯再出现了吗?
几乎同时,空汤的话语就在我心中响起:“不,我什么也没有做。得以见到未来的,是你自身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