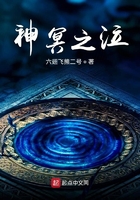“弗拉基米尔先生,您的身体状况已经无碍了吧?”
“谢谢您的关心,已经完全没问题了。”
“那太好了。”
参观樱花公园的后一天,在礼貌地询问了我的健康后,胡安所长宣布正式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胡安本人之外,还有副所长赵,他来自东亚的满洲,据说是一个所谓的心理学家。此外还有三个研究室的正副主任,一共8个人。
“在座的各位都是从社会学院各个机构抽调来的精兵强将,都是由院长先生和我亲自挑选的。”说到这里,胡安的嘴角划过一丝得意。他今天穿了衬衫、西裤,衬衫外还套了一件蓝色的马甲,算是既正式又随意,也许想表示我们这些人都是可靠、亲密的研究所“核心层”。
“前天,各位已经出席了我们社会学院研究所的成立大会。当然,在那样的场面里,也无非就是说几句振奋人心的‘官话’而已。”胡安被自己的幽默逗得哈哈大笑。“今天,当然要和各位管理层成员交个底,说两句大实话。的确,研究所是成立了,不过在座有几位也许还有些困惑,我们的主要研究方向到底是什么?确实‘研究所’这三个字太含糊了。但是,起这个名字完全是出于保密的需要——我们总不可能在自己门口挂个牌子叫‘密码研究所’吧。”
密码?这太让我感到意外了!
“所以,‘研究所’真正的名字就应该叫‘研究锁’。”坐在我身边的赫德林轻轻地肘击了我一下,挤眉弄眼地窃窃私语。
我仍然有些错愕,突然感觉自己仿佛升到了半空之中,俯瞰着我们所身处的这栋大楼,一幢“锁型”的办公楼,银白的“锁钩”反射出一道阳光,刺得我眼前一片空白。
虽然没听到赫德林说了什么,胡安还是忍不住白了他一眼,然后继续道:“研究所的成立,是院长先生亲自‘拍板’的。当然,这其中赵副所长的建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郑重向各位介绍一下,赵副所长之前在心理研究所工作,是一位多年研究潜意识的心理学专家。所以,下面我们请他来讲一下未来我们的具体工作。”
这个满洲人猛然站了起来,给大家鞠了一躬。他长得五大三粗,浓眉大眼,说话带着浓厚的鼻音,可气息确实“娘炮”的:“感谢胡安所长,下面我来说两句。鄙人姓赵,之前在心理研究所工作,潜心从事心理暗示、潜意识等方面的研究20余年。”
也许是担心胡安再有不满,赫德林低下头,在自己的智慧手机上按了几下,然后一条消息就传到了我的手机上:“这个满洲人绝对是个他妈的‘大忽悠’。”
满洲人还是在那里热情洋溢地继续“忽悠”下去:“在鄙人此前从事的课题中,通过对于近千名受访者的调查研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人所使用的密码,字母密码甚至是数字密码,往往隐藏着他内心最深的潜意识。于是,鄙人在第一时间将这一成果报告给了院长先生,并且受到了院长先生的高度肯定和重视。”
胡安插了一句:“正是赵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所以院长先生当即决定建立‘密码研究所’,通过对于这个国际上的每一个公民、每一项应用的密码进行监测,筛查出哪些人是潜伏着的、未被发现的、最最可怕的‘危险分子’。”
“大忽悠”与胡安相视一笑,以示感谢,然后继续说了下去。他告诉我们,三个研究中心未来的主要工作就是协调各应用软件服务商,从他们那里获取用户的密码数据,并且进行分析。
至于三个研究中心分工上的差异,赵解释说:“在我的故乡瓷娜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一千多年前,瓷娜国曾经出过一位清官,当时的皇帝赐他‘御制三铡’——龙、虎、狗,分别用来对犯下滔天大罪的皇室宗亲、高官大吏和平头百姓处以极刑。所以,在鄙人的建议下,研究所也分三个研究中心,分别调查目前处于核心层的国际领导、组织上有意培养的储备干部以及其他的普通公民。这也就是以后各位的分工。所以,院长先生、胡安所长以及鄙人,希望各位同仁效仿我的故乡历史上的那位清官,绝不放过每一个可能威胁到国际安全的可疑分子。总的来说,第一中心的工作性质最为严肃,第三中心的工作量最为繁重——不过,三个中心的工作对于整个研究所来说,都非常之重要。”说到这里,赵补偿性地看了我一眼,这也是我和他的第一次对视。
宣布散会的时候,胡安特别强调:“请各位注意会议纪律,今天我们会上所说的一切请务必确保不能让任何人知晓。至于你们的属下,绝大部分人只是负责日常的数据接收和维护工作,但对数据是什么、派什么用场,绝对一无所知。”
研究所?狗屁。竟然真的是“研究锁”!散了会,我越想心里越觉得不是滋味。我原本以为调到这个地方来,是继续搞“研究”的,现在倒好,真的成了“研究锁”的小偷了。真想不到,堂堂国际最高级别的研究机构,竟然一本正经地建立了一个分所,专门做此等鸡鸣狗盗之事。
我承认,在我的童年曾经有过那么一次不光彩的偷窃经历。我偷偷记下了母亲的电子商城和电子银行密码,悄悄为自己买了几样男孩子都会喜欢的玩具。那实在源自一个少年的“幼稚病”,我以为只要设置好适当的收获时间和地点就可以瞒天过海。可是在我“下单”的第一时间,订购通知、银行账户的金额变动通知,就足以让母亲知悉一切。后来,她只是改掉了自己的密码,也并未特别责怪自己少不更事的儿子。
经过那件事,除了感到羞耻之外,我还意识到,在这个数据时代,一个人甚至没有行窃的自由。但现在,我觉得这个想法错了。
这时,我的智慧手机又响了。文字传输软件显示,赫德林一口气给我传了好几条消息。
那个姓赵的家伙,是一个在心理所被人鄙视了一辈子的“傻鸟”。眼看着混到快50岁穷途末路了,突然祭出了他们满洲人善于“忽悠”的绝招。
什么一千多年前的清官,还什么“御制三铡”,这家伙也太能“忽悠”人了吧,谁知到真的假的?瓷娜国早就被分成东部的八九个省了,他们的历史还有谁搞得清楚。连瓷娜语输入法都被禁止使用,都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满洲人能来事儿的本事倒是真的。听说一百年前,他们的祖先,能在路上随便拦一个正常人下来,说他腿脚有毛病,把一对拐杖高价卖给人家。
话说胡安和老张真能“忽悠”,就这么个狗屁发现,搞起了一个整个研究所。两个人都升官了。我们也跟着“鸡犬升天”了。
说实话,这种“二逼”的研究,最多也就算个“项目”,搞个临时课题组就成了,竟然让他们搞出来一个近百号人的常设机构。最多忙几个月,以后就天天在办公室闲得“蛋疼”吧。
不过老兄,这他妈绝对是个美差,我们的好日子就要到了。
我心烦意乱,面对着赫德林扑面而来的“信息攻势”,又无可奈何。
我在智慧手机上按了几下,给他回了一条消息过去:
呵呵。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那位建筑师朋友。锁型大楼、研究所以及“研究锁”——现在,这幢大楼在外形、结构以及象征意义上终于实现了完美的和谐统一。可是,这他妈都算是怎么回事儿啊?
我抬头看了一眼办公室60英寸大的触摸屏。它开着,久未使用,于是屏幕上滚动着“屏保”内容,什么“热情庆祝社会学院研究所成立”啦,院长先生的亲笔贺信啦,研究院的行政结构图啦,晃得人发晕。
我仔细打量我的办公室,五六十平方米的宽敞空间,有体面的办公桌,高级研究人员才有资格配置的触摸电脑,价格不菲的真皮沙发,做工考究的实木茶几,甚至还有一个小隔间,里面摆了一张床,供我疲劳或者百无聊赖的躺一会儿。
这里曾经是我在“编译锁”的上级的房间。现在我成了这间办公室的主人。
我不禁哑然失笑。
因为正对着触摸屏,考虑到也许有人像曾经的赫德林一样,正躲在一个小房间里对着监视器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决定把这个微笑保持得更久、更自然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