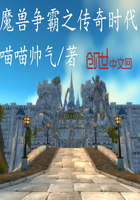“你先说。”西门笑着对张琦说。
“你二哥怎么姓陶,陶总我可是早就见过了,他不是北京里面做文化产业吗。”张琦问。
“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的时候,二哥就改了姓,随他母亲,这几天二哥一直在做文化产业,相当有成就,西门大哥估计也和我二哥认识吧。”
“何止认识。”西门叹口气说:“难怪老陶近几年一直有点抑郁,那个脾气倒是突然转变了,没那么强势了。我和他算是老朋友了,前几年他搞影视,我们认识的,一起合作了几部电视剧,上个月他说有个剧本很适合我,说是一个大导演的创意,我们谈了几天,最后我没接,那个大导演实在有点自以为是,我很难和他沟通,后来你二哥觉得占用我那么多时间,最后泡汤了,很不好意思,一定要请我一起去海南度假,我绕不过他,和他一起玩了几天,那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案件呢。”
“必须要孙悟空消失!”曹尔文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什么啊!”西门苦笑。
“你没看过《七龙珠》?别看我年纪一把,可是漫画粉丝。”曹尔文笑着说:“孙悟空总能打败坏人,所以他身边总出现超级坏人,最后神说,必须要孙悟空消失!他是地球的不安因素。”
张沛东笑了,他也看过这部经典的漫画。
“你说的有道理。”西门自己也点点头,然后说道:“也有读者问我,凭什么你就能遇到那么多案件,换句话说,案件跟着你走,我想了很久,终于搞明白了。”
“那是为什么?”张琦问。
“这样说吧,比如别墅外面有一对情侣,你们知道吗?小张一定知道。”西门说。
“对,厉害,西门大哥怎么知道的?”张沛东问。
“那个房车门紧闭,里面的灯开了又关,这天气,这么好的别墅,不进来却躲在车里,自然是亲密的情侣。”西门道。
“就凭这些,你就认定是一对情侣?”曹尔文不信。
“当然不是,哈,我和你下棋的时候看到有个漂亮的女人从车里出来,看了看天气,又回去了,还对车里说着什么。”西门笑着说。
“难怪。”张琦也笑了。
“那是市里一把手的女婿,叫徐刚,刚买了房车,开到我们这里宿营,他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张沛东苦笑着说:“出车祸,酒驾,他系着安全带,他老婆没有,所以他重伤,老婆死了,刘书记挺烦这个女婿,可想而知了,就一个女儿,没了,这女婿可是天天借着老丈人的名头,吃香的喝辣的,挺自在,这次又发了一笔小财,出来显摆,那女的我以前也没见过,看上去挺健美一个美女,比我还有劲。”
“你看,”西门满意地说:“这就是一个案件,只是你们的忽略让他不存在。”
“有道理啊,这就像我们考古,你要是认定了往北面走,那么东西南三个门就算开着,你也看不见。”曹尔文笑着说。
“本身我还以为很清静呢。”张琦无奈的说:“没想到人挺多。”
“哎,也是凑巧。”张沛东笑了笑。
又有人来了,给张沛东打电话要开门,西门看看手表,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厨师是个年轻瘦弱的女孩,她撤走残羹,只留下茶杯和茶壶。
张沛东,出去开铁门。
突然,天空一阵闷雷。
“你说是迷信吧,也真凑巧,”曹尔文说:“不孝顺的儿子,会伴着雷。”
“还真是罕见,”西门拉开窗帘的一角,看了看天说:“下雪了,下雪天很少闪电的。”
西门的话音刚落,一道闪电照亮了他刀锋般的脸。
“下雪了!”张琦颇为兴奋的走到窗前。
“咱们回去喝茶吧,不妨碍他们一家人重逢。”曹尔文起身离座。
张琦跑出用手机拍雪景去了,西门和曹尔文走上自己的客房,来到通用的阳台,坐下来喝茶聊天。
不一会儿,有人敲门,西门去开门。
“通!真没想到你在这儿,意外,真意外。”陶铸有个习惯,对于熟悉的朋友,他只叫一个字。这点白方最讨厌,因为到了陶铸嘴里,他叫做方,听上去像女孩的名字,于是白方也拿来主义,他叫陶铸铸!发音略向某个动物靠。
“我才没想到这里是你的老巢,我说老陶,你还真是狡兔三窟。”西门请陶铸进来,一起来到屋中。
曹尔文也从阳台出来和陶铸打招呼。
“曹大师也在啊,哈哈,正好,听说你们没喝酒,我拿瓶珍藏来一起品。”陶铸拿着一瓶洋酒,打开,顺手从桌子上拿了两个茶杯倒上酒,说:“每个房间两个茶杯,我就用瓶子吧,基本上能均分。”
“你也不问我们喝不喝就倒这么多。”西门假装不愿意。
“你少来了,你晚上不喝酒?能睡着么?你看这一箱酒,还都是不错的好酒啊,西门你真舍得,不!一定是别人送的,你平时二锅头就搞定了,一瓶都能喝三、四天。”
“是啊!经济实惠,第二天不会头疼。”西门笑了。
“曹大师也是海量,前天在招待所,我看那几个专家都不行了,曹大师还是神采奕奕,末了我看都翻了,县委那几个人都是久经沙场,都不行了,我见曹大师没回去,一个人雨中遛弯儿去了,真厉害。”
“是啊,我也是就贪恋这杯中物。”曹尔文笑道。
“啥也别说了,来吧,走一个。”陶铸对着酒瓶,咕咚一大口,喝完以后,环视四周。
“是不是恍如隔世啊。”西门看着陶铸的表情。
“是啊,七年前,我就住在这个房间,变化不算大。咳!往事历历在目。”陶铸的表情实在难以形容。
“你这个人不厚道。”西门也喝了一大口,加上先前的红酒作祟,此刻也有了几分醉意。
“怎么说?通,我对你还不厚道?”
“咱们去海南那天,雷雨交加,我要是知道你的历史,绝不出门。”西门借着醉意,双眼紧盯陶铸的神情。
“嗯,你知道了,哎,这个老四,一喝点酒醉酒不把关,什么都说。”
“没有啊,说了,但是你弟弟滴酒不沾啊。”西门道。
“不可能,这小子自称艺术家,能把酒戒了,打死我也不信。”陶铸道。
“真的戒了,”曹尔文笑着说:“到这里,现在是第三次喝酒了,前两次他都在,能忍住,说明他的确不喝酒很久了。”
“邪门了,”陶铸苦笑,说:“时间真的是能改变很多事情,我曾一度以为,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伤心地啊。”
“是啊,我无法想象你当时经受了多大的打击,”西门叹了一口气说:“咱们认识快十年了,说实话,最开始我很讨厌你,太强势,脾气也是在火爆,那时候咱们合作过几次,对啊,我亲眼见你对自己当时的女友发火,基本上快演变成家暴了。”
“那一次啊,你知道,我这个人……”
“你这个人最无法忍受别人对你的欺骗,哪怕是善意的,这点我十分了解。”西门笑着说。
“是啊,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成家,现在的爱情中,欺骗太多,我也不想对不起别人,更无法承受别人对我的欺骗。”陶铸苦笑着说。
“可能和你的地位有关。”曹尔文说道:“人一旦有了钱,他和别人之间的关系就变了。咱们中国人穷惯了,有时候太有钱,反倒是坏事,压不住啊!”
陶铸的脸色突然变的和难堪,难看的让人同情。他用酒瓶和曹尔文碰了一下,仰头喝了几大口酒,放下酒瓶,把气喘匀,还没张嘴,眼泪就流了下来。
“怎么了。”西门用手轻拍陶铸的脊背。
“曹大师说的话,和我父亲一模一样,那天我父亲也是这么说的。”陶铸用手掌抹去眼泪,缓和了一下心情,继续说道:“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可能就是钱烧的,太自大,加上父亲是有点絮叨,每次说不上几句,就吵起来,现在我一想起这些事,肠子都悔青了。”
“难怪你从此改变了性格,变得那么淡然,以至于我都自愧不如。”西门抿了一小口酒,问:“你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件事。”
“事发后的一个多礼拜,我那天和父亲吵架,愤愤而去,哎,没回老家几天,就和父亲闹翻,我本来想接他们夫妇俩出去,到北京去,也有个照应,我父亲不愿意,他可能喜欢这种一家人窝在一起的生活吧。”
“你和你的姐弟们关系不好吗?”曹尔文问。
“嗯,您怎么知道?老四说的?”陶铸问。
“不是,我觉得你不太喜欢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从你的语气中,听得出来。”曹尔文道。
“我们这个家族啊,”陶铸叹口气说:“本来我母亲一直没有生育,以为没希望了,过继了我大姐,是我舅舅家,他家孩子多,又生了女儿就不怎么喜欢,过继给我父亲了,那时候我大姐都记事儿了,来到我家,反正是有点倔,我妈说,开始他们努力想改变大姐的性情,对她极好,再说我父亲做生意那时候已经小有成就,家里条件也好,慢慢的我大姐,也就把他们当亲生父母了,不料有了我,我们相差七岁,我大姐从小就不喜欢我,可能是我的到来让她失去了很多关爱。”
“也是个苦命的人。”曹尔文摇摇头。
“她后来很孤僻,一直也没结婚,性格所至吧。然后我母亲去世了,老爷子哭的什么似得,可是没两天就娶了现在的阿姨,又生了三个孩子。那时候这个家就算是一台戏了,我高中就住校了,不怎么回来,后来大学去了北京,然后混呗,写点剧本,搞点策划,觉得自己差不多了,现在想想,那时候真青皮,拿着钱,回来盖了这别墅,特显摆吧,现在看也不过时。”
“不追潮流,就永不过时。”西门说。
“是什么让你有勇气回来呢?是那个古墓?”曹尔文问。
“是一个梦,您信吗,我父亲给我托了一个梦。”陶铸郑重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