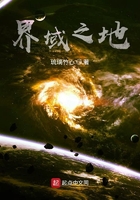这炸药的次序,就像是电路的串连一样,点着一个,其余的都会次序有递的逐个炸响。等人们都藏到了安全的地方,花太岁才把最近的一个炸药点燃,然后飞快的跑开了。
直到一支烟抽完,人们也没听见预想中的满山炮声。哑炮?如果说有一个两个的炸药没塞瓷实,也说得过去,可是这百十来个炸点都没响,事情就有点玄了。
花太岁骂了一声娘的,就从一处山崖下面闪出来,直奔最近的那个炸点。
还是领头的那个工人急忙就抱住了他的腰说:“老板,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平时咱可没出现过这事啊,再说,咱的炸药都是昨天刚炒的,雷管也没返潮!”
花太岁也是有些惴惴,骂了一声,还是返回了掩体。
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树林里的天似乎黑得还早。已经有晚归的鸟儿落在树杈上的窝边,聒噪个不停。远处的那棵杜梨树也呈现出一片朦胧。
花太岁怒道:“他娘的,白天炸不掉青衣岭,夜里加班也要平了它!”一边说一边钻出来,就要向前走去。这时只听呱呱两声,一只乌鸦从上空飞过,不偏不倚正好拉下一泡鸟屎,落在了花太岁的头上。在这一代流传着一个谶咒,说是鸟屎拉在了人的身上,这人三天内要走霉运!
花太岁不怒反笑:“哈哈,我他娘的三天死了两口子,难道还有闭着更倒霉的吗!”一边说一边走向了那最近的炸药点。
最近的炸药点,距离杜梨树不过有数尺之遥,等花太岁大步走到炸药点时,刚跪下身来查看哑炮的原因时,就听见头顶的杜梨树上一声冷哼,这一声冷哼甚是熟悉,使得花太岁头上的鸡皮疙瘩骤然起了一身!不错,正是青衣的声音!
花太岁一抬头,就见一个浑身缟素的女子正坐在树枝上,冲他诡异的冷笑。花太岁大骇,知道中了道了,便急忙拔腿,那只双腿却像注了铅一般寸步难移!花太岁张口冲后面的人喊道:“快救我!”
然而,他刚说出这句话,就见青衣冲他奴了奴嘴,露出轻蔑的一笑,转身便忽而不见!
“轰嗵!”一声声巨响之后,人们便远远地看见,花太岁就湮没在那一阵声浪骇人的爆炸声中……
许久,许久,当硝烟渐渐散去,一轮不太明亮的月亮竟然爬上到了头顶,惨淡的月光下,整个青衣岭像被翻了个遍,炸翻的泥土仿佛露出猩红的亵衣,到处散发着炸药的呛鼻味道,那棵近在咫尺的杜梨树竟然丝毫无损,依然屹立在青衣岭!
众人疯了般的往山下跑去,谁还顾得了化太岁的尸体?其实在巨大爆炸的冲击波作用下,花太岁的尸骨恐怕也早已化为齑粉,荡然无存……
就在花太岁殒命的档口,我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从镇上回来,我就浑身酸软。两只眼睛也粘滞的睁不开,胖三和吴莫离把我扔到炕上,我整个人就像一团煮糟了的面条,瘫软在那里,连身也翻不过来。
爹娘很是愤怒,也没有给胖三和吴莫离好脸色。甚至还气咻咻的说:“吴莫离,要是我家小子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给我摔老盆!”
吴莫离说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因为我只看到,米蓉正笑吟吟的走到我的面前,递给我一张黑色的证件,对,就是黑色的证件!
结婚证!
黑色的结婚证!
米蓉你不是死了吗?怎么……我稀里糊涂的问了一句,米蓉没有说话,只是走过来,轻轻地抚摸了我的一下头,便把证件塞到我得手里,米蓉一转身,恰死扯着一条引线,我便像一只摇曳不定的风筝,跟着她亦步亦趋的走了出去。当时我感到很奇怪,身子怎么轻飘飘的?心里也有种释然的解脱,仿佛尘世间的纷扰像一块巨石一下从身上掀开来去,说不出的爽心惬意。
吴莫离和胖三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低头站在门口,任凭我爹娘的训斥,我不禁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最起码没有人家胖三的责任啊。我站在爹面前,说道:“爹,这不管人家的事,是我自己执意要去的!”然而,我爹好像没听见我在说什么,依旧在絮絮叨叨的编排俩人的不是。可这俩家伙对我真不错,春天里捉蝎子,这俩人领着我在山上转悠一整天,到了夏天,这俩家伙带着我在村西的王八坑一中午不上来,虽然挨了几次呛水,但在这俩人的教导下,我也练就了一身潜水的好本领。所以,这俩人在村里与我的关系还是非常铁。
而今看着爹一劲儿的冲他俩发飙,心里也是有些过意不去,便转过头,想乞求娘劝劝爹,不要在难为这俩哥们了,可是一转头,我却看见了奇怪的一幕,自己的身体竟然还好好的躺在床上……
这时我忽然觉得眼睛一黑,脑袋一懵便不复再有记忆了。当然这之后发生的事,是以后胖三和吴莫离告诉我的……
等爹把这俩人训斥个狗血喷头,胖三才和吴莫离俩人灰溜溜的离开了。
路上,吴莫离还埋怨道:“胖三啊,你也吱一声,要不是咱俩把修言从上套上拽下来,这小子怕要嗝屁了,这个老杜,真让吕洞宾伤心!”
胖三笑笑道:“要不是你把人家鼓动到镇上,人家会青衣岭遇邪?还会差点搭了干白菜?”
吴莫离嘟囔了几下便不再说话。
因为俩人还未走远,这时,就听见后面不远的我家传来爹娘的阵阵哀嚎:“老天啊,我们这到底是做了什么孽啊……”
俩人一怔,胖三道:“八成是出事了!”说完便转身往回跑。
一进家门,就见我直挺挺的躺在床上,脸色青紫,却带着笑容。吴莫离还偷偷地把手指放到我得鼻子下,待察觉没有了一丝气息之后,也是大骇,转过身,不知所以的看着胖三。这时,爹娘冲过来,揪住吴莫离的头发就是一顿猛揍。那吴莫离为了在外貌上更加接近道士,这一头长发都蓄了好几年了,爹娘抓起来也是十分顺手。娘一边收拾吴莫离还一边哭骂:“都是你这个长毛贼,要不是你撺掇我儿子去吊孝,我儿子能把小命丢了吗?”
吴莫离也知道闯下了滔天大祸,任由爹娘打骂也好不还手。这时,一边的胖三辩解道:“这也不能完全怨莫离,葛秦鉴昨天不是说了吗,修言这三天会有性命之虞,这一切恐怕都是命中注定!”
我爹怔了怔,擦了一把眼泪,发疯似得喊道:“快去找葛秦鉴,他一定有办法!他一定有办法!“
那时的光景,约摸到了晚上七八点钟。那晚的月亮不是很亮,昏黄,有些惨淡。昨天被二奶奶毁坏的电力设施已经恢复,可是二奶奶带来的恐惧尚在,所以在平时还串门唠嗑的乡亲们这时已经大半睡下,我爹的几声哀嚎,顿时为这寂静的夜有平添了几多恐怖,就连平时喜欢汪汪的狗也夹着尾巴,钻到了狗窝里,惊恐的发出低低的因为恐惧带来的呜咽。
等胖三和吴莫离深一脚浅一脚的跑到蟒头沟的时候,葛秦鉴早已睡下了。吴莫离气喘吁吁的用力拍打着屋门:“师傅,出事了!出事了!”吴莫离的慌张,惊得羊圈里的几只羊扑棱棱的站起来,歪着头,一脸茫然并夹带着些许惊恐。
因为这里地处偏远,又到处林密沟深,所以,葛秦鉴的屋里没有电灯。
时辰不大,葛秦鉴擎着蜡烛,从屋里披着衣服走了出来。
吴莫离上前就要跪倒,却被葛秦鉴用脚尖及时地勾住膝盖:“男人膑膝,只跪至亲,只跪师道,只跪天地。我一样也沾不住,万不能承你百斤之躯!”
吴莫离甚是着急,一连催促道:“师傅,快救命,人命关天!”
看来这小子是真怕了,是啊,老杜一没生恩,二没养义,他可不想给老杜摔老盆。
葛秦鉴倒是十分痛快,说了声稍等,便回了屋里。时辰不大,一身道袍,头绾发髻,方鞋云口,身背挎包,形体虽略显清瘦,但精神却昂扬勃发的葛秦鉴道长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吴莫离讨好地上前要替葛秦鉴背包,葛秦鉴愣了一下,笑了笑,便把那个挎包随手递给吴莫离。吴莫离也是随意的接过那件毫不起眼的挎包,却身体一侧歪,乒地摔倒在地!胖三一边拉他一边奚落道:“你这心瞎,眼也瞎?连路都不看!”
吴莫离似乎很是惊讶,冲胖三连连摆手,并指着那个挎包。胖三疑惑了一下,便弯身想要把吴莫离摔落的挎包拎起来,胖三这家伙,岁数不大,可是工作的使然,那一嘟噜一嘟噜的好下水哪个不是先塞到他的嘴里?二百多斤的体重,几乎把他吹成了圆球。身大力不亏,那时,村东打麦场里的石头碾子,怕不下三百来斤,他一个咯吱窝夹起一个,绕着村子能转上一圈半!是附近几个村有名的大力士。胖三抓住挎包的带子,随手往起一提,不由咦了一声,于是又腾出另外一只手,往上一提,挎包还是纹丝不动!胖三看了一眼吴莫离,吴莫离幸灾乐祸。看了一眼葛秦鉴,葛秦鉴无动于衷。这下倒激起了胖三的无边豪气,他再次双手抓紧挎带,大吼一声,粗壮的脖子里顿时青筋暴起,嘴巴也夸张的张成了O形,但那挎包也只是轻微的离地寸许,便再也不能提升半厘!
胖三很是尴尬,红着脸站到一边,而葛秦鉴却是露出赞许的目光,要知道,一个凡人能把这载满乾坤日月,盛满山川星河的阴阳袋拎起地面,那着实不易!
葛秦鉴笑了笑,捡起挎包,自顾大步向村里走去。吴莫离和胖三急忙跟在后面。惨淡的月光下,密匝的山林里,这一中两青三个男人随着踢踏踢踏的脚步急急的走在山路间。
路上,葛秦鉴不时地询问了一些关于青衣岭的一些故事和今天白天在花太岁家发生的一些事。
有话路不长,无话路嫌远。工夫不大,葛秦鉴一行三人就到了我的家门口。家里此时早已经聚集了前来帮忙的村民,一半是来看热闹的,一半是来真心攒忙的。
葛秦鉴来到屋里,我爹早已迎了过去,冲着葛秦鉴就能跪下了:“先生,悔当初不听。
圣言,今天果然小儿殒命,还求先生不遗余力,施妙手神通,救活我家娃儿!”
众人早知葛秦鉴的能耐,急忙有人递凳子倒茶水,无不恭敬谦卑。
葛秦鉴叹了一口气道:“我昨天就见他印堂之中有一缕邪气,早知他近日会有恶鬼缠身,本想将其留在我处三天,等霉运过了再放他回家。可惜老哥哥你不容我细说就一口回绝了我啊!”
说着,葛秦鉴就来到我的炕前,伸手扣住我得寸关尺三脉,双目微闭。少顷,便睁开眼睛,从挎包里掏出一张黄符,贴在我的炕头的墙上,那些符咒正好面对着我。葛秦鉴嘱咐我爹道:三魂已去其二,七魄已丢其五,能就不能就,就看这张符了,千万别让它掉了!”说完一转身道:“走!”
胖三和吴莫离连忙追出来道:“师傅,这大半夜的咱们去哪?”
“青衣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