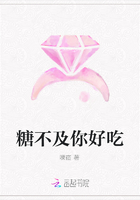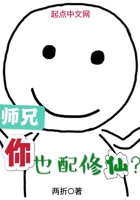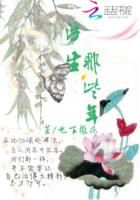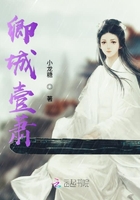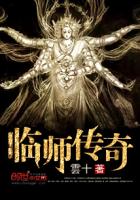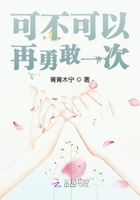在中国古代严格封闭的等级社会里,连贵族阶层也要位分五等:“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礼记·王制》)策士们多为布衣,和“王者”之间在地位、认知、利益上差距甚大。他们借助娴熟的语言技巧,构建起了双方广泛接受的共识域。苏秦初将连横说秦王时,因为和秦王没有建立起共识域,才“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后来,“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扺掌而谈,赵王大悦”。(《秦策一》)苏秦为什么先败后成功呢?根本原因还是建立共识域的问题。其实,建立共识域是公关语言的语用前提,如果建立不起共识域,语言信息就会在传送中受阻。反过来说,共识域又要靠语言信息来构建。当然,共识域的建立,须以双方的共同利益为前提,如果双方在利益需求上差距过大,共识域也就很难建立。对于这种利益共获,策士们有比较明智的认识。纵观《战国策》,策士们分两大阵营,一类要连横,一类要合纵。两大阵营的公关活动,是以和公关对象建立共识域为焦点的。《秦策一》中记录了司马错与张仪的一场辩难。在当时秦国的攻伐对象是蜀,还是韩、周的策略性问题上,两人的意见针锋相对。张仪主张伐韩劫周,“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而司马错则认为“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言深得惠王之心,“善!寡人请听子”。能言善辩的张仪败给司马错的根本原因是司马错的意见符合当时秦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容易和秦王建立起共识域。
现代公关活动中共识域的建立,是“沟通双方以类似的经验为条件,这种类似的经验越多,其(共识域)越大,沟通的共同语言也就越多。”(潘肖压《公关语言艺术》)不难看出,共识域的建立是指双方在平等基础上的有效沟通。
战国策士们以单向沟通方式和对方建立起了广泛的共识域,体现了他们在语言运用上的一个突出特征,即“说”。《说文》云:“说,释也。”荀子也曾言:“说不喻然后辨。”(《正名》)许氏和荀氏的训析,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策士们“说”的语言特征。其一,说服。战国时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特定阶段,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们为其所辅佐国的兴盛和个人功名利禄,凭借聪明才智,机变权谋,到处奔走游说,“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足见其游说不是一般意义的说服,有特定的运用模式。首先要“度时君之所能行”,审时度势,也就是首先要建立起一个共识域,靠利益的关联来说服对方。“诸侯力政……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说”是一个艰难的语用过程。策士们既要获得诸侯的赏识,又要入情入理地阐发各种观点。“说”作为策士特殊的语用形式,他们把这种方法运用得游刃有余,警策、譬喻、据典、曲文,各尽其妙。正如刘勰所言:“乐毅报书辨而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文心雕龙》)“说”成了战国策士的专用语体。其二,诡辩。把逻辑手段运用到“说”中,就发展出一种全新的说辩艺术。“辩”是从普遍的原理出发,经过正确的推导,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或者依据一定的方式,通过对个别事物的分析,归纳出一般的结论。战国策士把“辩”有效地用于驳论辩难中,增大了“说”的力度。虞卿阻割六城与秦(《赵策三》)就是“辩”之成功的范例。需要指出的是,策士们在辩难过程中,多发诡辩。诡辩是一种转移话题,避实就虚,强词夺理,投机取巧的语用形式。策士们连横和合纵两大阵营,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都竭尽全力想方设法说服对方,有时就难免使用诡辩术。再加上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更使诡辩术有了滋生的土壤。对于诡辩,也不能一概加以否定。诡辩作为一种语言技巧,用在公关活动中,有事半功倍的语言效果。对策士们的诡辩术,我们也应该结合语用环境分别对待。策士们有危言耸听、强词夺理之辞,也不乏避实就虚、审时度势之语。“诡辩”增加了说服的功效。笔者把“说”看作战国策士的专用语体,正是因为他们建立了这种游说模式,而且使用得娴熟得当。“说”是在特定的目的、对象和语境的制约下有层次、有特点、有质量的说服语用过程,它已经从一般意义的劝说中脱颖而出,形成一种有特色的体系和较完整的语用模式。
说服的过程是语用的综合过程,说服的结果是语用的结果。战国策士的语言既铺张扬厉、雄辩恣肆,也不乏婉转含蓄和巧比妙喻,具体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邹忌讽齐王纳谏(《齐策一》)巧寓事理,类比精当。冯谖说孟尝君(《齐策四》)言简意赅,质朴无华。张仪说楚王连横(《楚策一》)夸饰铺陈,持论恢弘。莫敖子华谏楚威王(《楚策一》)曲婉迂回,含蓄藉蕴。公关活动对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触动功能有较高的要求,它要求语言是一种流动的载体,信息在流动状态中不断传送和反馈。语用正是语言流动的推进力。语用的结果,使语言的普通用法在流动中加大了信息载量,从而产生激励效果。警策。警策是一个范畴广泛的语用现象,它的基本特点是:第一,警示性。精辟的分析给人以某种告诫和启示,预见事物的现在或未来结果,达到劝诫的目的,对对方的行为有牵制和导引作用。第二,策动性。由警示而产生的鼓动力、激发力。除了以上两点之外,还应该再加上一个夸饰性。即通过故意超越客观事实的说法来强调自己的思想,以激发对方行为。
战国策士经常采用这种手法,它能产生较强的激励效用,增大语言信息长度。这种激励效果指语言符号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内在激发力量。警策语以其持论恢弘和寓蕴哲理的特征最容易产生激励效应。鲁仲连劝田单攻狄(《齐策六》)分析透辟、论说深刻,用的就是警策手法。但是,战国策士们经常夸饰过当,他们往往故作警策,危言耸听。张仪说楚绝齐(《秦策二》)用的就是这种说法。夸大之辞,富于刺激性、鼓动性,也具有欺骗性,应该批判地对待。
刘勰云:“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文心雕龙·谐隐》)“遁辞”就是用婉转的语言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用在公关语言中,是对语言的软化处理,创造出舒缓的信息传播氛围。委婉的语用出于多种原因,为尊者讳,是战国策士委婉语用的根本原因。策士们和各国君王尊卑悬殊的地位,使他们不能直言,需要采取拐弯抹角、委婉曲折的方式来表达。本意要和春申君成知己之好,但他并不直言,却用骥服盐车这样一个相似的事物来烘托本旨,委婉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愿。这种交际过程中迂回、曲婉、含蓄的语用现象,避开了双方的冲撞。战国策士的公关以外交公关为主,他们的许多公关语言,堪称绝好的外交辞令。古人对外交场合的言辞十分重视,“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这个“命”,指的就是外交辞令。外交辞令讲究分寸,有文采而又婉转含蓄,策士们大多因境临时而发并运用得恰如其分,足见其深厚的口语功底。外交辞令对语言的情景化有更高的要求,受特定的时间、场合、对象等外围条件限制,策士们也因时、因地、因人而变,或讳饰、或借喻、或曲语,最终达到理想的公关效果。
巧比妙喻,是战国策士语用的又一显著特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分析这种妙喻中的隐含信息。比喻的主要作用,是为了使所要描绘的事物更具体,更生动,更形象。战国策士常用比喻说明事理,更能达到理想的公关效果。邹忌讽齐王纳谏(《齐策一》寓理于喻,鲁仲连义不帝秦(《赵策三》)巧设喻体,陈轸止昭阳攻齐(《齐策二》)借喻明理。用比喻方法传送信息,是以形象的方式让别人获得精神上的快感。比喻的力量,在于润滑了人际关系,减少了信道摩擦,扩大了信息内涵,提高了信息传播质量。策士们很善于借题发挥,把比喻引入论说主体,把真实信息隐含在喻体之中,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颇富感染力和说服力。策士们为了增加语言的激励性,除了运用一般比喻外,还经常把自己的某种主张隐含在一个寓言故事中,构成特殊的比喻形式。诸如狐假虎威、画蛇添足、鹬蚌相争、南辕北辙等,是《战国策》中有名的寓言,对后世影响也很大。这些寓言,设立了一种形象的语言情景,却实际上阐发出了某种令人信服的事理。
警策、委婉和比喻的选择,都建立在语言心理学基础上。一方面,公关行为过程本身就是心理交接过程;另一方面,汉民族的许多文化心理素质对汉语词语产生了深刻影响。反映在语言运用上,汉语中的谦辞、敬辞十分发达。而中国封建社会等级观念又导致了大量尊辞和卑辞的产生。“克己”的传统信条,造就了内向和含蓄的个性特征。这是汉语以含蓄为美的心理学基础。对于战国策士,他们也会毫无例外地打上这种民族心理的烙印,这恐怕也就是策士们擅长婉曲和妙比语用的文化心理因素。更何况公关是语言传送和反馈的双边活动,必须深谙对方心理,并以符合这种心理的语用形式传达语言,才能达到沟通的目的。从《战国策》中,我们就能找到许多谦词、警词、卑词、尊词,仅《乐毅报燕王书》(《燕策二》)就有20处之多。这类词语的运用,出于心理需求,容易博得对方的认同。语言和心理本身密不可分,“言为心声”,正此之谓也。
按照公共关系的一般定义,公关是指利用一定的传播手段而进行的一种活动或职能。战国策士们的行为符合这种公关定理的要求吗?表面上看,他们的游说活动似乎是一种个人行为,但他们却代表了一个阶层、一个群体、一个集团,甚至一个国家的利益。他们的行为和公关行为同质。近年来,在方兴未艾的公关语言研究中,忽略了颇具特色的战国策士们的公关语言实践,恐怕在于人们还没有把策士们的行为归属为公关范畴。公关语言学理论的建立是20世纪的事,但是,早在2000年前,孔子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已经开始了公关语言的实践,至于后来策士们游说诸侯,更把公关语言运用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公关语言作为公关形式,它不能不受公关目的制约,不能不以公关对象来取舍语言。战国策士们对此运用得游刃有余。他们投“时君世主之所好恶”,献“奇策异智”,以“取令诸侯”。他们是带着明确的目的和职能来运用语言的。公关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多边活动,这就要求公关语言要具有“随机性”。策士们很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语言运用恰如其分。看来,策士们的语言实践和现代公关语言原理有许多类似之处,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语言规律本来就是对语言实践抽象的结果,策士们的公关语言实践符合现代公关语言的一般特征。
当然,战国策士的公关行为还缺乏系统理论指导,在运用语言上,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一是辩难中的强词夺理;二是陈词时的过分铺张;三是说服时的危言耸听等。这些语言特征的形成和策士们的身份地位有密切关系。策士们出身成分比较复杂,游说目的各有不同,唯利是图、急功近利必然导致语言运用时的不择手段,这也就是策士语言的时代局限性。
《论语》“辞达”观产生的伦理基础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并无意专门探讨语言学说,但孔子及其弟子们在阐发儒家学说的同时,有意无意地表达出了一些语言观,并且把这些语言观运用到具体的语用实践中,这样才使《论语》体现出极高的思想水平和文学水平,无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在语言史上都有了较高的价值。《论语》中的这些语言理论与实践,无疑是建立在自身的思想主张基础之上的。《论语》的语用理论和语用实践,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建立,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其中“辞达”观的影响十分深远。纵观《论语》中的语言理论和语用实践,都和儒家的伦理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辞达”观就是因用而生,因时而发,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