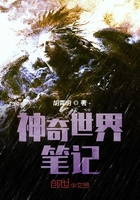我和珍妮依旧坐在咖啡馆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我喜欢这种感觉,我们聊到后来进入了一种毫无戒备,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的状态。我说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喜欢旅行,也许只是渴望自由。珍妮回答,对我来说,早上睡到自然醒,在自己的家中,穿着邋遢的衣服,做自己想做的事,任性的吃下一堆又一堆高热量的零食,那就是自由。
我看向窗外,不远处的花圃颜色已经渐渐变黄,这座小城的颜色从浓绿渐渐转为了淡绿,零星掺杂着几抹淡黄的点缀,也许是因为快要入秋了吧。
所谓的自由的确就像珍妮说的那样,在一个自主的空间里,按照自己的意愿享受生活,这确实就是一种相对的自由。
花圃后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小童。她的表情有些呆滞,双眼无神的看着前方,跌跌撞撞的朝咖啡馆走了过来。
“小童。”
她刚刚走进店门珍妮就朝她挥手,脸上是爽朗的笑容,我再次看到那道疤痕随着珍妮的手在我的眼前来回的摆动着。
“啊,你们怎么在这儿?”小童的表情有些惊讶,做出一个退缩的姿势,好像不想见到我们的样子。
“影展人太多了,我们过来这边儿透透气。”珍妮同样看出了小童异样的反应,有些疑惑的追问道:“你,没事儿吧?看上去脸色不太好。”
“没什么,没什么,我,我就是来买杯咖啡,买了我就走。”
“遇到就过来坐坐吧。”
小童支吾着,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
“几天没见了。”我朝小童招手,我对一切可疑的线索都有研究的兴趣,这是我的职业习惯。
小童有些不情愿的在珍妮身旁坐下,她皱着眉,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你到底怎么了?”珍妮好奇的看着小童问道。
“大城市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小童抬起头看着我们,一脸的茫然。
“大城市?”我好奇自言自语道:“大城市啊,每天有做不完的工作,很多的应酬,从早上你醒来的那一刻起,你脑中就会装满今天要做的事情,然后根据每件事情带上不一样的面具,你要在不同的群体里扮演不同的角色,每个人都充满了斗志,为了那看似伟大的追求,从出门的那一刻开始,你就要在堵车,工作,加班,饭局,出差,利益的环境中挣扎,你的欲望会随着所占有的东西不断的膨胀,你会发现自己开始不懂得满足,甚至,丢失了快乐和幸福,就像一个人肉机器,在水泥森林里成长,枯萎和死亡。”
我不知不觉的开始陈述我心中的城市,一边说着,内心却感到有些惊讶,原来城市在我的眼中这么的污浊和负面,曾经心中干净的理想不知何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我想终止自己的表达,却又无法停下,身旁的珍妮沉默的看着我,脸上有种蔑视的神情,让我有些发慌。
“可以啦。”珍妮说话了,有些不耐烦的语气:“不要总是把一切都说的那么肮脏,有时也许只是你自己用有色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罢了,我在夜场工作,但我依旧觉得这个世界是充满人情味的,男人也确实很色,但你不能说好色的男人就一定是个不好的男人,也许在事业上或者友情和亲情的部分,他们是很不错的,不要把城市说的那么淡漠。”
我不知道如何接话,突然感觉到自己似乎是有些偏激的看待这个世界,我有些尴尬的转头看向窗外,扪心自问,我是否真的很期待两天后的旅行?自己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也许我真的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切断我与那所谓肮脏都市的关系,因此可以用一种自以为是,清高自傲的眼神去打量那一个个都市里的蚂蚁,这无非也是一种逃避的方式而已。
“嗯,可能我会去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小童低声说。
“为什么,医院排你去出差?”
小童摇头,看得出她不想再告诉我们任何信息。她的脸上是一副矛盾的表情,好奇,欲望,惊慌,失落。这种种神色让小童显得成熟,曾经单纯的样子已消失不见。
半个小时后,天已渐渐暗下,我们起身走出咖啡馆。刚走到街道上,小童深深的呼吸,她用力的吸入墨江城的空气,好像以后就再也呼吸不到的样子。
岔路口,在我们三人准备分开的时候,小童低声说:“影展结束我也要离开这里了,但这次影展能认识你们真好,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见到,保重。”
还没等我和珍妮做出回应,小童转身快步离去,路灯下,我看到小童的肩膀开始微微颤动,好像哭了的样子,回过神,我看到珍妮看着我,她微笑,同样低声的说道:“我去上班了,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那么脏,再见。”
我一个人行走在小城的街道上,现在观察起这座城市似乎和我刚到时有些区别了。
拨通主编的电话,前方一个老人正带着孙子缓缓的穿过马路,老人穿了古朴的唐装,腰背有稍许的驼,皱纹深浅不一的分布在皮肤上,他拉着孙子的手,一道苍老的皮肤和稚嫩的小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知道这是一种幸福还是凄凉。
电话接通,我听到主编有些不耐烦的声音:“喂?小冯啊,什么事儿?”
“主编,我决定辞职了。”
“嗯?什么?信号不太好,你再说一遍。”电话里,我听主编起身移动的脚步声,还有隐约的争吵声。
“我决定辞职,过段时间我会回来和公司解除合同。”
“什么?什么合同要解除?哪个项目的?墨江城影展吗?款项我们已经收到了啊。”
“不是,我是说……”
“哎呀!别烦!我和小冯谈公事!”我话还没说完主编突然不耐烦的吼了起来,几秒钟后他稍带歉意的说:“不好意思,家里有些事情。”
“又和太太吵架了?”
“是啊,都是些屁事儿。”
“主编,我改天和你联系吧,信号也不好,你说话也不方便。”
“嗯?什么?什么方便?”
“我是说,再见。”
挂断电话,我朝客栈走去。
我不知道自己的哪一个决定是对的,就像曾经并没有想过成为编辑,更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每一次的决定都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虽然之后这些选择被公司和朋友渲染成所谓睿智的决策,其实,很多事也只有自己心里知道,成功与否,运气比智慧占更大的比重。
客栈门口,我看到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站在路灯下,是杨思霖。
当我走到她身旁时,她缓缓抬起头,我看到一个憔悴,沮丧,甚至有些绝望的女人,她的神情与早上展馆时有着很大的差别,如果说早上是一个成功者的表情,那么,现在她看上去就是一个失败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