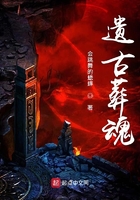真是小看了天下英雄啊。赫连突利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心里却已后悔得似要流血。自己自恃足智多谋,自以为能够看破敌人的用心,而这一点小小的自大却让仆固部陷入了如此惨痛的境地。思然可汗落在了共和军手里,族中勇士大半已成为共和军手中的武器,灭亡了楚都城,下一步自然就会直接与阿史那部对阵。那些五明王、六长老,包括思然可汗自己,还在认为这是个消灭世仇的契机而兴奋不已,唯有自己洞若观火。可是明明已经看破了共和军的用心,偏生又有口难言,这等滋味实在难以忍受。
好在,共和军并没有太注意自己,而这也是自己的机会。只要能抓住这个机会,仆固部就能涉险而过,而且还能借此机会迎来发展壮大的契机。
他的脸上终于浮起了一丝笑意。
信写完了。他将这片帛布卷成小小的一卷,向风刀招了招手,风刀吞下了肉条,飞到案头来,向他举起一只爪子。他将帛卷小心地缠在风刀足上,又轻轻一挥手,风刀立时飞了起来,从他这帐房上的天窗里钻了出去。
西原上鹰隼很多,又是晚上,风刀这样一只小小的苍鹘飞走自然根本没有人注意。赫连突利是这样想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除了不远处一个营帐里的一个人。
那个人身材瘦小,几乎不像个士卒,但一双眼睛却极其明亮。他一直坐在营帐边,动也不动,仿佛身躯都化成了一块顽石。风刀飞出天窗时声音极轻,但同样不曾注意,但当冲天直上时,夜风中传来的轻微声音却还是引起了这个人的注意。他猛地抬起头向上望去,看见了暮色中那小小的一点。
从哪里飞出来的?他并没有看清楚,但下意识地从腰间摸出了一把弹弓,搭上一颗石子,一下射了出去。
石子飞行极速,甚至带着轻微的破空之声。风刀此时正在向上飞,虽然这小鸟已能通灵,毕竟只是只小鸟,石子飞来时觉得有异,身子一侧,还是晚了。
“啪”一下,空中落下了一茎断羽,但风刀只是侧了侧身子,又盘旋直上,消失在夜空中了。那发射弹弓之人眼里闪过一丝懊恼,知道再没有机会了。
会是赫连台吉么?也许只是多心?
他想着,心中只是不住地反覆。在草原上,这种鹰隼之属相当多,不少人还拳养鹰隼,用来捕捉狐兔,也许并不足为奇。他思量了片刻,终于收好了弹弓。
这人正是王如柏去见过的北斗。这北斗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险些就揭破了楚都城唯一一个取胜的机会。正因为这机会实在太微乎其微了,连他也根本没去在意,所以也没多想,而现在,风刀就带着这唯一一个机会向楚都城飞去。
行军需要二十日的路程,风刀这样的苍鹘飞起来也需要好几天,何况这只小小的苍鹘左边翅膀受了伤。只是这只小鸟仍然在夜空中疾飞,仿佛并没有伤口。这只小鸟自然不知道下面这些人类的想法,它只知道主人让自己飞到这里来,必须马上飞回去。
飞到楚都城,已是它从赫连突利营帐出发后的第三日的黄昏了。平时一天多的路程,这一次它足足飞了三天。
将风刀放走的三日里,薛庭轩当真坐立不安。草原上鹰隼很多,有种鹰双翅展开足有一人的长度,可以一下将一只小羊叼走。风刀虽然凶猛,但与那些大鹰相比,依然不是对手。难道会被那些大鹰截下了?他向来镇定自若,但这三天里还是不由自主地焦躁。眼看着这已是出发后的第四天了,他坐在城头,心里翻来覆去怎么都平静不下来。
“庭轩。”
陈忠的声音响了起来。薛庭轩吃了一惊,扭头看去,却见陈忠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他身边。薛庭轩向来警惕万分,旁人走到他身边一丈以内他就能察觉,这次却已魂不守舍,居然陈忠到了他身边还没发觉。他忙站了起来,干笑道:“义父。”
陈忠拍了拍他的肩头,道:“坐下吧。”他自己也在雉堞上坐下了,两人同时望向东边。
半晌,陈忠轻声道:“庭轩,脱克兹撒林的死,也是你的计策吧?”
薛庭轩的身子略略一震。他没想到陈忠隔了好几天还想着这事,刚想否认,却见陈忠目光灼灼,想要否认的话便说不出来,低声道:“正如义父所想。”
陈忠叹了口气:“你这样做,难道就心安理得么?”
薛庭轩只道义父会责骂,没想到只是这般轻描淡写地一说,他也放下心来,小声道:“其实也不全是我的计策。脱克兹安多很有野心,一直想取而代之,我不过是添了把火而已。”
陈忠道:“这个当然。脱克兹部一共也不过两百来个能上阵的,但安多胆子再大,若没有你撑腰,他哪敢这样做。”
薛庭轩干笑了一下。对这个义父兼岳父,他一向都很尊敬,但也只尊敬陈忠的勇力与年纪。在他心里,陈忠也是归于“一勇之夫”的行列。不过,没想到这个一勇之夫也能看破自己的计谋,当然那是因为陈忠太了解自己了。他小声道:“义父,这不仅仅是两百来个兵而已。四部已是一体,脱克兹撒林离心,势必会影响到另三部的决心。”
“可是安多这人能够为了一个区区的族长之位,将自己堂兄都手刃了,这种人能相信么?”
薛庭轩脸上浮起一丝笑意:“好叫义父放心,他的结果我也已经定下了。脱克兹部日后会编入其余三部,不会有什么大碍的。”
西原部落众多,许多部落也是同族之人,分分合合那是常事,依附楚都城的四部便是出于同一个祖先,将来脱克兹部编入其余三部也不是什么异事。陈忠沉默了半晌,低低道:“可是,这样做法,还有仁义么?”
五德营便是以“仁义信廉勇”这五德命名,而仁义两字居其先,更是人人耳熟能详。薛庭轩正想反驳,陈忠又道:“当年五德营在楚帅麾下,以仁义为先,人人景仰,百战百胜。那时并非不曾杀人,可就算是我军的敌人,说起五德营无不敬佩。为将者,当不失仁者之心,不仁者,天诛之。当初楚帅常这么说,如果对人不仁,就算能得计于一时,最终还是会被天地诛灭。”
陈忠不是个健谈之人,这次滔滔不绝,与平时已大不一样。这一席话他实是骨鲠于喉,不吐不快。作为五德营最后的耆老,他一直在心中守护着记忆中的五德营,可是眼看着五德营在薛庭轩带领下起死回生,实力渐强,却与他的记忆越来越远,他也再不能不说了。
薛庭轩道:“义父,仁义何谓?有大仁大义,也有小仁小义,义父你还没想通么?”
陈忠一怔,道:“什么叫大仁大义?什么叫小仁小义?”
“战阵之上,两军对垒,当敌人举刀向你砍来,而你心怀恻隐,不去伤他性命,那便是小仁小义。你不杀他,固然饶了他一命,但他的刀下却要多死几个我军同袍。”
这个道理自然没什么错。陈忠本不善言,不由语塞,又道:“那什么叫大仁大义?”
“五德营被叛贼逼到了这等地步,眼看便要灰飞烟灭,为了这些父老,不论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只要五德营能够生存下来,那么就算我行鄙卑无耻之事,同样是大仁大义。义父,你难道不曾听说过,‘事缓从恒,事急从权’这句话么?”
这也是兵法中一句,陈忠对兵法虽无深研,当初却也曾经听楚帅说过。他再说不出什么来,薛庭轩却接道:“仁义二字,实是要有力量来做后盾。若无力量,那么仁义都是空话了。义父,我所作所为,也许在义父您眼里有不齿之举,但庭轩敢说,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五德营的父老兄弟,为了他们能在这异域活下去。为了活下去,挡我者杀!”
薛庭轩说到最后,已有几分激动,声音也响了些,边上有几个巡视的士兵不由往这边看了看,眼中有惊疑之色。薛帅和陈老将军有了争执!这事可非同小可,难怪他们生疑。薛庭轩这时已明白自己有点失态了,朗声笑道:“义父,你不必担心,就算战到最后一人,庭轩绝不后退。为了五德营的光荣,我死而无憾!”
陈忠脑筋虽慢,却也不是呆子,心知现在不能让士卒觉得将帅不和。他站起来道:“那就好吧,庭轩,你好自为之。”
这时薛庭轩眼里一亮,叫道:“来了!”他向东边打了个唿哨,陈忠扭头看去,却见暮色中风刀更斜斜地飞来。
看着风刀飞行的样子,薛庭轩也心如刀绞。等风刀一来,他伸臂便去接。原本臂上要套上牛皮套,但情急之下已全然忘了,风刀落到他臂上,爪尖透衣而入,已刺破了他的皮肤,他也只觉微微一阵刺痛。但薛庭轩见风刀脚上缠着个帛卷,哪还顾得上别个,伸手便去解。陈忠见他战袍袖子上已有血迹渗出,急道:“庭轩,你手臂伤了。”
薛庭轩已在看着帛卷,忽然大声笑道:“不碍事不碍事,这一回,叛贼已是必败无疑了!”他伸手抚了扶风刀,见风刀左边翅膀有伤,心疼之极,从怀里摸出金疮药来给风刀洒上,根本不顾自己臂上被风刀抓破了还在淌血。
共和军威名远播的三上将,这一次将要尽数丧在西原大地之上!
落日西沉,东边已是暮色一片,他看着这一片暮色,心中的豪气直如一团熊熊燃起的烈火,直欲冲霄而上。
决一胜负吧。
让这片大地浸在鲜血之中,血泊里将会有一个胜者巍然站立。
胜者,舍我其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