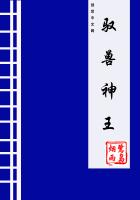阿佳格格被一个声音惊醒了。她睁开眼,也不知出了什么事,迷迷糊糊地只道已是天明,但一睁眼却见周围还是一片漆黑。她伸手摸了摸边上,却觉丈夫并没在身边,不由一惊,正想发问,却听有个人低低道:“是么?好吧,你辛苦了。”
那正是赫连突利的声音。赫连突利连衣服都没脱过,此时才走过来。阿佳格格见丈夫眼里布满血丝,不由心疼,披衣起身道:“突利,你一直没睡么?”
听得妻子的声音,赫连突利笑了笑道:“阿佳,我吵醒了你么?睡吧,我也要睡了。”
阿佳格格道:“出什么事了?”
赫连突利道:“今天,五德营的司徒郁前来密报,说明日大会之上,有人会行刺大汗。”
阿佳格格吓了一跳,叫道:“真的么?让八犬加倍小心。”
赫连突利道:“这个自然。不过,行刺有九成是假。”
阿佳格格又是一怔,马上道:“五德营想要我们和阿史那部火拼?”
赫连突利小小吃了一惊,笑道:“阿佳,你比大汗的脑子可要快得多。”
阿史那部和仆固部本来就是世仇,双方火拼毫不意外,只是双方互有顾忌,所以才能相安无事。现在,五德营这支突然进入西原的力量打破了暂时的均势,阿史那部和仆固部却如铁钳的两个钳口紧紧夹着他们,他们想要打开局面,只有挑拨双方互斗。现在,共和军已经败退,五德营不再有后顾之忧,势必就要开始新一轮的策划了。只是赫连突利一直觉得,眼下阿史那部出手的话,五德营并不能得到最大的好处,所以一直不敢相信薛庭轩会选在这个时候出手。当他派出的细作回来报告说,阿史那钵古所率增援军已在秘密班师,他这才明白这一切都是薛庭轩的计策。
这一次,其实和上一次如出一辙。那一次薛庭轩派死士冒称是前来散播畜疫的中原细作,迫使自己表态站在五德营一边,从而使中原军出奇计劫持了思然可汗,让仆固部当前驱攻打楚都城,最后自己再趁机夺回思然可汗,这样一来仆固部与共和军彻底决裂,完全解决了共和军和仆固部联手这个五德营的心腹之患。那条计环环相扣,自己明明看得清楚,却又不得不跟着薛庭轩的脚步,究其本原,实是自己远不如薛庭轩般不择手段。而这一次,薛庭轩又让人假冒奉阿史那唆罗之命前来行刺,迫使自己第二次表态。阿史那唆罗被胡继棠收买,恐怕是真的,但阿史那唆罗已绝对不可能再听从共和军之命来行刺思然可汗了。薛庭轩想要的,是阿史那部和仆固部的两败俱伤。与其说是阿史那唆罗想要刺杀思然可汗,兀宁说这是薛庭轩想要自己这样去觉得。本来中原军败退后,由于双方都和五德营有联系,无形中阿史那部和仆固部的敌对立场缓和了不少,而薛庭轩的用意,正是让仆固部和阿史那部立刻发生规模不太大的冲突,不希望双方减少敌意。
他想到这儿,再睡不着了。阿佳格格见丈夫仍然不脱衣上床,欠起身小声道:“突利,你还在想什么呢?”
赫连突利勉强笑了笑:“没什么,睡吧。”
他躺下了,心中却依然不能有片刻平静。薛庭轩这人当真是不择手段。现在阿史那部的增援军刚到,因为共和军已经败退,如果任由他们驻扎,阿史那部便要在楚都城反客为主,所以对于薛庭轩而言,这个时候阿史那部和仆固部发生火拼实是最好不过的情况。一来可以让两部实力大减,阿史那部无暇顾及五德营;二来他也不必再践前约去成为阿史那钵古的女婿。第三,则是向周边那些小部落宣告,阿史那部和仆固部都是言而无信,不顾信义之辈,只有他五德营,因为顾及到与双方的睦邻关系,只好置身事外。等阿史那部和仆固部的冲突结束后,不论谁胜谁负,西原列第一位的都将是五德营了。此人出手如风如电,简直不让人有喘息之机,赫连突利越来越觉得,不尽快干掉他,便要后患无穷。
薛庭轩能逃过狼旗军的突袭么?
狼旗军的实力,赫连突利很清楚。这支人马是他苦心打造出来的,虽然人数不多,但个个都是勇猛无匹的强者。可是狼旗军要对付的不是寻常人,而是他所见过的最狡诈、最危险的人物。就算狼旗军能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胜机也顶多只有五成。
好在,就算狼旗军不成功,薛庭轩做梦也猜不到这支纵横在西原以西的小队人马与自己会有什么关系。黑暗中,他又无声地笑了起来。
第二天是招待五德营使者的献功大会,仆固部的头面人物,自五明王六长老以降全都出席了。虽然仆固部先前被共和军胁迫着攻打五德营,但五德营能够将共和军这个庞然大物都击退了,仆固部众向来最景仰英雄好汉,因此对五德营毫无芥蒂,反而生怕五德营因为此事而对仆固部怀恨在心,于是一个个都来敬酒。司徒郁酒量不高,回敬之事自然都由安多担任了。对安多来说,与这些仆固部的头面人物平起平坐地交谈实是梦寐以求之事,酒到必干,更是红光满面。好在他的酒量极宏,这点酒倒不能使他失态,反而让他显得气度雍容不凡。
酒过三巡,从一边突然发出一阵欢呼。司徒郁不知出了什么事,扭头一看,却见十几个汉子抬着个什么东西正走过来。一边正向他敬酒的五明王中一个见他不解,笑道:“司徒先生,那是‘八宝山’上来了。”
司徒郁算是个西原通,却也没听说过这名目,正待问一句,一边安多却又惊又喜地道:“哎呀,要上八宝山了?大汗真是太客气了。”
司徒郁道:“八宝山是什么?”
安多不等旁人回答,便抢道:“这可是西原最隆重的一道菜了,是一只牛里套一只羊,羊里套一只鹅,鹅里套一只鸡,这般一层套一层。”
司徒郁道:“能套八层之多么?”
这回安多还没回答,那明王笑道:“其实也不是非要八层,最多会套八层罢了。不过这回上来的这道八宝山,套的还真是实实足足八层。”
这八层从外到里,是牛羊猪鹅鸡鸽鹊,最里面还有个炸过的蛋。这道菜是西原最隆重的一道,因为麻烦,也不见得有多好吃,所以一般不太会有人上,一般只有重大庆典时才上。仆固部这些年来,除了祭祠释祖,也就是在思然可汗成婚时才上过。
这时那十几个汉子将这道八宝山抬到了思然可汗跟前,放下后行了一礼,退到两边。那是一个很大的木头架子,上面搁着一头烤熟了的全牛。牛要烤熟很不容易,更何况是如此巨大的一头。思然可汗走到木架边,高声道:“仆固部的子民们!”
思然可汗的嗓门倒是不小。而他一身袍服,也显得颇有威势,加上贴身侍卫的八犬环绕在他四周,越发显得气度不凡,周围登时鸦雀无声。思然可汗道:“今日,乃是五德营的贵宾前来的日子,这道八宝山,敬的正是五德营的英豪们!”
他说得气宇轩昂,大是不凡,仆固众登时轰雷也似一声喝彩,仿佛谁也不记得先前仆固部也曾攻打楚都城。安多正在喝着身前一杯马奶酒,被这声突如其来的欢呼吓了一跳。他脱克兹部一共才一千多人,哪见过这等声势,险些将酒杯都脱手扔在地上。这时八犬的首领洛克什上前,将一把刀双手捧到思然可汗跟前,思然可汗接过手来,轻轻一拔,刀脱鞘而出,一道刀光闪过,却如闪电般划过。司徒郁原本并不怎么在意,但这道刀光却如利刺般在他眼底刺了一下,他心中一怔,忖道:“这是什么刀?”
这把刀绝非凡品。固然,西原人都是些刀头舐血的汉子,每个人的佩刀都是利刃,但有如此不凡刀光的,定非寻常之物。司徒郁虽非武人,却对相刀之术颇有研究,知道因为铸炼、打磨之法有异,因此各处出产之刀都有各处的特点,精通相刀之术的绝顶好手能仅仅看一眼刀口便说出那是一把什么地方的刀留下的。司徒郁虽然还不算此道的绝顶好手,却也已经察觉这刀光与寻常的西原宝刀有异。而且,虽然隔了一段,看不太清楚,但望过去也觉那刀式样甚古,不太像西原通行的刀,倒似中原武人所用。不过,西原本来就不出产铁器,很多刀都是从中原运来,所以也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