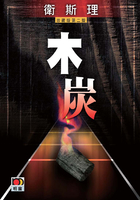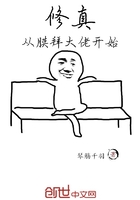“听不到……听不到……”当着苏雅和大海的面,戴晓梦把自己的两个耳膜捅破了,殷红的鲜血从她的耳朵里流了出来。为了逃避恐怖的死亡铃声,戴晓梦甘愿自残,变成聋子。
34
清晨七点,天色大亮。
医学院附近的一个早点店里,苏雅喝完最后一口稀饭,扔下两元硬币,从座位上站起来。
另一张桌子上,鼻青脸肿的大海对着一堆早点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一点食欲也没有。
大海没有想到的是,苏雅没有立即离去,而是走到了他身旁。
“喂,你吃完了没有?”
大海怯怯地望了一眼苏雅:“我不想吃了。”
“那你现在有时间吗?”
大海眼前一亮:“有时间!当然有时间!”
苏雅心中好笑,脸却绷得紧紧的:“有时间的话,陪我去一个地方。”
“好啊,愿意为你效劳!”大海一下子活跃起来,“去哪里?看电影?逛公园?还是逛商场?哎,无所谓,只要和你在一起,刀山火海只等闲。”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我就奇怪,你这个人,不说话会死吗?”
“说话是人的本能。不说话的人才可怕,你有没有看新闻?那些变态的杀人狂表面上看上去都是一副忠厚老实、木讷不语的样子。要知道,这种人才是最危险的,什么事都放在心里,发作起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苏雅白了大海一眼:“好了!你就不能让我清静点?”
大海赔着笑脸:“好,不说,不说。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能不能答应?”
“说吧!”
“下次要打,不要打我的脸。要知道,我可是靠这张脸出来混饭吃的!”
“你无聊不无聊!就你那张脸,能卖几个钱?再说了,你也真够笨的,这都躲不开!”
“我不是不好意思躲开嘛!”大海低声嘀咕,看到苏雅脸色不善,终于还是闭上了嘴。
上了的士,苏雅告诉司机目的地——青山精神病院。
大海苦笑,还以为有什么好事呢,结果又是去看那个疯子。
不巧的是,戴晓梦正在进行量表检查和交谈性诊断。苏雅百般请求,院长才勉强同意两人去现场观看。
等苏雅和大海到达时,戴晓梦的量表检查已经开始了。在她的面前,坐着两个女医生。一个是她的主治医生,瘦高个子,齐耳短发,脸平平的,像张白板,总给人一种发育不良的感觉。另一个年轻点,戴着眼镜,留着马尾辫。两人手里都拿着钢笔,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些什么。
白板和眼镜发了一张写满选择题的问卷,让戴晓梦来选择答案。这是例行的量表检查,用于检测精神病人的精神状况和临床治疗痊愈度。一般来说,里面的问题都是些常识性问题,精神正常的人很容易选择到正确答案。
戴晓梦还是那副冷漠阴郁的样子,拿着医生给她的铅笔,草草浏览下问卷,刷刷刷地几下子就填写完毕,速度是惊人的快。
白板收回问卷,看了看卷面,微微一笑:“不错嘛,差不多都答对了!”
戴晓梦面无表情,怔怔地望着白板。
白板把问卷交给眼镜,干笑两声,说:“戴晓梦,我现在问你些问题,你能不能好好回答我?”
“嗯!”
“我问你,你觉得最近的治疗对你的病情有帮助吗?”
戴晓梦冷笑:“我没病!”
白板摇摇头,失望地说:“你总是这样,不承认自己有病。你这样的态度,是不行的。”
按照交谈性诊断的惯例,凡是对刚才那个问题回答“我没病”的一律视为错误答案,需要继续住院治疗。
但今天,白板的心情不错,还想再给戴晓梦一个出院的机会。
“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吧!我问你,你身体还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没有,我的身体很好。”
白板笑容可掬:“这就对了!我再问你,你的大脑思维是否还受人控制?”
“没有,我的思维很好。”
白板的笑容益发灿烂了:“那还有没有人想害你?”
戴晓梦迟疑了一下,犹豫不决。想了一会,缓缓抬起头,说:“正确答案是没有人想害我,对不对?我如果说有人想害我,就意味着我的病情还没有好转,需要继续住院治疗,对不对?”
白板微笑不语。
戴晓梦对着白板诡谲地笑道:“当然有人想害我!”
白板惊讶道:“你说什么?你还是坚持认为有人想害你?”
戴晓梦冷笑:“你以为我像你一样白痴啊!全部回答对了,你还不把我送出病院!”
白板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戴晓梦这样的病人,竟然在精神病院里乐不思蜀,不想出院。作为戴晓梦的主治医生,如果一直治不好她,肯定会影响到她在医学界的声誉,让人怀疑她的医术水平。
白板勉强挤出一副和蔼的表情,柔声说:“戴晓梦,我是你的主治医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你应该尽量配合我,让你的病情得到好转,不要意气用事。”
白板还想继续说下去,这时,她的手机响起了铃声。
很奇怪的铃声,阴郁、压抑,每一个旋律都仿佛是幽灵的叹息,让人莫名地悲伤起来。这铃声,仿佛美丽的食人花,散发着强烈的诱人香气,花朵中却隐藏着累累白骨。
苏雅的心脏一阵抽搐,针一般疼痛的感觉弥漫了全身。她有种不好的预感,预感到即将发生悲惨的事情。
戴晓梦的瞳孔陡然间扩大,冷幽幽地盯着白板的手机,身体微微战栗着。
可惜,白板没注意到这些,一个劲地折腾手机。
“咦,怎么回事?”白板按了半天,都没办法接听。铃声不依不饶地响着,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节奏越来越快。
戴晓梦从座位上站起来,缓缓地走到了医生的桌前。
眼镜有所警觉地问:“你想做什么?”
戴晓梦对眼镜微微一笑,猛然挥拳狠狠地击在她的镜片上。
镜片破碎,碎片扎进了眼镜的眼睛里,鲜血直流。
白板这才反应过来,可惜,她的动作太慢了。戴晓梦在白板转过脸的一刹那间,已经拿到了桌上的钢笔,对着白板的眼睛就捅了过去!
正中目标!钢笔的笔尖直接插进了白板的左眼!
在白板的惨叫声中,戴晓梦顺手拔出钢笔,满脸惊恐地直往后退。
苏雅吓呆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前的场景,实在太震撼了。
手机的铃声还在继续,一声声,仿若重锤击打着戴晓梦。戴晓梦对着苏雅和大海凄然一笑,紧握着钢笔,对着自己的耳朵插了进去!
“听不到……听不到……”当着苏雅和大海的面,戴晓梦把自己的两个耳膜捅破了,殷红的鲜血从她的耳朵里流了出来。为了逃避恐怖的死亡铃声,戴晓梦甘愿自残,变成聋子。
如果说以前的戴晓梦还有可能是装疯,现在,她的的确确是疯了,而且疯得极为严重。
可是,变成聋子的戴晓梦,依然听到了死亡铃声!
“我不听!我不听!”戴晓梦捂着两个已经失聪的耳朵,疯狂大叫。
她终于明白,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无论她怎么做,死亡铃声都会在她耳边响起。她无从选择,只有等待命运的判决。
35
精神病院里警铃大响,保安们一拥而上,制伏了戴晓梦。
事实上,戴晓梦没有反抗,傻傻地站在那里,绝望地看着苏雅,任保安们把她五花大绑。
“没有人能逃得了……”戴晓梦喃喃自语,凄然泪下。
此后,戴晓梦仿佛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不吃不喝,不哭不笑,呆呆地躺在某个角落里,一动也不动,完全失去逻辑思维能力。医师们想尽了办法,尝试着和她交流。她嘴里反反复复都只有那句话:“没有人能逃得了……”
几天后的一个黎明,人们发现戴晓梦已经死去多时。她的眼睛是睁着的,可以猜测她死之前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痛苦,脸部的肌肉痉挛扭曲。虽然她聋了,可两只手仍然死死地捂住耳朵,怎么掰也掰不下来。
她是被吓死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当天中午,苏雅走出青山精神病院后,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塞住了,梗得难受。
戴晓梦绝望而痛苦的眼神深深地烙在苏雅的脑海里,甚至不时变幻成妹妹苏舒的眼神。同样的绝望,同样的痛苦,同样的凄凉。
不可置疑,戴晓梦是一个聪明的女生,和苏雅相比都不逊色。但她再聪明,依然逃脱不了死亡铃声的追杀。
妹妹是不是也会走上和戴晓梦一样的不归路?
这次,大海总算识趣,没有在她耳边叽叽喳喳,一脸的沉重。
这也是苏雅第一次看到大海严肃的样子。看得出,大海的心情也不好。毕竟,戴晓梦的模样实在太震撼人心了。
到了医学院,苏雅让大海先回去,自己独自去看望妹妹。
妹妹还没有醒过来,甚至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了。妹妹的脸,更加消瘦了,好像只有一层薄薄的皮肤依附在骨架上,仿佛一个骷髅人,让人看得心酸。
病房的护士对苏雅特别的友好。显然,父亲早就打点过了。听护士们说,父亲看了妹妹好几次。奇怪的是,他每次的态度都不同。有时,父亲很悲痛,失声痛哭;有时,父亲却很平静,仿佛在看望一个陌生人般;有时,父亲竟然大笑,笑得疯狂,令人不寒而栗。
苏雅不管这些,只是反复叮嘱护士,父亲来看望妹妹时,她一定要在场护理。护士眨着眼睛,似懂非懂。
苏雅想想,加了一句,因为妹妹的事情,父亲精神受到的打击太重,说不定会有失常的举止,尤其是在看望妹妹的时候。
护士连连点头,信誓旦旦地说会照顾好苏舒。
看望了妹妹后,苏雅去找李忧尘,想询问妹妹的病情。李忧尘不在办公室里,他昨晚做了一个手术,今天休假。
苏雅向其他的医师要到李忧尘的家庭地址,直接去他家里找他。
李忧尘家就在医学院的教师宿舍区里,一幢最靠后的平房。原来,李忧尘的父亲是医学院的老教师,一个权威的脑科专家。李忧尘是子承父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父亲死后,李忧尘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了,竟然放弃医院分给他的专家楼,搬回到那幢老房子里住。
那幢老房子独门独院,和医学院里新建的小区式楼房远远隔开。泛着灰色的红砖,长满铁锈的栏杆,苍翠欲滴的爬山虎,颇有些孤芳自赏的味道。
门是开着的,院子里种满了花草和盆景,弥漫着淡淡的清香。苏雅走进去,在院子里叫了一声:“李医师在家吗?”
屋子里传来李忧尘的声音:“在家,是哪位?进来吧。”
“是我,苏雅。”
“苏雅?那你等等,先不要进来!”李忧尘的声音有些古怪。
不但是声音,他的态度也有些古怪。听到是苏雅,他反而不愿意让苏雅进他家。难道,他有什么隐情不愿意让苏雅知道?
苏雅起了疑心,这个李忧尘,确实让她难以信任。他明明知道苏舒的受伤和死亡铃声有关,却一直故意隐瞒。身为脑科专家和精神病专家的李忧尘,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为什么要编造谎话来欺骗自己和刑警?
苏雅顿了顿,说:“我有事找你!”
“什么事?急吗?不急的话,下午再来吧,我现在手头上有事。”李忧尘隐晦地下了逐客令。
越是这样,苏雅的疑心越重。她干脆不再言语,径直走过去,用力推了推屋子的门。
门是关着的。只是,这种旧式的门,要打开也很容易。用脚大力踹,或者用一张类似身份证的卡片刷一下,都能打开。
苏雅咬了咬嘴唇,忍住想用脚踹门的冲动,用力拍门。
门开了,李忧尘对着苏雅苦笑,中指放在唇间,作了一个嘘声的动作。他的头发乱糟糟的。在家休假,他竟然还穿着一身白大褂,明亮亮地晃眼。
苏雅站在门口迟疑了一下,回头望了望,身后没有一个人影。不知为什么,她有些害怕。也许,她应该让大海陪着她来的。
“怎么了,还不进来?”李忧尘的声音还是那么和气,听不出什么异常。
苏雅缓缓走进屋子。
屋子里光线并不好,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地面上很潮湿,滑腻腻的,估计是返潮的缘故。家具都是老式的,八仙桌、老藤椅、大衣橱、电视柜、樟木箱,乍看过去,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幸好,日光灯是开着的。在屋子的中间,还亮着两盏应急灯,相互对照着。
然后,苏雅就看到一条剽悍的警犬。
警犬的四肢被绑住了,头部被铁架子固定住了,头颅被挖开了一个大洞,头皮被掀起来,露出血管密布的脑组织。
李忧尘手上拿着一个细长的仪器,尖端在警犬的脑组织里来回探索。更可怕的是,那条警犬,睁着眼,竟然是清醒状态的!
警犬的眼睛,正好奇地望着苏雅,两只眼珠子转来转去。
“小黑,专心点!”李忧尘没有看苏雅,继续手上的工作,“痛不痛?不痛的话就叫一声!”
小黑十分乖巧,喘着粗气低吠了一声。
李忧尘似乎很满意:“就是这里了……别怕,小黑,马上就好。”
小黑哼了两声,不以为然,似乎在说:“我才不怕呢!”
李忧尘摸了摸小黑的脑门,以示奖励。然后,他抬起头,对着苏雅微微一笑:“你先坐一下,很快就结束。”
李忧尘的眼神里流露出的兴奋和欢喜,灼伤了苏雅。那么狂热的兴奋和欢喜,原本只属于真正痴迷的艺术家和偏执狂,却从在手术中的李忧尘眼神里流露出来。难道,对于李忧尘来说,做开颅手术,竟然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苏雅嘴唇有些干涩:“你不用管我,我先去外面逛一会儿。”
“那样最好!”
苏雅逃也似的跑出屋子,跑出院子,跑到阳光灿烂的广场上,然后,蹲下来,“哇”的一声,呕吐起来。
她听说过开颅手术,但还从来没亲眼看到过。此时,她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李忧尘竟然在家里给一条警犬做开颅手术,而且那条警犬竟然还是清醒状态下的。
如果,那不是一条警犬,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有多恐怖!甚至,那个人,可能就是自己!
苏雅仿佛看到李忧尘把她固定在银色的支架上,一边和她谈笑风生,一边用冰冷的金属探进她的脑组织中,任意切除她的神经系统。或者将一些不知名的血块,置放到她的大脑中。
她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联想。也许,是李忧尘那种狂热欢喜的眼神,让她心生恐惧。她丝毫不怀疑,李忧尘这个谜一样的男人,有朝一日会做出超出她想象力的疯狂事情。
36
一个小时后,苏雅再次走进李忧尘家。
李忧尘已经脱下了他的白大褂,换上了休闲装,一个人坐在八仙桌旁吃饭。
令人惊奇的是,那条叫小黑的警犬也温顺地蹲在他身旁,正津津有味地啃着一块肉骨头,看上去一点事都没有,健康得很。
如果不是它的脑袋被剃掉的一块头皮,白花花的晃眼,苏雅还真难以相信。要知道,仅仅一个小时前,它的头颅还被李忧尘打开,现在却活蹦乱跳。
“吃了吗?”李忧尘的声音含糊不清。
他的嘴里,塞着一块肥得流油的红烧肉,酱色的肉汁顺着嘴角流下来。他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嘴唇,有些不好意思。
“呵呵,饿极了,吃相肯定不好看。”
“我吃过了。”苏雅远远地坐到另一张小茶几旁边。
“找我有什么事?”
“我想问你,你知道死亡铃声吗?”
“死亡铃声?”李忧尘放慢了咀嚼的速度,若有所思,然后呵呵一笑,“你说的是《午夜凶铃》吧,一部经典的日本恐怖电影,当然听说过,而且还看过。”
苏雅心中冷笑,李忧尘分明在敷衍她。
“李医师,我说的死亡铃声不是恐怖电影,而是现实中发生的事件。南江大学四女个生去大塘古村旅游,当晚三死一疯,这件事,你真的一点都没听说过?”
李忧尘拍了拍脑门,似乎恍然大悟:“哦,对,听说过。怎么了,好端端的你怎么提到这件事?”
“我怀疑,我妹妹的受伤,和死亡铃声有关。”
“是吗?”明显是不相信的声调。
苏雅耐着性子,把她从戴晓梦那里所听到的和所看到的叙述了一遍。
李忧尘听得很认真,甚至掏出笔记本,不时地记录着什么。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这么说,戴晓梦把自己的耳膜捅穿了,仍然听到了死亡铃声?”
“照当时的情形推测,应该是的。李医师,你能解释一下吗?”
李忧尘苦笑:“我又没有亲眼看到,怎么解释得了?耳膜破了,怎么可能还有听觉?非要解释的话,只有一个原因,由于过度的恐惧,戴晓梦产生了幻听。”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那个恐怖的死亡铃声,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确定,你听到了死亡铃声?”
“确定,不但我听到了,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也听到了。”
“是什么感觉?”
“忧郁、压抑,令人情绪低落,却没有可怕到让人受不了而自杀的程度。”
李忧尘忽然话题一转:“苏雅,你看小说时,有没有被感动得流过泪?”
苏雅微微一怔:“以前有过。”
“这就对了。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人的情感也是一样。有的人喜欢音乐,会在悲伤的音乐中黯然泪下;有的人喜欢文学,会在文学作品中自伤自怜;有的人喜欢影视,会随着影视中人物的际遇而悲痛不已。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软弱的敏感区域。现在的都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每个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心理隐疾,如果得不到正确的疏导和治疗,很容易会产生心理疾病,最常见的就是抑郁症。如果再被悲伤的音乐、文学、影视等氛围所渲染,情绪就会变得低落,很可能会产生厌世的心理而自杀。”
“你说的我懂,张国荣就是因为抑郁症跳楼自杀的。但是,这和我妹妹的受伤有什么关系?”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妹妹的确患有多种精神病,而且心理长期处于抑郁状态,跳楼自杀的可能性极大。”
“那死亡铃声呢?是我妹妹的幻听?戴晓梦她们四个女生,全都产生死亡铃声的幻听?而且一个个都因为幻听到死亡铃声而意外死亡,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情?”苏雅情绪激动地反问道。
李忧尘摆了摆手,微笑着说:“苏雅,你别急,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有没有想过,所谓的大塘古村死亡铃声事件,都只是戴晓梦她自己说的,没有旁证,查无实据,事实上并不可信。”
“怎么不可信?我相信她没有骗我!”
“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戴晓梦所说的只是她一个人的幻觉。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话,怎么能相信呢?苏雅,你最近是不是太焦虑了,要不要我帮你做下检查?”
李忧尘的笑容依然那么和蔼,只是在这和蔼的表情后面,似乎隐藏着什么,让苏雅敬而远之。
“不用!我才没病,有病的是你!”
李忧尘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知道你这种性格的人很难相信别人。有件事,我不得不告诉你,你妹妹的精神分裂症具有遗传性,因此,我认为你很有必要去做一次精神病方面的全面检查。”
一想到李忧尘给警犬做开颅手术时的那种狂喜的眼神,苏雅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去做一次精神病方面的全面检查?扯淡!那种地方,没病的人也要被逼出病来。
苏雅没有在死亡铃声这件事上做过多的纠缠,既然李忧尘不肯说,她再追问下去也是枉然。
“我妹妹呢?她的病情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持续性植物状态,也就是你们常说的植物人。”
“那她还能不能醒来?”
“那要看她的造化了。植物人,有的几天就会醒过来,有的几年甚至几十年也醒不过来。”看到苏雅一脸失望的表情,李忧尘又说,“你也不必太担心,从电脑扫描图来看,你妹妹大脑受损伤的地方正在恢复中,也许,过几天,她就会醒来。”
“是吗?”苏雅心中又升起一丝希望,“但愿如此。”
既然李忧尘对死亡铃声讳莫如深,再追问下去也是多余,苏雅就客气地告别了。离去时,小黑还站起来,亲昵地送她出去。
独自走在午后的阳光中,苏雅的心情好了许多。她真的希望妹妹的病情能像李忧尘说的那样,几天后好转,自然苏醒过来。
走到女生宿舍,管理员万阿姨正百无聊赖地坐在铁门处看书。
苏雅走上前,拍了拍万阿姨的肩膀说:“万阿姨,在看什么书?”
万阿姨看书看得太专注,被苏雅吓得一哆嗦,嗔声说道:“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差点吓死我了!”
苏雅吐了吐舌头,想去拿万阿姨手上的书。万阿姨却收了起来:“去、去、去,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别拿我老人家寻开心!”
苏雅隐隐看到书的封面上有“犯罪”两个字,估计是本推理小说。
这么大岁数的人了,竟然还看这种书?
苏雅还想和万阿姨再说几句话,突然传来一阵机动车辆的马达声,在她的身后戛然而止。
苏雅回头,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出崭新的红色标致跑车,走到苏雅面前,微微一笑:“苏雅,好久不见,没想到在这遇到你!”
37
“是你?”苏雅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愕,但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丝嘲讽,“我还以为是谁,原来是鼎鼎大名的江公子,怎么有空来我们医学院?不是又看上了哪位美女吧?”
江公子对苏雅的冷嘲热讽不以为意,呵呵一笑:“苏雅,你是知道的,在我心中,你是最美的。”
苏雅才不吃他这一套:“得了,这句话,你至少对几十个女孩子说过吧,俗不俗啊,就不能换个花样?”
“我是认真的。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为什么我说假话时,所有的人都相信,而我说真话时,却没有一个人相信?”江公子轻叹道,“只要你愿意,我很乐意履行我们的婚约。”
原来,江公子原名江逸风,出自南江的名门望族,其家族在南江市的政界和商界颇具影响力。苏志鹏虽然在房地产业颇有建树,但随着房地产业竞争的日益激烈,很想通过联姻的方式和江家拉上关系,从而借助江家的影响力让自己事业更上一层楼。巧的是,江逸风不知在哪看过苏雅,对苏雅是一见钟情,垂涎三尺,极力鼓动父母去撮合。江家也想强强联合,对南江市的房地产业实现规模性垄断,双方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只是苦了苏雅,本来就和父亲处于冷战时期,因为这件事,终于爆发了“世界大战”。用苏雅的话来说,就算她去峨眉山当尼姑,也不会嫁到江家。无论苏志鹏如何威逼利诱,巧言令色,苏雅始终不肯就范。再加上苏雅年龄尚小,还在读书,婚约之事双方只好暂时搁置。
尽管如此,苏家和江家还是实现了商业联盟,私底下更是“亲家公”、“亲家母”的叫得不亦乐乎。反正大家心中都有数,不过是商业上的互相利用,只要有利可图,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都没什么关系。
江逸风当然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他本来就是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喜欢拈花惹草。因为他那张比女孩子还要标致的脸蛋,因为他名门望族的背景,因为他阔绰的出手,江逸风的身边从来就不缺少漂亮的女孩子。
苏雅听到婚约气就不打一处来,怒骂道:“有多远你就给我滚多远!别在我面前装情圣,我看着恶心!”
江逸风早就习惯了苏雅的脾气,依然笑容满面:“你放心,我会等你的。等你玩累了,想通了,再来找我。你也用不着拿那种眼神瞪我,我不是来找你的,在等一个朋友,马上就走。”
果然,江逸风话音刚落,一个女生从女生宿舍中跑出来,边跑边叫:“逸风,我来了!”
苏雅愣住了,她怎么也想不到,江逸风等的女生,竟然是妹妹寝室的沈嘉月。
“逸风,我好了,可以走了吗?”沈嘉月的声音甜得发腻,仿佛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女儿。
“你……”苏雅指了指沈嘉月,望向江逸风。
江逸风微微颔首,颇有得意之色。对他来说,每一个即将到手的猎物都是值得炫耀的。
沈嘉月这才发现了苏雅的存在,惊讶地问:“你们……认识?”
“当然。”江逸风故意做出一个暧昧的笑脸,“岂止是认识这么简单,我和她,关系深着呢!”
苏雅把脸一沉:“谁和你关系深着呢?别瞎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说完,苏雅头也不回地走进女生宿舍。
直到苏雅的身影完全消失在女生宿舍的楼梯里,江逸风这才收回神采飞扬的目光,啧啧叹道:“苏雅就是苏雅,有味道……”
江逸风没有继续说下去,他察觉到沈嘉月幽怨冰冷的眼神,话音一转:“月月,怎么了,不高兴?”
沈嘉月当然高兴不起来。女孩子的直觉告诉她,江逸风对苏雅有着不同寻常的兴趣。如果是别人,沈嘉月或许会一争长短,但对苏雅,她毫无信心。
苏雅以她极具个人特色的姿态傲然屹立,让人惊叹于她的容颜她的才气她的魅力,所有的矫揉造作在她的面前都黯然失色。
沈嘉月有自知之明,对男孩的吸引力,她不可能超过苏雅,这也是她耿耿于怀的主要原因。
“是不是很漂亮?当然了,她可是我们医学院的校花。”酸溜溜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
“是吗?”江逸风不置可否。
沈嘉月沉默了一会儿,站在树荫下生闷气。
江逸风毕竟是风月老手,笑盈盈地走过来牵沈嘉月的手,哄道:“好了,月月,别生气,我和她只不过是普通朋友。其实,我和她连普通朋友都算不上,只不过两方的长辈有些生意往来,见过两次而已。怎么样?今天去哪里?一切行动听你指挥。”
沈嘉月陶醉在江逸风迷人的笑容中。稚气的女孩,感性总是超过理性。明明知道是些不着边际的甜言蜜语,偏偏还要对此深信不疑。
“走吧!”
两人手牵着手,钻进了江逸风那辆红色标致跑车中。几分钟后,这辆红色标致跑车驶出了南江市医学院。
他们先去了游乐场。在游乐场,沈嘉月比平常更像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更显得纯真可爱。事实上,江逸风正是看中了沈嘉月这种自然的纯真可爱。混迹情场多时,什么样的美女他没见过,一个比一个虚伪,一个比一个现实,太多的心机和算计让他感到一些疲倦。所以,他选择了沈嘉月,仿佛一股清新的晨风吹进了他的世界。
六点十分,江逸风带沈嘉月去了一个私人俱乐部,那里有小资女孩梦寐以求的生活。碧波荡漾的游泳池,储藏多年的红酒,高档精致的饮食,训练有素的服务员,各种休闲运动,全部都是高档的享受,随便一样消费所付出的金钱代价都让人叹为观止。
望着烛光中的江逸风,吃着那些不知名的高级西餐,悠扬的小提琴曲在耳边轻轻吟唱,沈嘉月真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整个西餐厅,只有她和江逸风两个人。杯中的红酒香气扑鼻,没喝就已经沉醉其中。
一杯红酒,比她一个月的生活费还多。一道菜,比她一年的生活费还多。
沈嘉月自惭形秽,自己身上廉价的衣裙和皮鞋,在如此高档的场所是那么格格不入。怪不得,那些俱乐部会员看她的眼神总是怪怪的。
如果,能一直过着这种生活,那该多好?
并不是没有希望,只要她能抓住眼前这个男孩的心。但是,她能抓得住吗?
沈嘉月越想越激动。由于激动,她紧张起来。
“不好意思,我去下洗手间。”
“没关系。”江逸风对这种场面早就见怪不怪了。
沈嘉月的身影刚刚离去,她放在餐桌上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抑郁、忧伤,仿佛垂死之人的呓语,在幽静的西餐厅里仿佛疯草一般迅速蔓延开来,轻易就覆盖掉小提琴的乐声。
江逸风皱了皱眉,这个手机铃声,有种说不出的魔力,一下子就把人带到悲伤的情绪中,不能自拔。沈嘉月这么单纯的女孩,怎么会用这种手机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