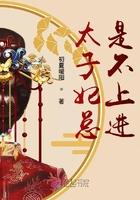然而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厅堂里帮着迎客打点的吴林见容许独自一个人应酬着,便装着无意地问了一句缘由。可容许只答“二奶奶和宋大奶奶在房里妆扮。”
吴林是何等狡猾的主,这样的回答是断不肯轻信的。暗暗派了一个心腹去藤园外张望了下,便知道原是二少奶奶不见了。
如是,这消息就传到老夫人冯梓君的面前。
今日推病不出面迎客,为得就是昨夜儿子儿媳妇对自己的忤逆,冯梓君知道若自己再不抖一抖威风,这个国公府出来的大小姐就要仗着自己的出身和丈夫的爱护不把婆婆放在眼里了。今日不参加宴席,仅仅刚开始而已。
此时,恰有林飞凤引了几位上年纪的老太太来看望婆婆,冯梓君自然斜靠在床上做柔弱状,挽了她们的手叫坐下说话。
见林飞凤侍立在一边,一位老夫人笑着问道:“怎么今日外头还是老三家的在应酬?原以为新奶奶在您面前侍奉着,想来瞧瞧新人,不想也碰不着。”
冯梓君面上讪讪的,拉了小媳妇的手道:“都说我偏疼她,可这孩子就是叫人疼。大房那里活脱一个活死人,什么也做不好,从前家里家外都靠老三家的帮着我。本以为老二娶了媳妇我好休养休养,却忘了新奶奶是公爷家的女儿,人家生下来就是享福受用的,哪里敢劳动了她。这会子她去了什么地方,我自然也不知道了。”
另一个不满道:“老夫人就不该这么想,难道公爷府上是这样的家教?既然进了门就要好好做媳妇,要她往东就不能往西,这才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女儿该有的品质。我们家那几个起先也仗着娘家几分脸面在我面前扭扭捏捏的,我是看不过,骂了几回打了几回,如今个个都服服帖帖。说句不怕人笑话的,咱们不也是这么过来的!”
绿绫奉了茶水上来,“哎哟”了一声道:“吕老夫人可是不知道我们新奶奶的厉害,昨儿晚上……”
“咳咳!”冯梓君故意干咳一声阻止绿绫将话说下去,嗔怪道,“那些琐事还值得说,不怕叫人笑话?”
吕氏却不依,“我们老姐妹几个还有什么不能讲的?你若怕笑话,往后我们不来了。你别挤兑绿绫,她跟了你几十年,还有比她更疼你的人?若非了得了,她能这样说话?”
冯梓君颔首称是,先嘱咐了小媳妇“外头二爷一个人不行,你去帮着照看下,也不知你嫂子什么时候能想起这些,凡事谨慎些。”
林飞凤应下,款款出来方松了口气。今日得了二嫂好处她还没向婆婆禀报,这才一句话也不说,只怕叫婆婆捏了把柄。且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她可不愿意轻易得罪了佟未这个财神爷。
前厅里客人越来越多,凡来者都必先问新奶奶何在,容许俱耐心地解释,也不嫌厌烦。林飞凤回来瞧见了,心里几番酸意:为何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竟是这样天壤之别的。老大虽然憨厚木讷,也是心疼老婆的人,老二看着冷冰冰的,却比谁都对媳妇好。可自己却嫁了个讨债鬼,还是个招母亲疼的讨债鬼,不由得自己每日每日地在婆婆和丈夫的夹缝中求生存。
恰见三香忽然跑来了前厅,拉着容许说了什么,但见容许嘱咐了吴林几句,又叫过宋云峰说了些什么,继而就撇下众宾客从厅堂出去了。
林飞凤轻轻一叹不再去想,旋身找了几家相熟的少奶奶说话。
且说容许离开前厅往后院赶,半路上便遇到了柳氏,一壁走一壁问,“她知不知道你们瞧见她了?”
“上官家的说只远远地看了一眼,没敢惊动。”柳妈妈紧赶慢赶,还是距离容许两三步远,再走,就跟不上了,一并连想解释的事情,也没来得及说。
“这个——画的是胡白舞吧!”然此刻,宁静的宥园里,穿了一身繁重华服的佟未对园子外的热闹和慌乱浑然不觉,也不知她会不会想到这一层,总之眼下她是极其气定神闲地在画影斋里欣赏悬挂了满室的画卷。
“容——无言。”她细细地识别画卷上的印章落款,奇怪地自言自语,“容无言是谁?好像容老爷的名讳是‘容竞言’。”
“家父字‘无言’。”这声音突然响起来,将佟未骇得不轻,转身朝房门处看,才发现出声的竟然是容许,可不仅语调奇怪,连他的脸上,似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