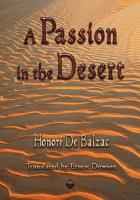容许回房时雨卉正要离去,见哥哥一脸担心,笑道:“嫂子没事了,休息便好。”
“好。”得知妻子没事,容许释然了,念及方才与允澄说的话,对妹妹道,“哥哥把一些事情与殿下说了,殿下希望你给他一些时间,他不能将你交给一个平庸之辈,所以他要看到子骋的能耐。卉儿,你只安安静静地在家等着,答应哥哥,不要做任何事情,更不要和宫里的妃嫔打交道。”
雨卉心里好一阵欢喜,她万想不到允澄是这样一个好人,听哥哥这么说,自然连连答应,阴郁许久的脸上也绽了舒心的笑容。
容许别过妹妹,进来看妻子,步子走得悄声,闪过屏风,竟见妻子正独自垂泪。
“未儿。”心里大疼,脱口喊了一声。
床上半躺的佟未显然一惊,慌张地别过头去胡乱抹脸上的泪水,随即才笑嘻嘻转来迎接相公,可相公已经是满脸的不解与担心,自己注定藏不住了。
“我……我只是有些累了。”佟未慌慌张张地解释,“自己一个人想着想着,就哭了……没,没别的事。”
容许却道:“不许撒谎,你天生不会撒谎,撒谎脸上就写字了。”
佟未下意识地去捂着自己的双颊,忽而明白相公的意思,心里一酸,眼泪又要出来了,都说孕妇情绪变化无偿,佟未实在深有体会,只是今日并非她变得快,当真是心里难受了。
“可相公你也有事情瞒着我对不对?从昨晚起你就心神不宁了……”
容许心里一沉,伸手去擦干妻子的泪水,无奈地回答她:“我要走了,一个人走。要带兄弟们去南边打仗,这一回是真的了。”
佟未愣愣地看着相公,嘴唇微微颤着,末了终于忍不住,一下扑进容许的怀里呜咽:“我就知道老天爷看不惯我过得好,非要叫我难过。我多想你陪着我把孩子生出来,相公你不在,我会害怕,真的会害怕……”
容许抱着的是妻子和孩子,他们都需要自己的保护和照顾,可自己不得不为了朝廷和边境百姓而奔赴前线,因此而对家人产生的愧疚,是一生也无法弥补的。
“未儿,我明晚天黑就要走,明天我送你回岳母身边去,这样我才放心。”容许松开妻子,含笑说,“不要哭,这样我怎么能放心离开?”
“这是第几次了?”佟未撅着嘴,呜呜咽咽地说,“大道理谁不懂呀?可是我现在哭你还能哄我,你走了我再哭,哪一个来哄我?”
“那刚才为什么哭,而我来了又笑?”容许道,“比起上一次,这回我更多了一个牵挂,你千万放心,好不好?”
佟未深深吸一口气,点头答应,又柔柔地答:“上回咱们说了好多,这次不要再婆婆妈妈了,今晚咱们说高兴的事情,给咱们的孩子起名字好不好?就算不起大名,也先给定个小名,等你回来我们再好好合计他的大名。不然他出来了,我喊他什么好?”
“好。”容许略有释怀,他也不想闹得生离死别一样的伤心难过,也正因是这样的佟未,才叫他如此珍惜。
转眼,夕阳西下,繁星满天,明日应是个好天气。
恒宅里,恒聿正独自在书房内翻阅南蛮的各种资料,因感口渴而茶水已凉,便推门出来欲唤人上茶,却见妻子独身一人提着灯笼静立在院子里,而那一隅,实为自己过去那一年里每日每夜都会站立的所在。
德恩似乎听见了动静,顺着方向转过来看,见是丈夫立在书房门前,淡淡地报以微笑,随即提着灯笼,轻挽披帛,回身往房内去了。
恒聿心里发紧,跟着往卧房去,可至门口,脚步反停下了,他忽而意识到自德恩清明出宫回来后,他已长久在书房过夜,而德恩也一次都没有派人来问过自己。
“驸马爷。”身后是如宝的声音,转身看,她手里端着托盘,上头稳稳地倒扣一只大青瓷碗。
“公主要的宵夜?”恒聿大概是找不出别的话来说。
如宝摇头,“是老夫人送来的,老夫人每晚都送来。”
“每晚……”恒聿念念有词,是啊,他不关心德恩的生活已经很久了。
“我来端进去吧。”恒聿伸手去接,这当是进房门的最佳理由了。才过手,忽而又问,“公主这些天每晚都会在院子里站一会儿是不是?”
如宝点头,语气里透着心疼,“其实这样很久了,起先是公主习惯了每晚去院子里接您回房,后来您不去了,她一个人来回几趟扑空后,就又习惯每晚在那里站一站,也不知她在看什么,也不知她在想什么。”
“这样,我知道了。”恒聿心里有些不适意,转身要进房,如宝又说,“驸马,奴婢不明白您和公主究竟发生了什么,坤宁宫里略有几句闲言碎语听在耳朵里,我和如珍都是不肯信的。您千万不要把公主看得和其他公主一样,公主真的很善良,奴婢服侍公主十几年,甚至常常会不记得她是高高在上的公主……”
“如宝,是你在外头吗?和谁说话?”房内的德恩听见了动静,喊了一声。
“你下去吧。”恒聿先开口,一面已推开了房门。
如宝只听得驸马一边走一边说:“母亲送来的宵夜,我给你端进来。”
“佛祖保佑。”如宝口中念佛,伸手将房门合上。
“延叔,怎么是你送来?如珍如宝呢?”德恩有些意外,但很快便从容了。
恒聿放下托盘,低头垂脸,将青瓷碗掀开,里头是一碗碧绿碧绿的羹肴,“我想来看看你好不好,另外想……”
“想问我为什么每晚站在你从前站的地方?”德恩先问。
恒聿舀着羹肴的手一震,继而放下,直起身子来看着德恩:“德恩,这件事我想和你说很久了,但一直都找不到机会,今天既然大家都心平气和,你能否给我一些时间听我说?”
德恩温柔恬美地笑:“你说啊,我自然愿意听。”
“我想你大概明白了我从前为什么会站在那个地方的原因,而如今我不去了,并不是因为那个人回京了。”恒聿停了一停,又道,“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情,即便我心里还有什么,那也仅仅在我一人,我希望你不要把事情牵扯到她的身上去,她没有任何错误。母后是怎样一个态度我们都清楚了,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母后再发现你因为她而伤心难过,我很怕太妃生辰那一晚的事会重演。我并不想和你或者母后站在对立的位置上,但我也不希望你们伤害她。”
德恩静静地耐心地给予自己极大勇气地听完这些话,世上可有人听见她心碎的声音?世上可有人会觉得她德恩可怜?没有啊,一个也没有。
“我明白,我也看到容夫人过着怎样幸福的生活,我知道不管我承受任何因你而起的痛苦,都与她无关。她是上天眷顾的人,每一个人都爱她、疼她。”德恩的眼睛酸酸的,她从不知自己原来是能够控制泪水的,她依旧含笑,故作镇定地看着丈夫,“你放心,我绝不会让母后伤害容夫人。”
恒聿听出这话里的怨气,可自己方才的话,又何尝不冷漠强硬?
“谢谢你。宵夜要凉了,你先吃,我去书房。”恒聿说着,转身。
德恩开口喊住他,“延叔,你身上的伤都好了吗?”
恒聿心头一紧,想起父亲对自己的那顿毒打,是何等的耻辱。没有转身,只答了一个“好”字。
德恩道:“那就好。”继而看着丈夫一步步往门外走,自己则一步步走到桌前,看了那一眼羹肴,忽而开口,“延叔,下一回再也不要这样对我说话,也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不爱听,也不想听。”
那一边没有答复,只是脚步声停过,再起,继而开门,关门,卧室复静。醇厚平静的羹肴忽而颤动起来,一滴、两滴,泪水落入其中,打破了凝滞。
“延叔……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德恩无力地伏到桌上,掩面而泣。
翌日,容许没有上朝,而是一早起来打点妻子的行李物件,趁空又来辞别母亲,将事情悉数告知,冯梓君于此是极明白的,虽然儿媳妇要回娘家待产让她很不愉快,但儿子要远行,她不能横生枝节,给他添堵,只口是心非地说了一句:“这样也好,她回娘家自在,我也不必多操心,家里还忙你妹妹的事情呢,虽然全权由皇室操办,可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送儿子出房门时,又笑着提了一句:“你若还有空闲,去西街看一看吧,你弟弟正忙着打理铺子,要正经做买卖呢。”
容许的确有些意外,然对母亲只是一笑,没有说别的话。反是送妻子回娘家时交代她留心弟弟那里的事,若有需要,当不吝予以资助和相帮。佟未自然满口答应。
回到佟宅,佟淮山得知女婿要远赴边疆打仗,总觉得这里头有几分奇怪,一时半会儿说不上来,只能叮嘱女婿诸多小心勿挂念妻儿,他会代为好生照顾。
何美琦虽然不忍女儿女婿相隔千山万水,但女儿能因此名正言顺地回家待产,做母亲的心里反踏实了许多,和丈夫一样对女婿说了诸多嘱咐,便不再打扰他们小夫妻相聚的时间,与丈夫知趣地离开了。
大概是回到父母身边了,佟未心安许多,与相公快乐地度过一天,在城门关上前一路将相公送到了城门下,但真的要离别,佟未还是不争气地哭了。
容许正好言哄着,轻快的马蹄声由远及近,夫妻俩看过去,待来者步入车马四周的灯光后,二人均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