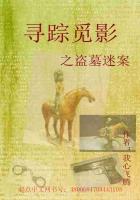我看着腕表,时间又过了十分钟。正常情况下,三人已经看清了石室内的状况,应该着手去摘那幅壁画了。摘完壁画,接着就会对石壁进行敲打探索。
再过十分钟,敲打声、争吵声、践踏碎石声都没出现,我们的前方与后方全都静悄悄的,死一般寂静。
我感觉情况不太对,但还是又等待了十分钟后,才谨慎地蹑足前进,过了两个拐角,小心地探出头去观察。
前面就是工人们干活的工作面,此刻满地都是大大小小的碎石块,铁锨、风镐、钻机、水罐胡乱地堆在甬道左侧,人只能从右侧通行。现在,工作面上没有人,向前二十米的石壁上有一个直径两尺的不规则洞口,距离地面约一尺多,能容一人钻入。
现场没有任何声音,我预估的争吵、敲打都没出现。此刻的状况,就好像那洞口里根本没有人一样。可是,三个大活人在里面,一定会发出某种动静的。
“他们应该在里面,但为什么没有动静?”连城璧在我身后喃喃自语。
我判断,那三人要么死了,要么离开了,才会不发出声响。
“你在这里等着,我过去,有什么不对劲,马上撤离。”我低声叮嘱连城璧。
“不行,要去一起去,要撤一起撤。”连城璧反对,紧攥着我的右手。
我甩不开手,只好带着她一起向前走。
二十米的距离平时只需要半分钟就能走过去,但这次我们两个至少用了五分钟才到洞口前,几乎是三步一停、五步一听。
我贴着石壁静听,洞口那边的确没有任何声响。
嗒的一声,连城璧打开了一支笔形手电筒,递到我手里。
我深吸了一口气,斜着伸出手电筒,向洞口的一侧照进去。此时我是在洞口的右边,手电筒光柱射进去,正好能照到石室的左侧墙面,也就是那西洋壁画所挂的位置。
笔形电筒的光柱很亮,我只照了十分之一秒,就倏地移开,同时身子后缩,以避开石室内可能出现的反扑突袭。
一瞥之下,我已经看清,墙上果然挂着一幅西洋壁画。其中的内容,与连城璧给我看过的大致相近。光柱划过时,我看清了那群衣着各异、手执冷兵器的洋人惊惧的脸。
壁画还在墙上,证明三人进去后,还没来得及摘下壁画。可是,他们无声无息地在里面干什么?难道是找到了另外的通道,已经远远离去?
还有,三人进入洞口,必定携带着手电筒,就算人死了,至少手电筒是亮着的,石室内不至于漆黑一片。
“什么情况?”连城璧在我身后问。
“画还在,似乎里面没人。”我并不确定自己的判断,声音毫无底气。
“不可能吧?按照‘探骊取珠之术’的显示,石室内没有其它通道,难道……难道石室的结构发生了其它变化?”连城璧不解。
我再次深吸气,示意连城璧去洞口左侧,然后把手电筒抛给她。
她跟我一样,只向洞口内探了一探,照了一照,最多只费了半秒钟,然后缩身后退。
这个简单的动作做完之后,她退回甬道左下角,但面部表情却在刹那间完全僵硬,仿佛见了鬼一般。
“怎么了?”我用唇语无声地问。
“他们——”她突然大声叫起来,根本没有理会我是用唇语提问,“他们在墙上,他们贴在墙上,他们……他们像那幅壁画一样贴在墙上……”
说到最后一遍,她突然丢下手电筒,双手捂着嘴,浑身颤抖,半哭半笑。
我跃过去,双臂搂着她,同时用双手大拇指按摩她颈后的大椎穴。
那个穴道主管人的心潮情绪,以指肚按住,逆时针、顺时针各揉三十次后,人的过激情绪就会慢慢平复下来。
“他们像画挂在墙上,他们变成壁画了……”连城璧在我怀里低泣。
我皱眉,根本不理解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等她情绪稳定了一些,我拿起电筒,向洞中照进去。光柱首先照到的是张运,他是三人中我最熟悉的,而且他的照片曾无数次出现在省内报纸上、济南宣传片里,所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是不会看错的。
那就是张运,他正贴墙而立,双臂高高上扬,手臂同样贴在墙上。向下看,他的双脚竟然离开了地面,距离地面约有三尺。没有人能凭空而立,除非是被挂在墙上。所以,当我看清他之后,不得不相信,他正是被“挂”在了墙上,并且是壁画一样平贴在墙上。
人的身体是个立体结构,即便是刚出生的婴儿,也会有身体的“厚度”,不可能像画一样扁平。从婴儿到成年人,身体厚度从半尺到两尺,不一而足。
很难想象,现在的张运变成了一幅壁画,牢牢地“贴”在墙上,浑身的骨骼、血肉、脏器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张徒有虚表的“人皮”。
我移动光柱,看到孙华子、万师傅两人也都被“贴”上了墙,除了外面的衣服,只剩一张人皮。
“怎么回事?简直不敢相信……”我不知该怎样描述自己看到的这一幕。
怪不得三人没有发出声音,都变成“人皮”了,还怎么能发声呢?
“他们变成了人皮,对不对?”连城璧伏在我背上,颤声问。
我点点头,但实在无法解释眼前看到的这一切。
接下来,我观察了石室的另外两面墙,再加上顶、地两面,与连城璧“探骊取珠之术”的结果大同小异。
那的确是一个高三米、宽三米、深三米的石室,墙上没有门也没有窗。左墙上挂着那幅西洋壁画,右墙上“贴着”张运、孙华子、万师傅的人皮。除此之外,再没有其它物件——对了,手电筒共有三只,分别握在三人手中,不过此刻全都不亮了。
“我进去拿壁画,你等一等。”我说。
我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既然石室中并无可见的危险,那我当然得进去拿画。
这次连城璧没有跟我争,因为那石室不算大,两人进去,毫无必要。
我矮身钻入洞中,抬头看着那壁画。
壁画的长度约一米半,高度约半米,类似于国画中的横向卷轴。
实物与照片看起来略有差异,因为壁画里的内容相当具有立体感,那条龙形怪物身上带着强大的杀气。虽然我只是看画,却已经感受到它发散出来的咄咄杀机。
如果是在光天化日下的闹市之中,见到这种画也许并不害怕,但此刻是在一个阴森恐怖的地道里,背后墙上贴着三张人皮,我心里的紧张感可想而知。
我没有耽搁,迅速走到壁画下面。
壁画外框没有任何挂钩,不是被挂在墙上的,而是贴在墙上。
我双手托住画框,向上一托,画框已经离开墙面。
如果它是被双面胶、胶水、浆糊之类粘在墙上的话,一推一拉,就能摘下来。
不知怎地,我脚下一个踉跄,身不由己地后退,双手也立刻离开了画框。
我试图拿桩站稳,但背后却出现了一股巨大的吸力,把我吸到了墙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那股吸力如同大海狂飙一般,我拼命扭腰挣扎,但却被越吸越紧,双臂也斜向上方,紧贴墙壁,动弹不得。
我想开口叫,但只一张口,却发现自己连气息都无法向外送出。恰恰相反,张口之际,外面的气流被那股吸力牵引,一直灌进我喉咙里来。
“原来,他们三个不出声,不是不想出声,而是……开不了口……”我突然明白了。
接下来,更恐怖的事发生了——我被吸在墙上之后,后脑勺贴着石壁,现在我发觉,那股吸力竟然是连思想都可以“吸”走的。很快,我的脑子都转悠不开了,所有的想法变得支离破碎,被“它”陆陆续续地吸走了。
我靠着最后一点意志力强迫自己控制脖颈,把头向前低下去,使后脑勺离开石壁。只做了这一个简单动作,我浑身的力气就用尽了,贴身衣物被汹涌而至的汗水打湿,眼前也是金星乱冒。
“不能……屈服,否则就会像……他们三个一样变成……人皮……”我艰难地扭动身子,手臂、双脚撑住墙面,艰难地向右面转身。
贴在右面的是孙华子的“人皮”,他半咧着嘴,脸上带着一个诡异而恶劣的笑,像是在嘲笑这次操蛋之极的夺宝之旅。
这个关键时刻,我竟然想起了那个站街女。如果她知道孙华子这个地痞流氓、张运这条道貌岸然的老狗变成现在这模样的话,一定会大呼痛快吧?
在思想被吸走的同时,我也看到了更多的东西——那是一条左右不见尽头的沟壑,深极,远极,除了搭建铁索桥或者肋生双翅之外,再也没办法通过。沟壑因其深极而变成了浓墨般的黑色,只看一眼,就头晕目眩,仿佛要被那黑色的世界吞噬进去。
没有光,但我能感觉到那深藏沟壑之内的东西。
那是一条妖龙——或者说,是一条龙妖。
龙是神圣之物,不可能化而为妖。那东西天生是妖,只不过是诞为龙形而已。
那龙妖在沟壑内翻腾逡巡,气吞山河,诡秘绝伦。
沟壑彼端,就是冲天而立的镜室。那座高科技巨楼就建在孤岛之上,四周被沟壑圈住,真的是一座危楼。
要想打破镜室,就要先渡过这条沟壑。
要想渡过沟壑,就要先降服龙妖。
“我不行了,我……我计算不下去了……”现在,我变成了一个崩溃掉的奥数算手,脑子一片空白,无法组织起任何有逻辑性的只言片语。
“阿璧,不要进来,逃,快逃,快逃……”这是我心底最后的呼唤。
如果济南城地底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心情去嘲笑建筑在活火山之上的扶桑之国?在科学家、物理学家、玄学家的预言中,日本终将沉没,全盘滑入地球上最深的海沟,成为第二个亚特兰蒂斯大陆。
“济南城呢?我们呢?我们的未来呢……”我昏昏沉沉地想。
龙妖一出,乾坤易主。
天地震动,山河冰封。
我仿佛看到了全人类的某日,但那已经与我无关,因为我即将变成一张可怕的“人皮”,像张运、孙华子、姓万的一样。
当一个人被全部掏空时,果真就会只剩下一张皮,像一个被扎破了的气球,肚子里的气一丝丝漏掉,然后在吸力的作用下,贴在墙上,慢慢风干,而后变成碎片。
我无法说清此刻的感觉,因为意识已经相当模糊,只能看到手电筒的光柱在石室内无意识地晃动着。
当然,正因为我看到了妖龙的存在,更加认识到镜室的非凡意义。
一切真相掩盖在层层表皮之下,所有人认为莫先生建造了镜室这种表象,只是无数表皮的其中之一。
我想,即使是身在镜室、投资镜室、研究镜室、攻击镜室的人,也未必知道镜室为什么存在?为什么要在山大校园之下存在?
沟壑合围,孤楼独立,已经说明,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个生死迷局。
我仿佛看到,大地为枰,天神执子,正在进行一场人类无法知晓的对弈。那么,渺小如蝼蚁的人类所能做的,就是在大人物的对局中苟且偷生,保全自己的性命。
对弈之道,本来就是顾大局而舍小地,而天神高高在上,更不可能照顾到全部人类。于是,散布于地的人类,性命皆在须臾之间。
死,是必然的结果。
不死,是暂时的侥幸。
龙妖潜于渊,大城可以暂保安宁。
龙妖行于田,则大城内外杀机四伏。
龙妖飞于天,则齐鲁大地顷刻间就要哀鸿遍野。
所以,我悟到了,这一战,真正的敌人是龙妖,不是长江、秦王会、赵王会、燕王府之间的反复内讧。中原人之间的相互倾轧,只会削弱各自力量,在龙妖脚爪之下辗转化为累累白骨。
“天石!”连城璧的叫声从洞口传来。
我无法发声,自然也不能开口警示她。
嗖的一声,连城璧从洞口闪入,脚下还没站稳,已经被石壁吸过来。
我的心猛地一沉,知道大势已去。
没有外力援助的话,我们两个只能困厄而亡。
连城璧反应极快,一见苗头不对,立刻双手拔枪,向着石壁连续扣动扳机。
按照常理,子弹射中石壁,定会迸射弹跳,射向别处。不过这一次,枪膛里共射出了二十四颗子弹,无一例外,全都被石壁吸收进去。
“走,快走……”我说不出话,只能用意识无声地呐喊。
连城璧比我稍微庆幸一点,她被吸向石壁的时候,立即抛下手枪,双手撑住,身体离石壁还有两尺远,最起码身体没有被全部吸住。
“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她顾不得自己的困境,先向我连声叫着。
蓦地,洞口一暗,又有人探进头来,竟然是那个跟张运见过面的小黑胖子李强。
这些人像吸血的蚂蟥一样,一看到发财的窍门,自动就跟踪过来,顾不上任何危险。
连城璧的头脑反应真快,立刻低叫:“这宝贝不能让外人得去,价值连城,史上罕见。天石,你赶紧过来,我们只要把宝贝运出去,就能发大财了。”
她如此说,正是为了引李强上钩。
“什么宝贝?你怀里抱着什么?”李强并未意识到危险迫近,更没有注意到石室内巨大吸力的存在。
“天石,咱们要的就是那幅画里的宝贝,就在我背后的墙上——”连城璧又叫。
李强手里握着一只加长的手电筒,光柱超强,犹如《星球大战》中的外星光剑。
他手腕一转,立刻照向了左侧石壁,发现了那幅西洋壁画。
“嗯,这个东西似乎还值点钱,不过,究竟是不是赝品,还得拿到市场上去问……”他一边说,一边钻进了石室,一步跨向那幅画。不过,说时迟那时快,当他双脚落地时,立刻被吸向石壁,距离连城璧只有半尺。
连城璧怒吼一声,身子横向一滚,右手抓住我的左腕,左手抓住李强的右腕,发力一扯一扭,我就被掷向洞口。
一离开石壁,我的意识立刻恢复,单手抠住洞口凸起的石头,另一只手发力,把连城璧扯过来。
我们连滚带爬地狼狈逃出洞口,根本顾不上去揭那幅西洋壁画。
“喂喂,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李强叫了两声,但随即就叫不出声来了。
不到一分钟,李强就被牢牢地吸在墙上。
我眼睁睁看着他的身体慢慢扁平下去,失去了皮囊下的一切骨肉和内脏,化为一张穿着衣服的人皮。
“我们……我们……闯大祸了!”连城璧靠在石壁上,大口喘息,面无人色。
石壁不会无缘无故产生吸力,我认为石壁后的龙妖才是始作俑者。
我想开口说话,但张了张嘴,才发现唇舌无力,浑身疲惫,像是刚刚给人献过血一样,而且献血量巨大,以至于我的气血已经供不上自身生存的需要。
“天石……你的脸太苍白了,刚才一定是出了问题,我带你去医院,别急,我带你去……”连城璧无法连贯说话,腰都直不起来。
我看到她的惨白脸色,自然就明白我身体里发生了什么。
“去医院,输血。”我在她手掌上快速地写了五个字。
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们两个没有变成人皮,但身体内的血液已经被凭空吸去了很大一部分,只有加急输血,才能补足气血。
连城璧不敢耽搁,架起我,跌跌撞撞地出了地道,直接奔向银座商城后面的私人诊所。
有钱能使鬼推磨,几千块钱递出去,十分钟后,我们两个就躺在了一间单人病房的两张单人床上,左右手腕同时扎针,右边输血,左边输液。
连城璧已经警告过医生和护士,不按铃就别进来。
死里逃生之后,我只想静静躺着,不开口,不动脑子,也不愿向任何人求救。
石室是条死路,而定下这条死亡路线的正是秦王麾下的丞相吕凤仙。
现在,吕凤仙应该出来收拾残局了。
我默数着,连城璧共按了六次电铃,护士进来了六次,每次给我换一个两百毫升的血袋,加起来总共给我输了一千四百毫升鲜血。
渐渐的,我觉得体内有了力气,头也不晕了,唇舌也变得利索了起来。
“找你的黑客朋友,问问那幅壁画的事?”我说。
连城璧一直平躺着,闭着双眼,一动不动。
“怎么啦?”我问。
“我在想,那壁画上的一百零八个洋人为什么那么恐惧?如果单单看见了龙,他们也许会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可是,他们恐惧地聚成了一堆,人人向后退,根本鼓不起作战的勇气来。我猜,他们大概很清楚,有些战斗是连尝试都不必尝试的,因为那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别的战斗,上就是死,不上还能多活几分钟。到底是什么样的敌人,能让这些全副武装的战士怕得要死?”连城璧问。
我苦笑着回答:“像刚才那样,进入石室不到一分钟,就会变成人皮——这种战斗,足以把人吓得再不敢回头。如果不是你反应快,现在躺在这里输血的就是两张人皮,而不是你我。”
这当然是玩笑话,人皮是不可能自动跑到医院里来的。而且,已经变成了人皮,再输多少血也不管用了。
连城璧拿出手机,看了看屏幕,悚然低叫:“手机……手机这么轻,似乎电池都被吸干了。”
我似乎想到了,那吸力的目标是一切“有能量”的东西。手机、电筒都是有电力的,而且还要加上张运、孙华子、姓万的、李强四个人的手机和电筒。这些东西一进入密室,就会失去力量,然后能量大半被怪力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