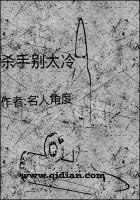店堂里,只有吧台后的两个服务生在闲聊。见来了一担生意,他们热情地同两人打招呼。不知道其中的一位从哪儿学来一句中文的“你好”,自顾亭然进店后,他就拼命重复这句话。同伴一个劲地笑话他,还直朝顾亭然挤眉弄眼。
起初,顾亭然倒还以中文回答他;时间长了,对方的热情反而把气氛搞得有些尴尬。正当顾亭然不知所措时,索菲娅在身后轻轻扯了他的衣袖,继而朝一个最靠内侧,不会被轻易打扰的地方走去。
见两人并不认同自己的玩笑,服务生迅速递上两杯咖啡,随后知趣的退回到吧台,又继续同他的伙伴闲聊起来。
“现在的法国人可是很热衷于学中文哦。”索菲娅俏皮的一笑。
顾亭然不置可否地努了努嘴,想要开口,又放弃了。
索菲娅见他表情凝重,也顿时收住笑容,问:“打算从哪里说起?”
顾亭然嘴唇紧闭,手里的汤匙不停地在咖啡杯中搅拌。金黄色的泡沫逐渐散去,留下来的却是浓黑色的液体。“还记得我的朋友,克劳德吗?”百般踌躇,顾亭然最终决定说出一切。
“对啊!”索菲娅像是突然醒悟了似的。“最近都没见他和你在一起。该不是圣徒的研究太过繁重了吧?”
刹那间,顾亭然觉得自己苍老了四、五十岁,仿佛一个久于世故的老人:每当一位老友从身旁消失,走上了另一条路时,他就会像哲学家似的,先是思绪万千,继而沉默不语。最后,他会喋喋不休,滔滔不绝的述说往事。
“他好像……好像对镜子有特别的偏好。”于是,顾亭然简单的讲述了那天拜访克劳德家时的情况,以及之后一系列怪异的行为和他日渐消瘦的身体。
“他不会有自恋癖吧?或者谈恋爱了?”索菲娅慢慢把玩羹匙,似乎有些抓不住重点。
“不会。他向来不修边幅。现在又是一副病怏怏,不像在恋爱。
“有没有服药?”
“他不是瘾君子。”
索菲娅终于忍不住,小声问到:“这和我们的‘玻璃杀手’有什么关系?”她一边观察着顾亭然,希望能从他的表情中琢磨出些端倪。
“我很想知道克劳德究竟从镜子里看到了什么,以至于他如此沉迷于此。之前我在西岱遇到一位清洁工。他说经常能从唱经班小巷里扫出许多碎玻璃,有一次,他亲眼看见克劳德拼命的拿镜子朝楼下砸。他原本想报警,可后来觉得麻烦,就只是朝楼上骂了几句。”他不合时宜地换了口气。却发现自己的话题依然游离于主题之外,已经渐渐引起了索菲娅的不耐烦。
“‘镜子’是一个特殊名词。它固然有所特指,但并不是只有镜子才能发挥镜子的作用。”用一门不熟练的语言,想要表达一句拗口的句子,顾亭然显得格外的狼狈。好在虽然说得缓慢,索菲娅倒也能渐渐明白他的意思。“其实,任何玻璃制品,只要能反射,都能被当成一面镜子……”
“他是‘玻璃杀手’?”索菲娅突然惊叫起来。由于咖啡厅里客人寥寥,巨大的回声顿时引起了两名服务生的好奇。其中一个更是夸张地趴在吧台上,探着身子摇头晃脑,笑称顾亭然不应当欺负自己的女友。
如果真是我的女友,该有多好!。顾亭然尴尬的红着脸,继续说。“在没有确凿证据前,我不愿意说他就是‘玻璃杀手’。”可是,我又不自觉得朝这个方面想。“既然克劳德有嫌疑,我们的调查不妨就从他开始。一则,我希望能帮他洗脱嫌疑;另一方面,我想知道克劳德究竟从镜子里看到了什么。”
索菲娅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顾亭然的一席话在她的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概念。之前,她从没有考虑过‘玻璃杀手’的行为动机。或者说她单纯地认为凶手只不过是在宣泄某种情绪;甚至只为了出名。
只有一个常人无法接受的理由,才会导致凶手的破坏欲。究竟,克劳德从镜子里看到了什么?
“能不能……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克劳德就是凶手?其实,我心里早有疑惑,但就是怕影响你的判断,所以才选择暂时保密。要知道,越是超乎常理的事情,我们越是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索菲娅没有想到顾亭然竟然能看穿她的心思,再一琢磨,也许思想无意间全都刻在了脸上。她歉意十足地朝顾亭然点点头,说:“我们该怎么办?”
“既然克劳德有嫌疑,不如从跟踪他开始。明天起就是春假,正好有时间监视他的行踪。”看他一脸沉着,似乎早有打算。
“我和你一起。”
“不行!”顾亭然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玻璃杀手’通常都是夜里犯案,必须整晚守候在克劳德的住所。你如果每天夜里都不回家,你的父母肯定会起疑心。而且,这也很危险。”
索菲娅老成地拍了拍顾亭然的肩,道:“放心!我早就想过要在夜里行动,所以前几天特地对他们说我打算和朋友们出去旅游。春假后才回来。”她把记事本翻到四月,上面分明写道“外出旅游”。她俏皮的对顾亭然挤眉弄眼,说:“法国女人可是即独立,又有主见的!”
顾亭然哑然失笑,无奈道:“那你得保证,一切行动必须听我安排。”索菲娅像只温顺的小猫似的拼命点头,生怕少点一次头都会遭来顾亭然的拒绝。后者疼爱的会心一笑。“明晚会是第一次熬夜,乘现在有时间先回家休息一下,做点准备。明天晚上九点半我们在圣母院正门碰头。如果你怕饿怕口渴的话,可以带些吃的。”他想了想,又说:“记住,夜里尽量穿深蓝色或深紫色的衣服,装束越简练越好。”
“为什么不是黑色?”
“忍……忍者,你知道忍者吗?”顾亭然不确定自己的发音是否正确,他连着说了几遍,又稍作解释,直到确定索菲娅知道他在说什么才继续。“这是日本忍者使用的颜色。因为深蓝或深紫色更接近夜空的颜色,这要比黑色更不容易被发现。”顾亭然又嘱咐了些琐碎事,便同索菲娅一起离开了咖啡馆。
漆黑的小巷,从一头看不到另一端的巷尾。喘息声掩盖了脚步声:先是一个人,继而两个,再是第三个。积水践踏声、杂物碰撞声此起彼伏,只是没有喊叫声。就像一场狩猎,猎物和猎人都屏气凝神,谁先发出叫喊声,就意味着胜利倒向了另一边。
黑暗中,顾亭然和索菲娅整整潜伏了五个小时。直到黑影从拐角闪出,他们便尾随其后。顾亭然首先冲了上去,他悄无声息地,试图尽可能接近黑影,然后一口气扑到他身上。计划似乎就要成功,索菲娅却不合时宜的发出了一点响动。黑影迅速的过头来。那时,顾亭然只在他身后数米。他们几乎要撞在一起。顾亭然头一次同他正面相对。可是,黑色连帽里,竟然是伸手不能触及的深渊。他在召唤我伸手进去……
就在顾亭然走神的刹那,黑影鬼魅般飞扑过来。好像一张皂色大网,铺天盖地地朝顾亭然的头顶压来。紧接着,顾亭然的脸颊遭到重创,生平未有的疼痛感险些使顾亭然昏过去。他,颤颤巍巍,摇晃着身子,重重跌倒在地。索菲娅的尖叫声,同时惊醒了缠斗在一起的两个人。黑影似乎无意取走顾亭然的性命,他再次扭头飞奔。
现在,黑影在前,索菲娅紧追其后,顾亭然掉到了第三位。谁都没想到这个女孩子有如此好的体力,她不啃一声,紧咬牙关。
黑影带头钻进一条巷子,慌忙中,他没有察觉到小巷深处竟和他一样漆黑。直到被逼入尽头,黑影停住了脚步。他背对尾随而来的索菲娅,悄无声息,沉默的低着头。心跳、喘气和脚步同时逼进,黑影如黑豹般转身扑向索菲娅。这一次,他不再手软,双手几乎同索菲娅的脖子融为一体。后者逐渐感到呼吸困难,胸腔仿佛干瘪的风箱,已经丧失了运动力。
如果顾亭然晚到一分钟,他将再也见不到心爱的索菲娅。他的脑海中顿时一片空白,全身竖起的毛发扎得他好不自在。他紧握双拳,加快脚步,做出一副要和对手拼命的架式。
突然,正当他瞪大双眼准备与黑影殊死一搏,黑影猛地抬起了头。这一次,他们终于对面而视。连帽下,再也遮挡不住那张恐怖的脸。那是一张真正能令人生畏的脸庞,任何一头野兽也不过如此。一对牛铃般的眼睛死死盯着顾亭然,颧骨凸起,脸颊上布满爆出的青筋。好像盘根错节般缠绕在整张脸上,除了一对眼睛,很难找到别的器官。
应该是一张嘴的位置,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紧接着,一张血盆大口突然出现在黑影的脸上。尖利的牙齿清晰可见,唾液仿佛胶水似的粘连着上下颚。咆哮声夹杂着一股强烈的气流从咽喉深处汹涌而出。那是他从没听到过得,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顾亭然本能的尖叫一声,身子如弹簧似的从床上弹坐了起来。豆大的汗珠顺着眉角淌下来。他重重地在脸上抹了一把,恐惧地扫视着房间里的情况。这只是一间昏暗的普通房间,和顾亭然记忆中的小窝何其相似。他看不见索菲娅,房间里也没了那个黑影的踪迹。他记得自己的脸颊上挨了一拳,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脸颊,那里却没有一丝的疼痛。
即使在做梦,顾亭然也从未对一张面目如此记忆犹新。那人面目可怖,简直可以比肩圣米歇尔广场上的那张万恶魁首的脸。但那绝不是克劳德!虽然是个梦,这恐怕也是顾亭然唯一感到庆幸的事。
他摇摇晃晃地起床,在书桌上找到了手机。离约定的时间尚有两个小时,顾亭然思量许久,还是决定给索菲娅去个电话。东方人很在意梦境给予的提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与神沟通的良好契机。今晚开始的行动吉凶未卜,顾亭然总是放心不下。
二十点三十分,比约定时间尚早一个小时。顾亭然再次踏上西岱岛的土地。他先是在唱经班小巷和修女街逛了一圈,继而迈开沉重的脚步朝圣母院走去。他凑巧在圣母院找到了一位执事的嬷嬷,后者正好负责那班学生的餐饮。据她说,克劳德同其他学生一起用过晚餐,回住所去了。她表示自己格外担心克劳德的身体,但见他胃口尚可,一时倒也没什么主意。
克劳德在自己的住所,今晚会是个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