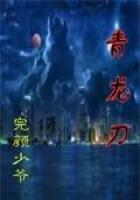五个人都没想先开口,他们同时安静的扫视着房间里的其他人。今天的话题需要一个突破口。通常情况下,欧仁总是这种僵局里第一个淘汰者,他不喜欢把话憋在肚子里。他清了清嗓子,道:“到目前为止,调查报告全在各位的手里了。”
三人这才埋头翻阅材料。但是,除了金斯顿主教不住的发出“啧啧”声,另两位对此似乎不很感兴趣。他们草草读完报告,又是一脸凝重的望着欧仁。后者只得硬着头皮继续说:“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确定这起案件的性质。安托万神父的死因可能有各种解释。如果各位想得到更多的情况,恐怕,”他看了看身旁的孔陶。“得过上一阵子。”
“教皇可是很关注这件事情的,”拉萨尔大主教阴阳怪气的说到。他的声音像个女人,听起来很不舒服。“这是对天主教的挑衅!在这么一个繁华的、历史悠久的都市,却发生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案件。这不是中世纪,先生!也不是那些野蛮的新教徒的地盘!”他装模作样地双手握住胸前的十字架。
“没有进一步的线索或证物?”阿道夫部长早就把材料扔在一旁。他当过秘密警察,知道怎样的文件才算完整,又有那些纯粹为了搪塞人。
欧仁老头摸摸大鼻子,侧着脑袋撇着身旁的孔陶。“比隆男爵”目不斜视,却像是感受到一双讯问的目光,他微微点头,示意可以透露一点。老头这才放宽心,他故作镇定地从自己的文件夹里取出一份文件,转了个头,递给了离他最近的拉萨尔大主教。“这是在死者身上找到的一段文字。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测和骚动,我们没有公诸于众。”
拉萨尔第一个阅读到这段文字,他才看了头几个字,就开始不停地、痛苦地呻吟。再往下读几个字,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将文件顺手甩给身旁的阿道夫。看来他的心情一时间是难以平复了,颤抖的右手微微隆起,从额头到胸前,再从左肩到右肩,拉萨尔反复划着十字。持续了大约一分钟,才从他的嘴里悄悄流露出“哦,上帝!哦,玛丽亚!”
阿道夫不是个教徒,他只是扫视了一边文件,便交给了金斯顿主教。
三人中,属金斯顿主教的反应最强烈。他才看了不到几个字,就触电似地把文件扔在地上。他突然从椅子上滑了下来,长身跪在地毯上。他也是单手在胸前划着十字,口中不停地念着“玛丽亚”。
老人家怕是年时过高,激动之余,有些体力透支。他颤颤巍巍,摇摇晃晃,口里却依然念念有词。若不是孔陶把他重新搀扶回椅子,金斯顿主教怕是已经趴在了地上。
“魔鬼!魔鬼!”金斯顿主教已经说不出话来,唯一的宗教代表拉萨尔大主教还在嘟哝着。
“这是什么?”阿道夫部长谨慎地问到。
“《圣经·启示录》的章节。先生。”孔陶负责从旁解释。“我们从死者的衣服里找到的。上面没有指纹,纸张和打印墨水也很普通。”
“还有呢?”阿道夫部长部部紧逼。某种意义上,阿道夫比任何人都在意这桩案件。他和拉萨尔大主教关系莫逆,后者目前正在为进军梵蒂冈做准备。一旦后者成为法国籍枢机主教,就能从外围为阿道夫参选总统造势。因此,阿道夫绝不允许拉萨尔在离开法国前有任何的闪失。他要确保这位大主教所辖教省的太平盛世。
“他一定是个无赖,一个门外汉却力图羞辱上帝!”拉萨尔似乎有了灵感。“两位先生,我正式向你们提供一条线索!”他示意孔陶再把文件交给他。这一次,拉萨尔反应小了许多。他只是捏着文件一角,对众人说:“各位,这是用英文写的。任何一部英语版《圣经》,甚至网络上也能找到这段文字。他并不是个兄弟,否则,他应该使用希伯莱语才是。”拉萨尔大主教振振有词。
高谈阔论下,欧仁险些笑出声来。拉萨尔也只能去做教徒了,他的思想毫无逻辑可言,甚至可笑之极。欧仁心里想到。殊不知,拉萨尔大主教的心里却又是别的打算。
这次从圣域回来,他觉得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他是被单独地、秘密地召唤去了圣域,受到的是教皇的手谕,却没有见到教皇一面。几个掌实权的枢机主教把他带去了一个密室,类似于现在他身处的地方。他们深情凝重,开门见山便问他知不知道巴黎出乱子了?
巴黎出乱子了?拉萨尔大主教一头雾水,他昨天晚上还在香榭丽舍大街用了晚餐,那里直到次日凌晨都人群熙攘,丝毫看不出出乱子的迹象。
巴黎正蔓延着严重的“圣痕崇拜”行为,他们对拉萨尔大主教如是说。他们点名批评了安托万神父,这位著名的巴黎圣母院院长,似乎从很久前就同“圣痕崇拜”扯在一起。拉萨尔大主教一声不啃,他知道这项指控很严重,如果传言属实,甚至会影响到他本人。
另外,枢机主教们命令拉萨尔大主教派出一批干练的人对巴黎市展开调查。原因来自于不久前梵蒂冈被窃事件。梵蒂冈宗教图书馆的保险库在层层守卫下,还是被不明来客攻破。他或者他们几乎翻乱了保险库里所有绝密文件,直到现在,工作人员还无法完全整理那些被翻得天翻地覆的文件,他们也估计不出凶手究竟想得到什么。
据可靠消息,凶手逃往巴黎。枢机主教们要求他尽量组织人力,调查此事。他们不希望警方介入,因为许多绝密文件是无法公诸于众的。很多东西就连拉萨尔这种级别的人都闻所未闻。
圣域决定让巴黎对自己采取行动。
拉萨尔大主教打得正是这个主意:无论他的意见多么的滑稽可笑,只要他在这个秘密的房间里提出凶手并非来自宗教界,那么当他离开警察局,他就能在媒体面前天花乱坠。其余的人无法否认,因为他的确说过。重要的是,媒体会帮他将消息传到圣域。红衣主教们未必全信报纸的一套,可至少有了种说法,拉萨尔大主教也好在圣域有个交代。
他并不知晓圣域图书馆被窃的事,也想不明白为何圣域三缄其口,只打算小范围搜捕窃贼。然而那些老头们又确信窃贼就在巴黎,再愚蠢的人也能体会到其中不同寻常的韵味。如果再联想到上任教皇几个月前猝死……
拉萨尔大主教正在编织一个惊悚故事,连他自己都不禁打了个冷颤。
回过神来,秘密会议都快结束了。这次碰头其实根本得不出什么结论,拉萨尔大主教和阿道夫内政部长无非是来给警察们施加压力的。
阿道夫最后又唱了几句空洞的高调,那都是说给拉萨尔听得。他还神秘兮兮地冲着欧仁挤对眼睛,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道:“如果需要帮助,可以找他。”
欧仁接过名片,粗略扫了一眼,敷衍的应了一声。
名片上的人是现在秘密警察的掌舵人,欧仁听说过,其中包括他曾经用化名干过的勾当。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名片上的人化名生活于东柏林。他实际是法国派驻在东柏林的特工,负责调查法国共产党同德国以及苏联的联系。并被委任刺杀及破坏等任务。柏林墙倒塌后,他又被派往法属北非殖民地,监视和破坏当时风头正盛的独立运动。没有证据表明他直接参与了大规模的屠杀,但欧仁的耳边时常会有类似的传闻。特别是当他恢复本名出掌秘密警察部门,外界的风闻就更多了。欧仁见过他几次,两人年龄相仿,性格却迥异。某种程度上,那位先生比阿道夫部长更阴险。
不过只要不真的去找他,调查工作就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欧仁局长总算长舒了口气,他送走了两尊瘟神,他们也没过多追问目击证人的事。欧仁想保护两位大学生。通常这类离奇案件的目击者总会倍受关注,这不但会影响他们的私生活,甚至在不断的纠缠下,他们也会下意识的虚构一些情节,以换取暂时的安宁。若真到了那刻,欧仁又得忙了。
他已经计划好,送走了两尊瘟神,便派人暗中保护两位大学生。
殊不知,索菲娅和顾亭然已经踏进了一摊淤泥。
上午九点,送走了索菲娅,顾亭然拖着疲惫的身子,磨磨蹭蹭地回自己的家。春假后,巴黎的天空,一抹浓重的乌云始终挥而不去。湿漉漉的天气比起顾亭然的故乡上海算是舒服了许多,可他仍旧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想到家里墙面上不断蔓延的霉斑,顾亭然更是全身不自在。他向房东投诉了多日,却迟迟收不到回音。他真想扯开嗓子冲天冲地好好骂一顿。
最后一个拐角处,天上突然飘起茫茫细雨。敏感的脸部皮肤在雨水的拍打下微微起着激灵,像是在按摩。烦心事搁在一旁,俗务就一股脑儿的涌了上来。仰头望着那栋小灰楼。顾亭然轻轻叹了口气。他突然想起房间好久没有打扫;一堆臭衣服也没拿出去洗。
密码盘上,总是那几个固定的按钮。顾亭然推开门,融入了黑色的空气里。他家小楼的走道闭不见日,一进底楼大厅就要按动电灯开关。以他的速度,走上四楼,灯刚巧熄灭。此时,右手边会出现一个橙色的小光环。第二次亮灯能让他坚持到家门口,六楼,小阁楼里。
踏上三楼最后一级台阶,他的眼睛仿佛被人夺去,头顶的灯突然灭了。没有丝毫的光明,瞬间内,就连大脑里的思想也一并抢走了一般。
顾亭然双脚僵立在原地,他的第一反应便是自己的眼睛出了状况。克劳德的惨剧始终萦绕在脑海中,他迅速将双手凑近面前。黑暗里,双手隐约可见。
“真倒霉!楼道的灯又坏了。”顾亭然嘟哝到。三楼的电灯开关在走廊的另一侧,他必须摸索着走大约十步路。
刚踏出第一步,他觉得脑后一阵阴风袭来。他想回头看个究竟,可没等跨出第二步,硬物已经重重打在他的后脑勺上。刺骨的疼痛只在瞬间产生作用,他很快边失去了知觉。身子无力地向前瘫软。就在知觉丧失的瞬间,他意外地感到自己竟然倒在一堵墙上。那里应该是没有东西的。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