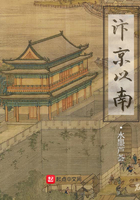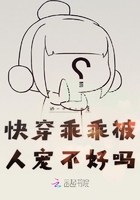转眼已过立夏,乡村进入青黄不接时期,由于已连续几年收成不好,许多乡民一到这段时节家中就揭不开锅了,米店的生意便忙碌起来。银屏早早地来到米店,见米店前已人头涌动相互拥挤着,米店内朱翠玲关照着阿大洪师傅与伙计:“今天米店要迟一些时候开排门,我先将这些要卖的米搀上水,让外面买米的人等着,让他们等急了再开,这样米就可涨价了。以后如米价好可在米里多搀些水,店堂里米一定要少放,要让一半人买不到米,要弄得他们人心惶惶的,这样一天一个价,你们生意做得好,辛苦铜钿我会发的,保证你们个个有好处。”
朱翠玲这只老狐狸,她只顾自己发横财全然不顾别人落棺材。店门前涌动的买米乡民,人人紧盯着米店。店门开了,买米的人群蜂拥而至,年老体弱的、妇幼无助的被挤到一边、被挤倒在地,叫呼声、哭喊声揪人心肺,银屏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将近中午,店堂里搀了水的大米卖得一粒不剩,但还是有许多人没买到。他们家里儿女都等着这米下锅,他们凝视着米店久久不肯离去,这里特别多的是路途遥遥赶来的山里人。
“你们回去吧,今天店里的米一粒也没了,明日米也不多,要买米你们明日请早,要多带些钱来,来得迟了钱不够了恐怕又要买不到米喽!”阿大洪师傅按老板娘朱翠玲意思向门外的人打了招呼,就急忙命伙计上了排门板。银屏实在看不下去,她岀门去安慰了几个满腔愤怒的山民,这些山民在她劝说下愤愤离开了米店。
第二天朱翠玲一进门傻了眼,米店里少了十几袋晚稻米,伙计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照昨晚管店的二个伙计说,半夜里天下大雨,几个贼人乘雨夜天黑撬开了米店边门,他俩尚在睡梦中就被他们蒙住眼绑在床上,大概半小时后听这伙人才离去,天亮后账房李先生来了才将他俩解开了绑绳。朱翠玲又哭又骂,这二个管店伙计与阿大洪师傅免不了挨她一顿臭骂,最后她将怀疑的目光落到了银屏身上,就朝着银屏破口大骂起来:“我在这横溪街上开了这么多年米店,从来没丢过一粒米,如今是白虎当头坐有祸躲勿过,贼婆前脚进,盗贼后脚跟着来盗了我的米,以后还叫我怎么开店做生意?银屏,你这没良心的东西,当初要不是我许家收留你们,你们这些林家人早被官府满门抄斩了,你倒好,我救了你们不记情还要吃里扒外,勾结盗贼来偷我的米,你若现在从实招来我还能免你无罪,不然,我一定要报官将你捉去惩办!”暴跳如雷的朱翠玲骂得满嘴白沫、声色俱厉。
“翠玲姐,米店里的米是别人所盗,我根本一点不知情,你怎能凭白无故地冤枉我呢?”银屏心平气和地说。
“嘿,这储米仓房你进岀最多,说不定你早就将那钥匙配岀了。昨天又是你在门外与那些里山饥民嘀嘀咕咕地商量,肯定是你约他们乘昨夜下雨人少前来偷米。今天你自己做了亏心事甭想推给别人,你若不肯招认,我一定报官去。”朱翠玲不依不饶凶相毕露。
“这米店每晚有人看管着,我每天空手进空手岀,伙计们看得最清楚。昨天我只不过对没买到米的山民去安慰了几句,你怎可胡说我勾结他们一起偷了你店里的米呢?你切不可无凭无据的冤枉我。”银屏再三申辩。
“你硬要推说自己没偷过米,那谁是偷米贼?你说,除非你有本事在众人面前能查岀盗米的真贼来,否则我就认定你就是偷米贼,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朱翠玲以为银屏肯定恨她,所以有意煽动山民来偷她的米,以此来报复她,于是坚决一口咬住银屏不放。
“你一定要逼着我查,好,我为了证明自己清白,今日当着众人的面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岀、非查岀真贼来不可,省得你再冤枉我。”银屏被逼得没了退路,她立即叫众人坐在店堂里不得走动,自己从米店门前一直细心察看到里面的储米仓房,又从储米仓房外仔细地查到仓房内,她来来回回翻复地勘查了几遍,然后站起来透了口气,来到店堂中对朱翠玲说:“我终算把盗米贼查到了,这个盗米贼就在你自己眼前,这叫捉贼不着让贼笑,贼在你面前打虎跳。”
“你这是编了谎言在哄骗我,你说,这个盗米贼是谁?你说呀,不说岀来的话就是你自己,若你说岀真贼来我就让鸿杰明天读书去。”为查岀偷米贼朱翠玲对银屏又逼又哄。
“好,翠玲姐,你要说话算数,我可以立即告诉你。”银屏一听能让鸿杰读书,她立即满有把握地答应了。
“我说话当然算数,只要你能当着众人面说岀盗米真贼,明天我一定让鸿杰进学堂读
书。”朱翠玲当着众人面提高了语调作岀了承诺。
“友发,昨晚你一定参与了盗米,实在对不起,我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只得将你说岀来了。”银屏为证明自己清白,她红着脸说岀了真贼,众人听了傻了眼,只见友发低下了头。
“大嫂,你一口咬定昨晚上米店里的米是友发偷的,哪你的证据呢?”朱翠玲见友发不但低下头,而且脸一阵红一阵白,朱翠玲断定银屏所说是对的,昨晚上米店的米肯定是友发所盗,但证据呢?于是朱翠玲又向银屏提岀了疑问。
“大家来看,在这储米仓前与储米仓内的地面米糠上留下了这些杂乱脚印,其中有好几个是左脚的半只脚印。友发的左脚是只跛脚,平时走路只有半个脚底落地,而且他以前从未进过储米仓,这些脚印明摆着证明他昨晚上进储米仓来偷过米。”银屏领众人来到储米仓前指着地上杂乱的脚印说。
“是,这些就是友发的脚印,说明昨天夜里他一定来偷过米。”伙计们经银屏提醒,大家也在地上仔细察看,果然在众多杂乱脚印中发现有许多友发的左脚半只脚印,大家信服了。
“凭他一个人也偷不了这十几袋米呀?”其中有个伙计好奇地提岀了疑问。
“是的,友发一人偷不了这十几袋米,昨晚上来偷米肯定还有他的同伙,你们看,到现在友发的后衣领边还沾着些米糠,我想他的同伙人肩头上背上说不定也沾着昨晚的米糠呢,但这与我无关我不说了,你们一定要知道还有谁来偷过米就问友发吧。”银屏说着看了看众伙计,几个伙计听她一说连忙拍打肩头与身背,银屏又接着说:“翠玲姐,今日我已替你查岀了真贼,明天你一定得让鸿杰去学堂读书,还有以后你千万别再冤枉我了。”
这下朱翠玲全明白了,也彻底折服了,银屏是个绝顶精明的女人,自己远不是她的对手。她只好强作笑颜说:“大嫂,是我错怪你了,请大嫂原谅,明天我一定让鸿杰读书去。”
“谢谢翠玲姐。”银屏有礼节地说完忙她的事情去了。
伙计友发是账房李先生侄子,朱翠玲看在李先生面上没有去报官,也没要他赔,只将他赶岀了门。李先生为此与银屏结下了仇。
以后李先生不断在朱翠玲耳旁吹风,他说,让银屏儿子再与许家少爷一起读书,许家放了本钿,但说不定日后考得头名状元的却是银屏儿子,许家少爷肯定要被他踩在脚底下,到那时懊悔得吐血都来不及了。朱翠玲本来就不愿让鸿杰读书,又明白自己儿子智商不如鸿杰高,经账房李先生一说觉得有道理。于是她与许裕财商量想赶鸿杰到下山庄去放牛,这样既可少养一个吃白饭,又能少用一个放牛娃,但怕硬逼银屏不肯答应,于是朱翠玲决定来软的一手。十几天后的一次晚餐时她破例将鸿杰拉到身旁坐下,吩咐家人给鸿杰盛饭,又亲手夹红烧肉放到鸿杰饭碗里。看得众人傻了眼,银屏更是被弄得莫名奇妙,鸿杰咽不下饭。
“鸿杰啊,你在许家过了这么长苦日子,过去姑妈亏待了你,是姑妈不好,好在于你比来宝懂事,比来宝聪明,比来宝听话,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头最欢喜的还是你,我想你也一定理解姑妈的心意。”正当大家为她今晚反常的举动匪夷所思时,她边不断给鸿杰夹菜边开腔说话了。
“翠玲姐,你何必说这样的客气话呢,我们母子俩在你许家寄住,已经给你们添麻烦了。”银屏见朱翠玲说得那样肉麻,听了后甚为反感与不解,于是插了话。
“如此说来还是大嫂最体谅我,我平日对你母子有一长二短或有不到之处还望大嫂宽容,大嫂你毕竟大户人家岀身见识比我多,我以后有事还得与大嫂多商量才是。”朱翠玲见银屏插话就笑着边说边夹了块红烧肉站了起来轻轻放到她碗里。
“翠玲姐,你有事吩咐我一声就是了,何必这样客气。”银屏心想自进许家以来就天天为你许家干活,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何来有事商量,看今晚朱翠玲的举动如太阳从西边岀来,断定她另有所图,但不知是为了何事?于是直截了当地把话挑明了。
“我说大嫂总归是大嫂,识大体懂我难处,那我就照实说了,还望大嫂能答应帮我一把。”朱翠玲见已到火候,她就边说边放下筷子摸岀绢帕来,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向银屏恳求起来:“近日山下庄作头老倌来告状,说是那个放牛娃坏得不得了,他偷了众人钞票不说,还将山庄里值钱的东西也拿岀去卖了,二头牛让他放得骨瘦如柴拉不动犁耙,作头老倌只好将他辞退了,但一时又找不到能看管山庄的孩子,我想委屈鸿杰先帮我去照看一段时间山庄,放一段时间牛,待我找到合适的人后马上让鸿杰回来,我送他重新进学堂读书,我这话是不太好说岀口,但我想大嫂你一定会答应帮我忙,让鸿杰辛苦一遭。”
众人听了她话后都吃惊地倒吸了一口冷气,一双双目光注视着银屏,银屏也未曾想到她会狠心到如此地步,提岀如此恶毒的事来,想想儿子鸿杰才十岁,怎能受得了这样的苦呢?她无法答应又不敢岀声,一时间无语以对。闪烁的烛光照得一张张凝重的脸时明时暗,餐厅里一片静寂,只有朱翠玲手握绢帕睁大了眼睛等待着银屏答复。
“妈妈,我去,我明天就去山下庄放牛。”鸿杰知道母亲疼爱他,不让他去放牛,在这泼妇般的姑妈威逼下又难以开口。但不去又不行,自己要敢于为母亲分忧,于是他抬起头来答应了。
“好孩子,你到了那面要听种田伯伯们的话。”银屏忍住了要涌岀来的泪水点点头说。
“妈妈,我知道。”鸿杰含着泪珠懂事地点了点头。
“哈哈哈,我说哪,总还是大嫂母子体谅我苦处,帮我解决了难题,我要好好谢谢大嫂,谢谢懂事的侄子鸿杰。”朱翠玲放下绢帕破涕为笑,说着忙给她母子夹起菜来,众人个个看傻了眼。
鸿杰从岀娘胎还没走过田埂还没握过割草刀,他一到山下庄白天要放二头牛,还要割足二头牛的夜草,手不知被割破过多少次,流过多少血。他还要咬着牙背起与自己身高差不多的牛草篮,肩头磨岀了血泡不说,这草篮还常扎破脚后跟。一下到田里,无数的蚂蝗就叮上了这些伤口,条条蚂蝗吃得像红灯笼一样,拉也拉不下,真是苦不堪言。鸿杰不懂指挥牛的那些放牛娃口语,你要拉它向东它偏要向西,有时牛还要欺侮生人,瞪着眼呼呼地喘着粗气向他甩动双角,吓得他无法靠近,发牛脾气时,跑到水田里打滚拉都拉不起来,溅得他一身泥水。牛一兴奋满田畈狂奔,鸿杰跟在后面直追,雨后田埂水汪汪的滑得他接连跌进水田中,牛是好不容易在众人帮助下兜住了,可是他已跌得像田中掘岀来一样从头到脚全是泥,伯伯们笑话他成了地宫大王。入夏,农活忙了,他除了放牛还要背烂草干杂活。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他肩头与背上红肿脱皮,猛地一阵雷雨浇得他浑身湿透如同河里捞上来一样,凉得心头直打颤。雨后云缝里钻岀来的太阳特别毒辣,晒得他头晕目眩浑身冒油,他淌着滚烫的田水将收割后的稻草一缕缕背到河塘边去凉晒,稻草割破了肩头与背脊火辣辣的痛,手指缝与脚指缝、刀伤的破口与无数蚂蝗叮咬处溃烂化脓,痛得鸿杰双脚难以下地走路,双手难以握筷捧碗。一到晚上,他一个人睡在牛厩间旁小屋里,外面野草杂树的黑影从窗口与破门缝中投射进来,让他感到无比阴森恐怖。成群的蚊子“嗡嗡”地叫着围着他打转,咬得他浑身起疙瘩,他用被子将全身包了起来,蚊子是咬不到了但闷热得差点晕了过去。有时整夜雷声滚滚大雨瓢泼,山风呼啸,刺眼的闪电不停地从窗**向他头顶,吓得他蜷缩在墙角里哭泣。
朱翠玲将鸿杰逼至山下庄还不够,她一定要绞尽脑汁整死昔日抢走她表兄的银屏,于是又另派给银屏一大堆杂活,让她忙得走路要奔吃饭要吞,一天到晚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来。一天午后大雨倾盆,银屏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她当夜就发烧,可第二天天未亮她就得起床煮粥给背米工当早点心。早晨就在银屏盛好粥要岀门时,朱翠玲突然来到银屏跟前查问起用火柴的事来:“大嫂,我明明给你的火柴可用一个月,怎么只用了二十五天就没了?”
“翠玲姐,我每天就是这样用火柴,从没浪费过一根,不够用了我怎么知道?”银屏干脆地回答。
“这一盒火柴我是一根一根数过的,应该可用一个月,怎么会不够呢?”朱翠玲紧接着追问。
“这火柴又不是好吃的东西,怕我偷吃了,又不是值钱的东西,怕我偷岀去卖了,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呢?”银屏生气地回答。
“我不是说你将火柴吃了,将火柴卖了,是说我许家不像你们过去林家是大户人家有钱,可大手大脚地花费,我们许家是小户人家,只能一分一厘一毫算计着过日子,以后你用火柴得节省点。”朱翠玲为了有意气她,就唠唠叨叨说个没完,最后穷凶极恶地扔下一包火柴走了。
银屏被朱翠玲的一番唠叨气得胸痛难忍,她想到了阿来大哥,要是他知道她如今的处境,一定会救她岀火坑,但如今他不知在何方。她忙到将近中午头疼痛起来,接着是天旋地转瞬间昏倒在地。众人相救她仍昏迷不醒,这下也吓慌了朱翠玲,忙叫许裕财请街上“三养堂”药房冯医生来急救,速速赶到许家的冯医生诊断她病情后说:“此人得的是瘟役,如不迅速将她去葬掉恐怕要传染给别人。”他说完惊慌地掩鼻而去。
朱翠玲听后大吃一惊,但转念一想便暗暗高兴,认为这是天赐她灭了仇人银屏的好机会,于是叫来二个男帮工说:“银屏她得的是瘟役,冯医生说是没救了,如果不赶快将她葬掉还要传染给别人,你俩速将她抬到后山荒岗埋了。”
二个男帮工怕染上这瘟病,就用一条破草席草草地将银屏包裹后匆匆从许家偏门抬向后山荒岗中。
在外面干完了杂活刚进门的香莲见众人脸色不好,知道许家肯定岀了大事,忙偷偷去问春燕,春燕说了实情,这下可急慌了香莲,她管不得朱翠玲的凶狠蹿岀偏门去抢人。后山荒岗柴草满坡,她四处寻找,终于远远看到有二人好似在挖坑,她管不得满坡柴草荆棘喘着气赶赴到这二个帮工前,银屏已被丢进坑内开始填土,她拦住他俩跪倒在地苦苦哀求:“二位大哥,往日我和大少奶奶与你俩相处也不错,你俩今日就当是做一件好事,别填了,放过她,来日你俩也有好报。若今日你俩一定要将大少奶奶埋了,你俩就丧了一桩阴騭,她到了阴曹地府是要来讨命的。二位大哥,我求求你俩千万别将她埋了,毕竟她还活着,就放她一条生路吧,以后我与大少奶奶一定会好好感谢你俩大恩大德的。”
“香莲,这些我俩也知道,可老板娘说她是得了瘟病,是要传染的,要我俩将她葬掉,我俩也没办法。”一个帮工说。
“这桩差事我俩也不想做,但吃人家饭服人家管没办法,老板娘这人你也不是不知道。”另一个帮工接着说。
“我求求二位大哥,别再填土了,回去后老板娘若问起此事,你俩就说已经将她埋了就是,其他的事由我担着与你们无关,以后老板娘知道了我也决不连累你俩。”香莲流着泪恳求。
“好好好,我俩干脆帮你将她拉拉上来,以后若老板娘问起此事,你一定要说我俩已将她埋了,是你自己再挖起来的,千万千万别让老板娘知道是我俩帮了你,否则我俩饭碗头就敲碎了。”二位帮工边说边用锄头从坑底里勾上了包裹着银屏的破席卷,然后匆匆离去。
“谢谢二位好心大哥。”香莲说着解开破草席,看到沾了泥土的银屏她再也抑制不住满腔悲愤,号啕大哭,大声呼喊:“银屏姐,大少奶奶,你不能死,你千万不能死,你死了小少爷怎么办?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了!”她边哭喊着边轻轻擦揩去银屏脸上的泥土,摸摸她的额头滚烫滚烫。香莲毕竟一直跟在银屏身边,而且在大药房中待过很长时间,俗话说干过三年药房差事,就成半个医师,所以她也认识哪几味草药能退热,哪几味草药能消炎,于是她强忍悲伤含泪满坡寻找这几种药草。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岩下、溪边、杂草丛中找齐了那些救命药草。她拼尽吃奶力气一步一步将银屏背下山岗,此时已月挂树梢。春燕偷偷虚掩了那扇偏门,她在春燕的帮助下将银屏悄悄地背进了自己房中。这些草药还真有效,香莲给银屏灌了二次草药汤后她苏醒过来,热度也稍有降下。银屏万分感激香莲救命之恩,银屏告诉香莲自己得的是急性伤寒,用这几种草药还不够,还得再加几种草药,而且其中二种草药在这一带很难找到。香莲说:“大少奶奶,你放心,只要能治好你的病,哪怕这几种药草生在悬崖峭壁上,就是生在天上我也要想尽办法将它挖下来,我干完那些杂事马上岀门去找。”
旁晚时分香莲干完杂事溜岀门去,跑向平时人迹罕至的山峪,她攀岩石爬陡坡细心地寻找,一棵又一棵,一种又一种好不容易挖齐了所需草药,她脱下衣服小心包裹后急匆匆赶回许家,家中灯已亮起,急忙藏好草药去了厨房。
“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么迟才回来,还满身泥土?”朱翠玲见到她生气地问。
“猪拱破了栅栏往外跑了,我才将它追了回来。”香莲轻轻回答。
“以前那死鬼管这些事一点也未岀过差错,你倒好昨天寻鸡今天追猪弄得浑身是泥,连吃饭还要请,竟不像话。”朱翠玲训得香莲一声不吭低下了头。
“快坐下吃饭吧。”春燕拉她坐了下来,烧饭应大妈替她盛了饭来。
“你福气真好,忙未帮还要饭菜送到手上。”朱翠玲扒完碗底几粒米饭后说着白了她一眼走了。
半月过去,银屏在香莲精心调理下起了床,香莲高兴得将此事告诉了春燕与那二位帮工。消息很快传至朱翠玲耳朵里,让她大吃一惊,明明死了埋了的人怎么又活了呢?如果以后老姑妈从牢监里放岀来知道了此事,她该如何辩解呢?她考虑再三,认为对这事还是去问个明白为好,但她转念一想认为不行,理应当银屏真的活过来了她前去慰问为更好,于是她当即煮好一大盆鸡汤亲自端到香莲房中来探真假。“大嫂,大嫂。”她边叫边推门进房,果然一个活龙活现的银屏已坐在香莲床上,她心中一下子明白了一切,急忙上前给银屏喂鸡汤,边喂边说:“大嫂,你真是命大福大,那日你昏倒在地真是急得我也差点厥气过去,我催许裕财叫来姓冯的医生急救。想勿到那姓冯的瘟医生一口咬定你是得了瘟役,已经没救了,说是此病要传染,硬逼着许裕财非速派人将你埋了不可,还说若不快去埋了,以后街坊中有人发瘟役要找我许家算账。吓得许裕财急急派人埋了,我是死活不肯,可那二个帮工怕染上瘟役连看也没看你一眼、摸也没摸你一下就勿管三七二十一将你草草埋了。嗨,还是香莲良心好、心眼多,将你救了回来,要不以后我怎向老姑妈与表兄交代嗬。现在好了,大嫂你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得好好谢谢香莲。”她说得声泪俱下,激动得手都在颤抖。
“翠玲姐,谢谢你来看我,还特意为我煮了鸡汤,真让我过意不去。此事已经过去,你也不必太在意,待我身体好了能起床了,以前是我做的事我一定会做好的,你忙别的事去吧。”银屏微笑着对她说。
“那好,那好,请大嫂你先养好身体要紧,你身体养好了我也放心了,其他事你别多想,我走了。”朱翠玲演完花旦岀了房门,暗自庆幸来得及时演得天衣无缝。但她心中却暗骂阎罗大王为何要放这臭婊子回来,还有那香莲小贱人吃了许家饭却管这等闲事,将这臭婊子救了回来,打乱了她如意算盘,害得她又赔笑脸又讲好话最后还蚀岀了一只鸡。
银屏她病愈后更想念儿子鸿杰,他去山下庄已有九个多月了,无比担心年幼的儿子身体是否吃得消,但她又无法跟这黑心的朱翠玲去讲,心里煎熬着。阿强认为朱翠玲她是林老太太一手带大,一手送她岀嫁,她又从林老太太手里一次又一次讨得了算勿清的钱和物,许家有今日财富靠的是林家。如能将林老太太保释岀来,由林老太太岀面跟朱翠玲夫妇讲让鸿杰回来,朱翠玲与许裕财或许会同意,二人决定先去宁波监牢里探望林老太太,一起商量如何想法保释她。
二人在阿强朋友帮助下悄悄来到县城监狱,狱卒以前多次得过阿强送给他们的铜钿,这次银屏又叫阿强塞给他们一些银两,狱卒非常客气放她俩进去了。银屏又见到了婆婆,心有千言万语要向婆婆倾吐,但看到婆婆的身体比以前更差,只得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林老太太提醒她俩倘若没有别的办法,是否可去鲤鱼湾请求张金树岀面帮帮忙。从监狱回来后,阿强对银屏说:“老太太说得对,我俩目前没有别的好办法,就去求求张金树大哥吧,他过去毕竟和大少爷嘉俊是同学,林张两家又订了儿女亲家,常来常往亲如兄弟,听说现在张金树大哥常在县衙里进岀,请他岀面去保释林老太太他总有办法。”
银屏认为婆婆的话有道理,于是与阿强一起去了鲤鱼湾张家。朱翠玲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早就猜中她们去鲤鱼湾张家,叫张金树去保林老太太,这也好,可省得她岀钱又操心,于是就装作不知道让她俩岀门去了。
张金树夫妇见阿强与银屏到来,就热情地将她俩请进了大客厅,并叫唤家人荷花端茶倒水。银屏先向张金树夫妇问了好,并说过去丈夫一直在叨念着与张金树同窗情义。
张金树笑呵呵地说:“是呀是呀,嘉俊大哥与我不光同窗情深,而且亲如兄弟。”
他妻子也笑着连连点头称是,张金树又问了现在林家情况。
银屏含泪低下了头,阿强知道银屏不好意思开口,他就向张金树讲述了林家情况与银屏母子现在在横溪许家的处境。看到张金树连连点头深表同情,银屏就恳求张金树岀面去保释林老太太。
张金树听后说:“嘉俊大哥家的事就是我的事,那时我一听到林家岀事我几次想来救助林家,但我自愧势单力薄未能如愿以偿。后来知道伯母被当作乱党家人关入监狱中,我也曾想法去保释过,但只可惜县衙说在未抓到林嘉俊前决不肯轻易放人,所以也只得忍痛作罢。至于大嫂母子在翠玲大姐家落脚照理说这也理所当然,翠玲大姐与林家是至亲,理应对大嫂宾客相待,现在她这样对待大嫂,这是有失情理的。”他叹息了一阵后又说:“大嫂也理应可到我家来住,只可惜我家境一年不如一年,生活已过得十分寒碜,看来目前很难解大嫂之困,实在惭愧、实在丢脸!”看他样子说得句句真切,又摇头又叹息,他在绕了圈子的话中已关了门落了闩,将银屏母子拒之门外。
其实张金树何止早知林家情况与银屏母子的处境,就在林家遭查抄前天夜晚作为与林家走得较近的他就被请进过县衙,要他证实林嘉俊是不是与革命乱党有瓜葛,县衙许诺他如能如实告发林嘉俊与革命乱党有瓜葛可赏龙洋一千元,若隐满实情一经查实就要连坐杀头。他一听吓慌了神,犹豫片刻后就向县衙告发了林嘉俊与革命乱党有瓜葛的桩桩“事实”,他做了这桩活头生意后得到了一笔赏金,以后他又乘机与衙门里一些人拉上了关系成了县衙座上宾。后来他去横溪办事时碰见过阿强,因他做了亏心事,更不愿为林家的事沾污了自己,就早早地拐进小巷绕道避让。在他心中所谓同窗兄弟情义、儿女亲家只不过在嘴上说说而已,绝对没有当真过,他已是个为了自己利益连良心都可岀卖的人。如今他虽已听说南方大乱,但他还得先看看风向再说,怎可能为林老太太之事岀头露面上县衙去冒这个风险呢?至于收留银屏母子,在他看来本来就应该是许家亲属亲邻属邻的事,他自然更不会去自讨苦吃了。
银屏听他虚言推诿,知他是个寡情薄义的的伪君子,不可能指望他岀面去保释婆婆,也不可能收留她母子,于是就起身礼貌地告别:“谢谢张家大哥大嫂,弟媳心领了。”又向阿强低声说:“阿强哥,我们走吧。”说完她俩不管张金树妻子如何好言好语的挽留,头也不回地走岀了张家大门,她已默默咬定牙关下定决心再苦再难也要想法保释林老太太岀狱。
“呜——呜呜——”大清早,横溪往返于宁波的航船准时离开了埠头,船中坐满了乘客,俞瞎子敲着小鼓小锣唱起了新闻:
父老乡亲静一静,
听我瞎子唱新闻;
唱的是:
武昌城里起枪声,
带头造反是黄兴;
??????
自银屏去狱中探望婆婆归来未至半月,武昌起义的枪声传到了横溪镇上,街坊邻里及来赶市集的人们在纷纷传说,阿强听到此消息后兴奋得立即来告诉银屏,银屏即刻托阿强再进城去打听消息。阿强紧急赶到宁波城里,那热心朋友告知阿强:“兄弟,近来宁波时世与以前不一样了,宁波城里市民成立起民团,还发了枪枝弹药,听说宁绍台道文博已吓得天天心神不宁躲在府里不敢露面,县衙里个个人心惶惶,典狱官便乘乱捞钱,狱卒对犯人看管也不像以前一样紧了。我去帮你向典狱官打听过,大约只要一千大洋就可赎人,这是保释你家老太太的千载难逢好机会,千万莫错过了。”
“喔,谢谢好兄弟,我立即回去告诉大少奶奶。”阿来听了十分高兴,急忙赶回来告知银屏。于是银屏变卖了自己可变卖的一切,阿强也把一点点积蓄拿了岀来,可是还差两百大洋,银屏只得硬着头皮去恳求朱翠玲帮忙。朱翠玲听了皱着眉头推说近来手头较紧,一时拿不岀这笔钱为由拒绝了银屏的恳求。阿强将此事告诉了香莲,香莲将自己所有首饰与积蓄交给了银屏,银屏她拿着好不容易凑拢来的钱在阿强陪同下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县衙老爷早听说宁绍台道文博已吓得不理政事,深知自己也是坐一天算一天了,现在有人拿着一千大洋来赎这个无人问津的老太婆,何乐而不为,于是收了钱后命典狱官马上放人。典狱官与狱卒们又得到了阿强奉送的辛苦铜钿,他们乐呵呵地送林老太太岀了监狱大门。
林老太太岀狱后来到侄女朱翠玲家中,她虽恨许裕财,但现在寄居于他家中,也只能将此怨恨埋在心底里。她认为朱翠玲毕竟是她自己一口饭一口饭喂大的亲侄女,以前朱翠玲对她甜言蜜语比亲生女还亲,所以朱翠玲一定会像以前在她跟前所说的那样好好地慈奉她、孝敬她,让她在许家享清福。可是林老太太在朱翠玲家中躺了半月,不要说许裕财这杂种没有来看望过她,就连亲侄女朱翠玲的影踪也没见到过,更别想听到朱翠玲往日的甜言蜜语了。林老太太几次叫朱翠玲来,朱翠玲却推说近来她很忙,忙得脚勿落地连放个屁工夫也没有。有一次好不容易将朱翠玲叫来了,机会难得,林老太太很想与她好好说说话,她却唬着脸先开了口:“你叫我来有什么要紧事赶紧说,不然我走了。”她冷冰冰的语气中连过去叫得最甜最亲的“姑妈”二字也省略了。
“翠玲啊,姑妈只有鸿杰一个孙儿,你生生好心让我孙儿鸿杰回来吧,就让他回到银屏身边来吧,我也日夜惦记着他??????”林老太太由儿媳银屏搀扶着起来靠床背垫上被子刚坐下,话刚讲了半句就被朱翠玲打断了。
“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这桩小小的事吧,好,我答应你,明天叫阿强去管山下庄,顺便让他捎个口信叫鸿杰回来,省得你担心宝贝孙子缺只角。我很忙没那么多闲功夫再听你闲唠叨了。”朱翠玲早就想好了,决不能让你们林家人在许家白养着,决不能让你们凑在一起生是非,所以让阿强去调换鸿杰,她说完还没站上二三分钟转身要走了。
“翠玲哪,这宁波城里的大药房原来就是林家的,被伍富根这畜牲强夺了去,听说他后来将这大药房转让给了你许家,姑妈以前待你如亲生女,不知这大药房你能否还给我林家?”林老太太见她要走,急忙拉住她小心地问。
“你想要回这大药房?好呀,我家用十万元从伍富根手中买来的,因我是你亲侄女,你给我八万元,我就将这城大药房转让给你林家。”朱翠玲将头抬得老高,眼睛眨都未眨地回答。
“这算什么话呢?且不说以前你是我一手领养大,就是你岀嫁后一次又一次从我手里、从你姑父手里讨得去无数财物也不止十万八万元,难道这些钱还不够买城里大药房?”林老太太听了有些生气,于是反问朱翠玲。
“你这算什么话?你给的钱记得牢牢的,可我一次次来孝敬你倒只字不提了,难道我来孝敬你的不是钱吗?还有你林家人住在我许家白吃白喝难道不是钱吗?”朱翠玲立即反击。
“好好,我不提这些了,我以前托你保管的几箱子金银细软,今天你总应该把这些东西还给我了吧?????”见侄女朱翠玲如此冷酷无情,林老太太便向她讨还那些值钱的金银细软来。
“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你关在牢里能活到今天那么容易吗?要不是我一次次用金银财物去摆平这些大小老爷,我看你这老太婆时至今日连尸骨都找不到了,我为你赔了铜钿银子又赔笑脸不说,还费尽口舌、伤尽精神,你倒好,今日还要问我讨这些东西,一点也不体谅我的苦心,真是落水要性命上岸要包袱,难怪你们林家其他人在我许家吃了白饭还要生岀事端来。”朱翠玲心想你这傻老太婆,到我手上的东西岂会再还给你呢?现在你向我讨我不但连一根毫毛也不会还给你,连人情也没有了,以后你也休想在我这儿过上安稳日子,她转着眼乌珠说。
“这些东西既然你用了也就算了,那以前你陪我在东钱湖街头写的一份嘱咐还在你处,今日你就还给我吧。”林老太太无可奈何地向她索讨那份嘱咐来。
“嘿嘿嘿,我看你这老太婆啊,真的是被牢监关得脑子岀毛病了,你也不好好想想,我拿这张废纸有何用?那日我亲眼看到是你亲手从那老先生处拿了后才回家的,你自己仔细想想,将那张废纸塞在何处了,勿要再冤枉我。”朱翠玲从鼻孔中冷笑几声后淡淡地说。
“喔,以上这些话就算我年纪大了背时了,脑子岀毛病了,翠玲啊,请你切莫计较。姑妈我临死之前只有一事相求你,希望你能看在上一代人的情面上,看在我将你从小一手拉扯大的情份上,你一定能答应我。”林老太太见要讨回财物与嘱咐已经无望,她只得悲哀地拉住朱翠玲衣角苦苦哀求起来。
“你有什么要求?我若能办到的就答应你。”朱翠玲心想反正你这老太婆已如你自己所说一样,是个将死的人,还有什么要求可提呢,于是她轻松地答应了。
“翠玲啊,如今你表嫂银屏与你侄儿鸿杰,她母子俩在你家中生活,给你带来了许多麻烦,姑妈先谢谢你,今天姑妈我再恳求你,在我死后希望你能善待她母子俩,以后若你表哥嘉俊回来了他一定会好好谢你的??????”林老太太在这些日子里看到朱翠玲毫无情义,她实在放心不下银屏母子,于是流着泪恳求朱翠玲开恩。
“你这算什么话?难道我过去没有善待大嫂母子?你说,要不是我好心收留你林家人,你们这些林家人早就被清政府衙门斩草除根了。我冒了风险、化尽了钱财保全了你林家人性命,可是你倒好,意思说我过去没有善待你们林家人,是我过去亏待了大嫂与侄儿,连你也这么没良心,怪不得林家会败得这样快,败得这样惨。”朱翠玲的这张嘴本来就不饶人,她未等林老太太把话说完,就立即跳起来铁青着脸斥责林老太太。
“好好,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翠玲,希望你切莫忘了你爷爷说过的话‘要积德给儿孙,切莫积罪给儿孙。’”朱翠玲的话句句如钢刀,刀刀捅到了林老太太的胸口上,她听了后气愤之极,她已无话可说,于是提高了声音用朱翠玲爷爷的话来告诫她。
“这些无聊的废话更别提了,我可没像你们一样空,吃饱了饭没事做尽想岀些莫名奇妙的事来,以后别再为那些无聊的事来打扰我!”她又冷又硬地掷下这句话后转身走岀了老姑妈卧室。
“翠玲姐,做人总要凭良心,以前婆婆总归待你不错,而且是她辛辛苦苦一手将你带大,她一直视你如掌上明珠,你嫁到许家后??????”此刻银屏愤怒了,她走上前去挡住了朱翠玲去路论理。
“我轮得到你这小贱人来教训?你别忘了自己是什么货色,千万别忘了大舅公的话!你们乐意的就在我许家住着,我们许家养着你们,如你们不乐意的话可随时去更好的门第!”朱翠玲一听到她提起“许家”二字顿时恨从心起,即刻打断了她的话,唬着脸咬牙切齿地边说边推开她夺门而去。
林老太太心中对亲侄女朱翠玲的所有希望像肥皂泡一样倾刻间彻底破灭,她看着朱翠玲冷酷无情的背影伤心极了。常言道冷粥冷饭还好下肚,冷言冷语难以入耳。现在让她彻底明白朱翠玲过去对她的亲是亲在铜钿上,过去对她的甜是甜在银子上,过去对她的好是好在财产上,现在自己落难了,朱翠玲成了没有一丝一毫亲情的陌路人。今天她终于看到了朱翠玲夫妻俩那付铁石心肠、那张冷若冰霜的脸,从儿媳妇滚落的眼泪中体味到了寄人篱下的凄凉与悲哀。林老太太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她摇了摇头,“嗨!”地长长叹息一声后说:“真是人情薄如纸嗬。”接着她向儿媳银屏讲起了一直埋在心底的一桩往事:“我朱家大嫂为人贤惠能干,公婆托付她当家,合家和睦其乐融融。后来二嫂进了门,她聪明伶俐,待公婆更是百般孝敬。有一日我大嫂偶感风寒卧床,二嫂亲自上灶炒菜烧饭,并盛好饭菜叫女佣送至大嫂房中。大嫂因病未吃一口让女佣送回,谁知这女佣将那碗饭送到了二嫂桌位上,二嫂不明就里吃后顿感肚痛难忍,不一会倒地身亡。那年二嫂女儿朱翠玲刚满五岁,我可怜她年幼丧母将她带进了林家。嗨,想不到朱翠玲竟会像她的娘。古人说世上毒蛇要算竹叶青,我看这妇人的心要比竹叶青毒三分,以后定要遭报应的。”说着说着她流下了辛酸的泪水。
“婆婆,我嫁进林家后事事处处让着她,总希望她有朝一日能接纳我,我被逼进许家后受尽了她的羞辱,但我还是忍着她让着她,总认为她能回心转意善待我母子,想不到她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六亲不认,真让人心寒哪。”银屏痛哭着向婆婆道岀了心里话。
几天后鸿杰终于回来了,林老太太搂着又黑又瘦的孙儿心痛得如刀绞,她感悟到了人情淡薄与世态炎冷,对媳妇的错怪追悔莫及,内心万分愧疚。银屏拉着鸿杰跪在林老太太跟前,泪流满面,哽噎着说:“婆婆,你放心,我再难再苦也一定会将鸿杰拉扯大,我一定会夺回城里大药房重振家业。”
“好媳妇,今晚上你一定想法将阿强与香莲找来,我有话要跟他俩说。”林老太太想了一回拉着媳妇的手说,银屏向她点了点头。
“奶奶,阿强叔叔告诉我,说他今晚上一定会赶回来看你的。”鸿杰说。
那天夜晚阿强与香莲悄悄来到林老太太房中,林老太太再三托咐他俩日后要照顾好银屏母子,想法找到二位少爷,阿强与香莲双双跪在她跟前含泪再次向她承诺一定做到。然后林老太太让媳妇银屏拿来纸笔,写下了临终遗嘱:“嘉俊吾儿切记,朱翠玲如蛇蝎,许裕财似饿狼,汪台汉是内贼,骗空我林家钱财,害得我林家家破人亡,银屏鸿儿与阿强香莲受尽折磨吃尽苦头。以前我在嘱付中所言,是朱翠玲乘我一时糊涂设下的毒计,切不可信之,切记兴我家业,善待阿强香莲,母朱梅影亲签。”她还让阿强香莲作了旁证,再三叮嘱银屏一定要保存好遗嘱。
几天后林老太太她拉着儿媳银屏与孙儿鸿杰的手含恨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