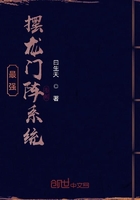抗日如同流行性感冒,从东向西席卷过来。成为街头儿巷议热衷的话题。
有的说着说着,嚎啕大哭,曰国之将灭,何以为家。
而某些人说着说着,瞅根电线杆子过去,撒泡尿,就不知所踪。该吃的吃,该喝得喝。对于他们而言,抗日是别人的事,自己负责赞美就是。
绝大多数人,则连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有什么不同都不知道,脑壳一热,瞅个人就要日人祖宗。上了战场,向对面的扔手榴弹,打枪籽籽。
好不热闹。眼睛一睁,发现打错了,对手是友军。
实在是糊涂得紧。
没办法。糊涂虫大多热血。
很多人因此成了烈士,永垂不朽。同理,有人成了杀敌英雄,戴上了英雄勋章。加官进爵,荫及子孙。
都匀师范学校里,这样的糊涂虫倒是少些。因为大都是文化人,视野当然也开阔许多。他们大多则热衷于谈论日本人打到哪里了,光头先生带着他那爱出风头的“darlig”又逃到了哪里,诸如此类的。
如此带着调侃的语调,谈论自己国家之元首,确实有失尊重。于自己也有失体面。所谓一荣俱荣,一辱俱辱矣。
都匀师范学校,座落在东山脚下。前身是鹤楼书院。
传说是为了纪念明代,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贪贿乱政的忠臣张翀,流放都匀而建。
学校前身是满清维新政府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兴建的新式学堂,都匀官立中学。
如若是做买卖,孙立人将军定是要折得底裤都没得穿。今天来两个,明天走五个。常常是报名得人,没有卷铺盖离开得人多。
很多人一听不是正规军,是隶属于宋子文孔祥熙财政部的缉私警察,便泄了气。
感觉一下子从原配,降格为妾似地,难以承受。沮丧,失落写在绝大多数人的脸上。
好多人都是千里迢迢,历经千辛万苦,风尘仆仆地赶过来的。有人觉得受了骗上了当,而泼口大骂。
骗人的人也多少有些难以为情。
做完这个工作,又做那个工作。希望大家留下来。无外乎就是说,打得虽则是稽私警察的招牌,与正规军其实无异。绝不会缩在后方不动,也是要开往前线打鬼子的。绝不至于是某某的私人部队。然而这样的承诺,连发愿的人,心里也没有底。因为当家的人,孙立人,还在武汉与孔祥熙在交涉饷粮装备事宜。
好不容易留下来的,也是心浮气躁。忧心忡忡。连写往家乡的书信,都失去了写得勇气。觉得难以启齿。做了逃兵也似地。
幽幽报国情,殷殷赤子心,是人都能理解。
负责招生的人,当然也能够理解。
只有象施耐德阮氏兄妹这样,才是铁了心留下来不走的。
因为对他而言,上不上战场,是无可无不可的事。
对于一个以前从未过过流浪生活的人来说,找一个落脚点,重新回到一种类似于家的状态,才是当下他所最最需要的。
阮静玉也多多少少让他体会了,来自家人的那种感觉。
加之这里吃穿不愁。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穿,除了星级酒店,哪里去寻这样好的招待所去?
稽私警察学校因为招不到人,无法开班授课训练。所以每天他们都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游泳钓鱼,上山采摘杨梅。东山、剑河,乃至更远些的独山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个个晒得跟泥鳅样的。夕阳余晖里,与苗族水族布依族人家的孩子在剑河里打水仗,是他们最喜欢的事。笑声叫声斥骂声充斥剑河两岸。原先是古代驿道的石板桥,无论是清晨还是黄昏,都不乏下棋与观棋的老人,一面抽着水烟,一面喝着都匀当地的毛尖。恬适中散漫的味道。让人很难想到,这是在国家生死生亡的时候。
施耐德阮静玉既非下棋之人,也非看客,也常夹杂其中。纯粹是因为热闹。
其中当然也有不和谐得。用米粉店老板的话说,扔孩子的多了。
香港陷落,马来陷落,在欧洲战场上采取绥靖政策的张伯伦政府,在遥远的东南亚,亦毫无抵抗决心,带着一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上饱食终日的老爷官老爷兵们,节节败退。作为紧邻广西的都匀,已然嗅到了不一样的气氛。
这一天他数了数三百米长不到的石板街上,一共扔了多少个孩子在街上。三十一个。
“抱一个回去可好?”他一本正经地与阮静玉商量。
“开什么玩笑!”阮静玉一蹦三尺。
“说正经得。”
“我比你更加正经。不可以。”
“我不是征求你的意见。我是问你能不能帮我带孩子。”
“帮你带孩子,凭什么?”
“因为,因为,”施耐德做了个双手托胸的动作,“因为你有这个。”
“想得美。”阮静玉一抱胸,感觉就象有人,要与她抢她胸前的那两坨包包似地。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看这些小孩子,扔在这里多可怜!没人领走的话,晚上很可能会被流浪狗或者山上下来的野狼给叼走。命就没有了。你说可怜不可怜,凄惨不凄惨,好歹也是条命啊!”
“别说了,你这么说,我心里头压力好大。”阮静玉愁容不展道。
“你看这个好漂亮。眼珠子清澈得就象黑色的珍珠一样。你能忍心让她被野狗被狼-----。”
“这么多呢,我们救一个,其他的还不是会被叼走。”
“救一个是一个,再说了,别人看我们行动,在我们的感染下,别人兴许也会下起决心,对不对?”
“你讲得不无道理。那我们收养一个吧。这么多,养哪一个呢?”下了决心以后,阮静玉突然间兴趣大涨,挨个地看,哪一个孩子精神,哪一个好看。最后两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将目光锁定在一个胎发乌黑发亮尤如黑绸缎子一般,眼睛如同黑色琉璃一般,清澈透亮,照得人心里头直发喃的小家伙身上,“就是他了,好吗?”两人异口同声道。奇怪得是,当他们决定要她时,那孩子原本哭得哼啊哼啊地,立马不哭了。居然露出了笑意。阮静玉忍不住在她的小脸上捏了又捏,“好可爱,就是他(她)了!”
“有生辰八字的,看看跟你们是否有缘。”见有人要领养孩子,而且是一对年轻人,女孩子还稚气未脱,说话一股子奶哄气,许多人都围了上来。有人就向他们提议道。
“肯定跟我们有缘了,不然,我们怎么会选中他(她)。”施耐德傻傻地乐着。就象那些在产房外面焦急等待着大人与小孩消息的父亲们,突然听到母子平安的消息,忍不住就要泪流满面的感觉。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也期待着真凭实据。孩子的生辰八字正好与他,或者与她相契合。
襁褓中的孩子放在一只新编的竹篮里。施耐德伸手在襁褓中寻找。
“轻点轻点,你这样大手大脚的,会划伤着他的。是女生唉!”施耐德找生辰八字时。她开始将孩子的腿分开,辨清性别。蓦地兴奋道。如果是男孩子,想必她也是如此兴奋的。象他一样,她并不太介意男孩还是女孩。
在婴儿的衣服兜里他发现了一张黄裱纸,纸上用墨写着些字样的东西。
只是他一个字也看不明白。
“你认得吗?”不待阮静玉伸头过来,他把黄裱纸凑她面前问。阮静玉大眼绷小眼,把头摇头拨浪鼓模样。
“这是水文。”当中有识物的,笃定道。脖子伸过来,象消防队自由伸缩的液压救生云梯一样。
“水文?水文是什么?”施耐德问道。
“就是水族的文字。”
------。
热心人特别多,然后便有人告诉他们,哪里有人懂这水文。再然后,又有人自告奋勇地说要带他们去拜访认识水文的老人。
那是一个十岁左右的水族小孩。赤着脚。精赤着身子。剑河里他和他们两个打过水仗。如今能够为他们效劳,并不因为他们曾是他的“敌人”有所折扣。屁颠屁颠地在前面引路。而他的伙伴,大都也是一丝不挂地小家伙们,嘴里喊着吆喝着围着他们是蹿来蹿去。摔倒了,顶多也就咧一咧嘴。爬起来依然接着跑。
那是一个水族男性巫师。盘着头发。给人一种男不男女不女的感觉。水族男性盘发,女性则是短发。
水族人没有神一说法,只相信世上有鬼。而巫师则是人与鬼之间沟通联系的桥梁。巫师大多也是水族当中的学者与医生。
那名巫师向他们解释了,黄裱纸上写得那些字是什么意思。
俩人一边听着一面点头,眼睛里却越来越迷茫。因为他们并不明白那些字所代表的确切意思。
水族人有水族人的历法。水族的生日当然亦按照水族历法记载。二人当然无法搞清那些字所代表的意思了。
好在巫师加以解释。他们才慢慢明白过来。
水族年历,一年的起始则起始于端午。换算成公历是一种算法,算做农历又是一等算法。而要换作民国,更是一种算法。颇费了些脑筋,巫师大人终于将孩子的生日算清楚了。放在民国,应该是民国二十一年腊月二十一日酉时。他说。
“跟我的生辰不一样。”阮静玉象是释然,又不乏失落的样子,咕哝道。
“跟我生辰也不一样。”他觉得她需要些安慰。
突然一道闪电击中了他。眼眶一热,眼泪顿时如山洪暴发一般,奔腾而下。
“怎搞得怎搞得,老大?”望着情绪突然失控的施耐德,阮静玉显得张惶不知所措。
“没什么,”施耐德抹了抹眼泪,眼泪依然以不可抵挡之势磅礴而下,“我也有了属于我自己的孩子了。一时间感觉好幸福好幸福,太不可思议了!不是吗?”因为太过突然的幸福,已经冲昏了他的头脑,说起话来,显得颠三倒四。
“是啊,”阮静玉也是一副喜不自胜的样子,“只是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努力将她抚养长大,真得是任重而道远哩。”
“我会帮你的。我们共同把她抚养长大。她将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你说,对不对?”
“对,没错,她会成为对这个国家,对这个世界都非常有用的一个人。”两人就象是在对着什么东西在宣誓一样,信誓旦旦道。特别有存在感的仪式感。
俩人都开始流泪。
只是他的眼泪还暗藏着另外一番道理。
辉姬。坂本香珠。
那个在他怀里,生命力一点一滴耗尽的美丽的日本女子,在他的心底里,已经与眼前的婴儿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因为,因为。眼前这位婴儿出生的时间,正是他此生唯一的真爱,辉姬,切腹自戕之时。
女孩很显然便是辉姬之转世。那晶亮清澈的眼眸。当他们决定要她时,那一瞬间的笑,都是辉姬在世的模样。
想到这,他那结了痂的心,趋于愈合的破碎的心,疮疤迸裂,再次四分五裂,渗出丝丝滴滴,淋灕的鲜血来。两人在江城凄寒的冰天雪地里,生死相依时,不离不弃的身影,相互起誓,来世再见的画面,一帧一帧,依然如昨。
“哥哥,我们会再见得,”她那哽咽着,低低的声音,“下辈子,我还会做你的女人。”
“是的,辉,我们真地再见了!”施耐德心里凄然呐喊。
--------。
“你们把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两人收养小孩子的事,立马风传到了学校的拐拐落落。
教员们一窝蜂般地来了七八个,包括孙立人清华同学,临时负责人,副总,齐学启。
“抗日也需要后继有人。”施耐德解释道。
当然这样的解释貌似很有道理,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
“要么把孩子扔掉,要么马上从学校滚出去?”齐学启下了最后通牒,“胡闹。简直。”
-------。
“胡闹。简直。”抱着孩子,两人学着齐学启怒不可遏的神情,开怀大笑。没有预期的被人驱赶后的不快,反倒是特别开心。仿佛已经等到了孩子长大的这一天,他们在对她诉说起当年收养她的那一天,他们为她所做出的牺牲。
在他们尚未成熟的心间,似乎已经体会到了那种为人父母才会体会到的,为儿女付出以后,才会体会到的苦并快乐着的感受。
没有痛的快乐是无聊的,噙着泪水的笑,才是真地快乐。
他们在剑河畔,如今的小吃街上,租了套带杂院的茅草房,住了下来。
孩子哭。他说,“孩他娘,该给孩子喂奶了!”
“我知道,要你讲。”
“那你还不喂她?”施耐德故作一副家主的样子。
十六岁的娘,假模假式地敞开怀,“坏蛋!”
“唔!”施耐德看着孩子将X头塞进孩子衔进嘴里,眼里荡漾着满满的爱意。
“还看还看,流氓!”
“哦!”施耐德这才吃了一惊。在他眼里,女人哺乳是神圣的,并没有想过,有什么不可以看得。直到对方抗议,才恍然大悟。忙不迭地背过身去。
“痛!”同样还是个孩子的阮静玉大叫,“小坏蛋,咬我!”
好不容易把X头从孩子嘴里夺出来。小的哭,大得也哭。比赛谁的声音大似地。
邻居里几个妇人好奇地走了过来,隔着门框,张望着问。其中一个怀里还搂个孩子一面衔着他妈妈的X头,吮吸着,一边眼珠子乌溜溜地看着他们家哭得稀里哗啦的女婴。那孩子至少已经有八九岁,依然没有断奶。
“你有奶吗?”那个奶着孩子的女人努努嘴问。
“当然!”阮静玉拍拍胸脯道。那女人的问法,让她好生奇怪。“是不是眼瞎?”她都这么怀疑。
“她是问你有没有奶水?”一个眼睛吊吊着的老年妇女与她解释道。
“好象没有。”倒底是女孩子。阮静玉看了施耐德一眼,脸腾地红了,把怀掩上。
“没有,你奶什么孩子!”妇人争相大笑起来。
“嘬嘬不就有了吗?”阮静玉不懂她们都在笑些什么。
“是啊!”施耐德也觉得那些女人无厘头。
“一对小家伙,什么都不懂,把孩子给我吧。”那个奶着孩子的妇人,把自家孩子放到地上,伸出手来,“没生过人,哪来的奶水,真是被你们给气死了!”
她们都听说了,一对小夫妻收养了个弃婴,在他们这条街什么赁了间房住着。于是结伴而来,瞅看热闹。刚好被她们看到他们出洋相。
------。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晃已是月余。在周围邻居的帮助下,孩子长大了不少。依依呀呀地开始学说讲话。真地让他们俩好不欢喜。以往离不开哥哥的家伙,这时,早已经将东山下的哥哥忘得一干二净了。全身心地投入到哺育孩子的行动当中。只是到了这天夜里。情况变了。“殿下,开门!”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夜晚的窗外传了进来。
“你们怎么不死咧!”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坂本次郎,枭园战芥三人。
“这里不是阁下呆得地方。”阴影当中另外一个人也走了出来。那特别的芜湖腔,让他立马意识到,同来的还有谁。为不打扰到孩子,他把四个人引到河边。为了孩子,他已经动了杀念。“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们。”他铁青着脸道。弦月如钩。尽管是下半夜了,空气中依然暑气未消,让人身上汗津津地,很不舒服。
“我们消失可以,您跟我们回去。”翻译不卑不亢道。
“我现在过得很好,你们无需牵挂于我。”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殿下。你不回去的话,我全家人都要死,你知道吗?”
“你全家死与不死,跟我没有关系。你没必要拿你家人的死与不死来要挟我。”
“好吧,既然如此,殿下,我们也不好意思了!”翻译一挥手,阮静玉与孩子的身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他们这一行,原来来得不止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