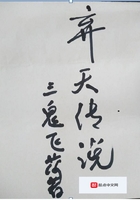夜雨纷靡。
灼文帝看着庭院,两眼出神。视线处,一朵白花,被散落的雨滴压弯了枝头。
“父亲?”身后传来的声音,透着些许担心,“果然,还是没办法睡觉吗?”
“小萨这么晚了,不也没睡吗?”灼文帝微笑回头,身后的姑娘已走上前,把大衣披在文帝身上,“……去里屋吧,这里太冷。”
“不。”文帝笑着摸摸女儿的头,“老爹还有点事……你先去睡吧。”
“嘛,算了。”萨摇了摇头,蹲在一旁,“糟老头不去睡,小姑娘就得陪。”
“没有一米七八的小姑娘吧?”
“老爹,你很烦诶!”
“嘛,不闹了不闹了。”文帝笑着摆了摆手,继续看向庭院。
先前的白花,此刻已然散落,碎满了四周。
“呵!”泉辛喘了口气,身后是灰墙,左边是刀,连同白衣的手——一把拽住,提刀,斩落!“你们就这点能耐?”他嘲讽着,俯身,翻滚,贴地扫膛,起身,刀旋刃,横劈,收回架住,弯腰,当胸一拳,“开!”他大吼一声,利刃翻飞,最后的刺客已没有机会捡回——
一声脆响,白衣包裹的躯体,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悍刀重扛在肩上,泉辛环顾四周,视线再无阻拦。“小子,你没事吧?”他转过头,看向护在身后的谨宣。谨宣一脸茫然无措,“他……他们是谁?”
“……坏人。”泉辛撇了撇嘴,蹲下身来,拽住一个刺客的衣领,“喂,谁派你来的?”
“……”刺客丝毫反应也没有,任凭泉辛摇晃。
“嘛,虽然我知道你不会说,但还是要例行公事一下。”泉辛松开手,站起身,“回去告诉你主子,泉辛大老爷叫他上点更好的货色。你们啊,”泉辛咂了咂嘴,“欠练。”说完,他把刀收回鞘中,然后转身,冲向谨宣,双手抱住,一跃而起——
咔!!
墙体出现裂纹。砖土的残屑,在半空中飞散。“……讲究人,呵!”泉辛重新落地,松开已经吓呆的谨宣,起身,重新拔出悍刀。不远处,一个人影缓慢浮现,清晰。
一片漆黑的巷子里,一水儿的白衣,就那么肆无忌惮地站在那,应该会很显眼吧。可这个男人却毫无这种感觉。他站在那里,缓缓抽出腰间的短恪刀,两眼死死盯着泉辛。“啧……说是那么说,但也不用这么快吧喂……”泉辛吐了口唾沫,微微躬身。
呼——
——铿!!下一秒,面对面,四目相对,气浪排空。“好身手。”泉辛赞叹一句,悍刀回身,再斩!
咚!!刀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白衣男子堪堪闪过,随后踏地而起,跃身,浮空,三枚刃镖飞出,紧接着便直冲而下,泉辛急忙弹开刃镖,左手伸向面前,“破!”气弹轰出,白衣一刀砍碎,格开悍刀,借力起跳,落地翻滚,转身,直冲向角落的谨宣——
“砰!”猝不及防,白衣男被一面长盾挡飞。“……深更半夜在这里胡闹。”透明的金色长盾后,是一位穿着棕褐色长袍的金发男子,他回头看向谨宣,“……站在我身后。”此时,白衣男已然翻身而起,右手持刃,左手悬镖,视线在泉辛和陌生男子之间不停挪移。最终,他还是缓缓后退,伴随着月光,慢慢消失在空气之中。
“呵。”男子拍了拍袍子,长盾随之破碎,消失。“谢谢你。”身后的谨宣说。“不客气。”男子刚想发问,却马上被泉辛打断,“喂——你怎么在这儿?”泉辛把刀插回鞘中,快步走向两人。
“这很奇怪吗?”男子皱了皱眉头,问。
“到这儿传教,你也是溜。”泉辛拍了拍男子的肩。“那,现在能回答我吗?你们这么晚还在外面的原因?”男子问。
“咳。”泉辛轻轻咳嗽一声,“所以,你这么晚还在外面又是要干什么呢,通缉犯普希托尔先生?”
“你似乎没资格用这个来嘲讽我,任泉辛。”普希托尔无奈地摇了摇头。“到处都在抓我,再呆下去只会给这儿的弟兄添麻烦。我现在准备离开天守城——你们应该也是要走的吧?——要跟我一起吗?”
“那个……”谨宣突然说,“我现在还是不太明白,老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生总是充满未知与迷茫的,小子。”泉辛的脸上写满了深沉。
“……这位弟兄,以后再听你老师慢慢解释也不迟,现在的当务之急,”普希托尔看向泉辛,“这就走吧,迟则生变。”
“看这情形,也确实不能在这儿久留。对了。”泉辛指着那些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刺客,“你知道这些人什么来历吗?”
普希瞥了一眼,“不知道。”他缓缓蹲下,“你带相机了吗?”
“我怎么可能带那种东西……”泉辛耸了耸肩。“那个……我这里有,原本打算拍拍风景什么的……”谨宣边说边从背包里掏出相机,递给普希,“你帮大忙了,弟兄。”普希说着,对面前的一个刺客拍了几张,“会有认识的人的。”他说着,站起身,还给谨宣。泉辛拍了拍手,“好了,我估计再过一会儿,他们就醒了——我可不想重来一遍。”
“那,这就出发吧。”普希说。
……
“……所以说,你失败了,近井?”文帝看着窗外,缓缓地问。
“……是我的失误。”被唤作近井的白衣男子说。
“……算了。”文帝整了整身后的大衣,“十八年,我都等了这么久,也不差这一会儿了。”他转过身,“你可从没让我失望过,近井。”
近井默然。文帝叹了口气,朝殿门走去,“先挑几个好手吧,盯住他们。”
“我绝不会一直失败。”近井低沉地说。
“但愿如此。”文帝说着,走出殿外。
雨,终于停了。
只是……月亮,依然被乌云遮挡,黯淡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