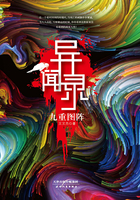“我马上就拿来。但是他没有拒绝;相反,斯齐发还存着希望。”道丽在门口停着说。
“我不存希望,我也不想要那样。”安娜说。
“这是什么意思?吉蒂认为和我会面是降低身份吗?”剩下了一个人的时候,安娜想着,“也许,她是对的。即使这是真的,但是她,爱过佛隆斯基的人,她不该向我这样表示。我知道,我在我这种地位上,不会被任何正派的女人接待的。我知道,从最初的一分钟起我就为他牺牲了一切!这就是我的酬报!啊,我多么恨他!为什么我到这里来呢?这对我更加不好,更加痛苦。”她听见了另一个房间里两姐妹交谈的声音。“我现在要向道丽说什么呢?让吉蒂乐意看到我不幸,我受她的颜色吗?不,连道丽也不会明白的。我用不着向她说。单是看看吉蒂,向她表示,我看不起一切的人和一切的东西,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那倒是有趣的。”
道丽带着信进来了。安娜看过,无言地递回。
“这一切我都知道了,”她说,“这个我一点也不关心。”
“可是为什么呢?相反,我还存着希望。”道丽好奇地望着安娜说。她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在这么异常的暴躁的心情中。“你什么时候走呢?”她问。
安娜眯着眼望着自己前面,没有回答她。
“为什么吉蒂要躲避我?”她望着门红着脸说。
“啊,瞎说!她在喂奶,她的事情不如意,我在劝她……她很高兴会面的。她马上就来,”不会说谎的道丽不自如地说,“呵,她来了。”
听说安娜来了,吉蒂本不愿出来;但是道丽劝了她。鼓起了勇气,吉蒂走进来,红着脸走到她面前,伸手去握。
“我很高兴看到您。”她用发抖的声音说。
吉蒂因为她心里面所发生的对这个坏女人的敌意和对她宽容的愿望两者间的冲突而感到狼狈;但是她一看见了安娜的美丽的动人的脸,所有的敌意就马上消失了。
“假若您不愿意和我会面,我也不会惊讶的。我对一切都弄惯了。您害过病吗?是的,您变了。”安娜说。
吉蒂觉得安娜带着敌意地望她。她认为这种敌意是由于从前对她宽容的安娜现在在她面前所感到的难处的地位,于是她同情安娜了。
她们谈到吉蒂的病,谈到婴儿,谈到斯齐发,但是显然,都不使安娜发生兴趣。
“我来向你辞行的。”她站起身说。
“你们什么时候走?”
但是安娜又没有回答,转向着吉蒂。
“是的,我很高兴看见了您,”她带着笑容说,“我从各方面听到许多关于您的话,甚至从您丈夫那里听到。他来看过我,他很使我满意,”她显然带着恶意添说,“他在哪里?”
“他下乡去了。”吉蒂红着脸说。
“替我向他致意,务必替我致意。”
“一定的!”吉蒂单纯地说,同情地望着她的眼睛。
“那么,再会了,道丽!”于是吻了道丽,和吉蒂握了手,安娜连忙走出。
“她依然如旧,还是那么动人。很好看!”剩下吉蒂一个人和姐姐在一起时,她说,“但是她有点可怜的地方。非常可怜的!”
“呵,今天她有点异常的地方,”道丽说,“当我送她到外厅的时候,我仿佛觉得她要哭了。”
二十九
安娜坐上车子,心情比她从家里出门时更恶劣。在原先的痛苦之外,又添了她和吉蒂会面时所明明感到的侮辱与见弃的情绪。
“哪里去呢?回家吗?”彼得问。
“是的,回家。”她说,现在并未想到她到哪里去。
“他们怎么看我好像是看什么可怕的、不可解的、奇怪的东西!他能够那么热烈地向另一个人说些什么呢?”她望着两个步行的人,这样想道,“人可以向别人说出他所感觉的情绪吗?我本想要向道丽说,幸而我没有说。她会多么高兴我的不幸啊!她会隐藏这个的;但是主要的情绪是她高兴我为了她所羡慕的那些快乐而受罚。吉蒂,她会更加高兴的。我把她完全看透了!她知道,我在她丈夫看来是超乎寻常地可爱的。她嫉妒我,怨恨我,还轻视我。在她的眼睛里我是不道德的女人。假若我是不道德的女人,我就可以使她的丈夫爱我了……如果我想要的话。我是真想要这样。这个人满意他自己。”她想到一个肥胖的红润的迎面走来的绅士,他把她当作熟人,在光亮的秃头上脱了脱光亮的帽子,然后又知道他认错人了。“他以为他认识我。但他是和世界上任何认识我的人同样地不认识我。我自己也不认识自己。我知道我的胃口,像法国人所说的,他们想要吃那肮脏的冰淇淋。这个他们一定知道,”望着两个站在卖冰淇淋的人旁边的孩子,她想,卖冰淇淋的人从头上拿下了桶,用巾端拭着汗脸。“我们都想吃甜的美味的东西。没有糖果,就吃肮脏的冰淇淋。吉蒂也是这样:没有佛隆斯基,就要列文。她羡慕我,还恨我。我们互相怨恨。我恨吉蒂,吉蒂恨我。这是真的。邱特肯,coiffeur(理发师)。Je me fair coiffer par Tyutkin(我的发是给邱特肯理的)……他来的时候,我要向他说这个。”她想着,微笑着。但是同时她想起来了,她现在没有人听她说可笑的话了。“可笑的东西是没有的,有趣的东西是没有的。一切都是可憎的。在敲晚祷的钟了,那个商人画十字多么正确!好像怕失掉什么东西似的。为什么要有这些教堂,这个钟声,这个谎话呢?只是为了掩饰我们像这些互相怒骂的车夫一般的互相憎恨。雅施文说:他要使我衬衣也不剩,我也要使他衬衣也不剩。这是真的!”
她在这些思想中一直到了自家门口,它们那么吸引她的注意,她不再想到自己的处境了。她看见了出外迎接她的门丁,她才想起了字条和电报。
“有回信么?”她问。
“我来看看。”门丁回答,望了望桌子,拿了方形的薄纸的电报封套递给她。
“十时前我不得回来。佛隆斯基。”她看着。
“送信的人没有回来吗?”
“还没有。”门丁回答。
“呵,假若这样,我就知道,我要怎么办了。”她说,并且,感觉着心里起了不明确的怒火和报复的愿望,她跑上了楼。“我要自己去找他。在我永远地离开之前,我要向他说一切。我从来没有恨过任何人像恨这个人那样的!”她想。她看见了衣架上的帽子,她憎恶得发抖。她没有考虑他的电报是回答她的电报,他还没有接到她的字条。她向自己假想着,他现在正在安闲地和母亲和索罗基娜公爵小姐在谈话,并且乐意她的痛苦。“是的,我必须立刻就去。”她向自己说,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她想要赶快离开她在这个可怕的屋子里所感到的那些情绪。仆人,墙壁,这个屋子里的东西——一切都引起她心中的憎恶与恨怒,并且给她某种压迫。
“是的,我一定要到火车站去,假若他不在那里,我就到那里去当场抓他。”安娜在报纸上看了看火车时刻表,晚上八点零二分有一班车开出。“是的,我来得及。”她吩咐了套别的马,忙着在旅行袋里装放几天之内所必需的东西。她知道她不再回到这里来了。在来到她头脑里的许多计划之中,她茫然地决定了,要是在火车站上或者在伯爵夫人的田庄上发生了那件事情以后,她便搭下城线的火车到第一个城市,在那里停下来。
饭摆在桌上;她走到桌前,闻到面包与干酪的气味,认为一切食物的气味都是讨厌的,便吩咐预备马车,出了门。房屋的影子已经投到街道的对面,那是明亮的,在阳光中还是暖和的傍晚。拿东西送她出来的安奴施卡,把东西放上马车的彼得,还有那个显然是不满意的车夫——都使她觉得讨厌,他们都拿言语和动作激怒了她。
“我不需要你,彼得。”
“车票怎办呢?”“哦,随你的便吧,我觉得无所谓。”她恼怒地说。彼得跳上了驾驶台,手叉着腰,吩咐了赶到车站去。
三十
“又是那个姑娘!我又明白了一切。”车子刚开驶并且颠动着,在马路的砾石上辗响着,安娜就向自己这么说,于是她心中的印象接连地变换着。
“是的,我清清楚楚地想到的最后的东西是什么?”她努力回想着。“邱特肯,coiffeur(理发师)吗?不,不是这个。对了,想到雅施文所说的话:生存竞争和憎恨——是把人结合在一起的唯一的东西。不,你们去是徒劳啊。”她在心里向四匹马的轿车里的一行人说,他们显然是到城外去寻乐的。“你们带的狗不会帮助你们的。你们不能够逃避你们自己。”她把目光朝向彼得所看的方向,她看见一个醉得半死的工厂工人,带着摇摆的头,被警察带走。“呵,他有了更快的方法,”她想,“佛隆斯基伯爵和我也没有找到这种满足,虽然我们很期望。”安娜现在第一次用她看一切东西时的那种清楚的看法来看她和他的关系,这是她从前所避免想到的。“他在我身上所寻求的是什么?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虚荣的满足。”她想起了在他们的关系的初期中他的话,他的使人想到驯顺的猎犬的那种面部表情。现在一切都证实了这个。“是的,他有了虚荣满足的胜利。当然也有爱情,但大部分是对于成功的骄傲。他拿我去夸耀他自己。现在这已经过去了。没有骄傲的地方了。不是骄傲,却是羞耻。他已经从我身上拿去了他能够拿去的一切,现在他不需要我了。他讨厌我了,他努力不要对我做一个不名誉的人。他昨天说了——他希望我离婚和他结婚,表示他破釜沉舟的决心。他爱我——但是怎样了?The zest is gone(趣味没有了)。那个人想使大家都对他惊异,他很满意自己。”她望着一个红润的骑着租用的马的店员,这么想道,“是的,我对于他已经没有那种趣味了。假若我离开他,他要在心里边高兴的。”
这不是假设——她在那穿透的亮光中清晰地看见了这个,那亮光现在向她展示了人生的意义和人类关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