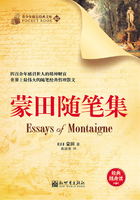“我们一道到他们家去是多么好啊!你什么时候去呢?”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问发生卡。
“我要在他们家里过七月。”
“你也去吗?”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向他妻子说。
“我早就想要去了,我一定去,”道丽说,“我替她可惜,我知道她。她是极好的女子。我要在你走了的时候一个人去,这样就什么人也不妨碍了。甚至没有你还好些。”
“好极了,”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说,“你呢,吉蒂?”
“我?为什么我要去?”吉蒂满脸通红地说。她回头望了她丈夫。
“您认识安娜·阿尔卡即耶芙娜吗?”维斯洛夫斯基问她,“她是很动人的女子。”
“是的。”她更加脸红地回答了维斯洛夫斯基,站起来走到丈夫面前。
“那么你明天去打猎吗?”她说。
他的嫉妒在这几分钟里已经很深了,特别是因为在她和维斯洛夫斯基说话时散布在她腮上的赤红。此刻,听着她的话,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了解它们。虽然他日后想起这个觉得奇怪,此刻他却似乎明明地觉得,她问他去不去打猎,她关心这事,只是因为要知道他会不会给发生卡·维斯洛夫斯基这种乐趣,而照他的意思,吉蒂已经爱上了他。
“是的,我要去。”他用不自然的自己也觉得讨厌的声音回答她。
“不,还是过了明天好些,不然,道丽就完全不能够跟她丈夫会谈了,后天去吧。”吉蒂说。
吉蒂的话意此刻却被列文解释成这样的:“不要使我和他分离吧,你去不去——对我都是一样,但是让我享受这个优美的年轻人的交谊吧。”
“呵,假若你愿意,我们明天就不走了。”列文特别和气地回答。
这时,发生卡一点也不怀疑到他的在场所引起的这种痛苦,随着吉蒂从桌前站起来,用笑意的亲切的目光注视着她,跟着她走。
列文看见了这个目光。他脸色发白,有一会儿不能够呼吸。“他怎么敢这样地望我的妻子。”这念头在他心里沸腾着。
“那么,明天吗?请同我们去吧。”发生卡说,坐到椅子上,又习惯地盘着一只腿。
列文的嫉妒更加厉害了。他已经把自己看作被欺骗的丈夫,妻子和她的情人需要他,只是为了供给他们的生活便利与满足……但,尽管是这样,他却有礼貌地好客地向发生卡问到他的打猎、枪、靴子,并且同意了明天去打猎。
对列文侥幸的是,老公爵夫人自己站起来劝吉蒂去睡觉,借此打断了他的痛苦。但是甚至在这时候,要列文没有新的痛苦也是不行的。发生卡和女主人道再会时,又想要吻她的手,但是吉蒂红了脸,缩回了手,带着后来她母亲因而责备她的那种单纯的粗鲁行动,说道:“我们不作行这样。”
在列文的眼睛里这要怪她,是她容许这种关系的,尤其要怪她的是她这样笨拙地表示了她不喜欢这样。
“哦,怎么会想睡觉!”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说,他在吃晚饭时所喝的几杯酒之后,有了最可爱的诗意的心情。“看啊,吉蒂,”他指着从菩提树后边升起的月亮说,“多么优美!维斯洛夫斯基,这正是唱良夜曲的时候。你知道,他有不寻常的声音,我和他在路上一起唱歌的。他带来一些极好的短歌,有两首新的。和发尔发拉·安德来芙娜一起唱吧。”
当大家已经分散时,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还和维斯洛夫斯基在大道上走动了好久,可以听到他们的在唱新歌的声音。
列文听着这些声音,皱着眉坐在妻子卧室里的靠臂椅上,对于她问到他有了什么事情的话顽固地沉默着。但是在最后她自己畏怯地微笑着问道:“是不是维斯洛夫斯基有什么地方叫你不高兴?”这时候,他爆发了,说出了一切;他所说出的话使他痛心,因此更使他激怒了。
他带着在颦蹙的眉毛下可怕地闪耀着的眼睛,站在她面前,把强有力的手臂压在胸脯上,好像是用着全部的精力来抑制自己。他脸上的表情假若不是同时显出使她感动的痛苦,便显得是严峻的甚至是残酷的了。他的下颚颤抖着,声音频断着。
“你要明白我不是嫉妒:这是一个可恶的字眼。我不能够嫉妒,并且相信……我不能够说出我所感觉到的,但这是可怕的……我不是嫉妒,但是使我痛心和屈辱的,是任何人都敢想到,敢用那样的眼睛望你……”
“什么样的眼睛?”吉蒂说,她尽量公正地去回想那天晚上的一切言语与姿势以及它们的一切含意。
她在心坎里觉得,正在维斯洛夫斯基跟她绕到桌子另一端的那一片刻,有了什么事情,但是她简直不敢向自己承认这个,尤其不敢向他说这话,更怕因此增加他的痛苦。
“我这个样子,有什么地方可以动人呢?”
“呵,”他抓着头叫着,“你不该这么说!……意思是,假若你那时候是动人的……”
“噢不,考斯洽,等一等,听我说!”她带着痛苦而同情的表情望着他说,“哦,你会想到什么呢?这时候我心里没有别的人了,没有人,没有人了!……你是要我永远不看见任何人吗?”
在最初的片刻,她讨厌他的嫉妒;她恼怒的是连最微小和最无辜的欢娱也要禁止她;但是此刻为了他的心安,她乐意地不但牺牲这些无谓的东西,还要牺牲一切,好使他免除他所受的痛苦。
“你要明白我的地位的可怕和可笑,”他用绝望的低声继续说着,“他是在我家里,除了放肆和盘腿,他也没有做出什么特别不得体的事。他以为这是最好的态度,因此我不得不对他客气。”
“但是,考斯洽,你说得过分了。”吉蒂说,在她心坎里却高兴着此刻表现在他嫉妒中的对她的爱力。
“最可怕的是,你总是你那个样子,而现在,你对于我是那样的圣物,我们是那么幸福,那么特殊的幸福,这时候,忽然那个坏东西……不是坏东西,为什么我要骂他呢?我与他无关。但是为什么我和你的幸福……”
“你知道,我明白这是因为什么发生的。”吉蒂开始说。
“因为什么?因为什么?”
“我看到当我们在晚饭桌子谈话的时候,你怎样地望我们。”
“哦,对了,哦对了!”列文惊惶地说。
她向他说了他们谈到什么。并且说这话时,她兴奋得喘不过气来。列文沉默着,后来望了望她的发白的惊慌的脸,突然地抓头。
“卡洽,我苦恼你了!亲爱的,原谅我吧!这是发疯!卡洽,这完全怪我。我怎么能够为这样的愚蠢的事受苦呢?”
“不,我替你难过。”
“替我?替我?我怎样了?发疯了!……为什么要叫你受苦呢?要想到任何生人会破坏我们的幸福,是可怕的。”
“当然这是痛心的……”
“哦,相反,我要特地整个夏天把他留在我们家里,我要尽量对他客气。”列文说,吻着她的手,“你看吧,明天……哦,对了,明天我们要去打猎。”
八
第二天太太们还没有起床,出猎的马车、快车和荷车已经停在门口了,从清早就明白他们要去打猎的拉斯卡,嘶叫蹦跳够了,就坐在快车上车夫的旁边,兴奋地因为迟延而不满地望着门,猎人们还没有从门里走出来。第一个出来的是发生卡·维斯洛夫斯基,他穿了齐到肥胖大腿当中的长筒新皮靴,绿色外衣,系着芳香的新皮的弹药带,戴着有缎带的小帽子,带了一支没有背带的崭新的英国枪。拉斯卡跳到他面前,欢迎他,跳起来,用它自己的方式问他,他们是不是快要出来了,但是没有得到他的回答,便回到了它的等待的地方,歪着头,竖起一只耳朵,又安静了。门终于带着辗轧声打开了,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的黄斑的指向狗克拉克飞奔出来,兜圈子跑着,望着天空,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自己也手拿着枪、口衔雪茄走了出来。“不动,不动,克拉克!”他亲善地向狗叫着,狗正举起爪子搔他的肚子和胸脯并且碰着猎袋。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穿了覆鞋套,打着绑腿,穿着破裤子和短外套。头上是一顶不成样子的破帽子,但是新式的枪是玲珑巧小的,而猎袋和弹药带虽然破旧却是最上品的。
发生卡·维斯洛夫斯基以前不明白这种真正的猎人的特色——是穿得破旧,却有最上品的猎具。望着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在破旧的衣服里闪耀着优美的、肥胖的、快乐的贵族姿态,他此刻明白了这个,并且决定了下次打猎的时候他一定要这样打扮。
“哦,我们的主人怎么样了?”他问。
“年轻的妻子。”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微笑地说。
“是的,并且是那样艳美。”
“他已经穿好了。一定是又跑到她那里去了。”
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猜对了。列文又跑到妻子那里,又向她问了一次,她是否饶恕他昨晚的愚行,并且又请求她,为了基督的缘故,她要更加小心。最重要的是和小孩们离远一点——他们随时会撞她的。然后又必须再听一次她的保证,说她不为了他离开两天而对他生气,他又要求她明天早晨一定派人骑马送个字条给他,即使是只写两个字,只要他能够知道她是安然无事就行了。
吉蒂和寻常一样,为了和丈夫离别两天觉得难受;但是看见了他的生气蓬勃的身材,在猎靴和白外衣里显得特别魁梧和强健,和她所不了解的一种猎人兴奋的光彩,她为了他的快乐而忘记自己的烦恼,快活地和他告别了。
“对不起,诸位先生!”他跑到台阶上说,“午饭放上车了吗?为什么栗色马在右边?哦,都是一样。拉斯卡,下去,去躺下来!”
“放进阉牛群里去,”他向那个带着关于阉牛的问题在台阶上等候他的牧牛人说,“对不起,又有一个家伙来了。”
列文从他已经坐上的快车里跳下来,去会那个拿着沙绳尺向台阶走来的包工木匠。
“昨天不到账房里来,现在您要耽搁我了。哦,什么事情?”
“请吩咐再做一个弯角吧。一共加三级。我们要同时把它配好。这要稳得多。”
“你该听我说,”列文恼怒地回答,“我说过的上了横木,然后装梯级。现在你不用修改了,照我说的做吧——做新的。”
问题是在这里,包工木匠做坏了正在建造的厢房里的楼梯,没有算好距离就单独装配了楼梯,因此在安置楼梯时,梯级都变成了歪斜的。现在包工木匠想要留下这个梯子,再添上三级。
“这要好得多。”
“但是你的梯子加上三级要通到什么地方呢?”
“啊哟,老爷,”木匠带着轻蔑的笑容说,“通到原来的地方。就是说,加在下边,”他带着劝服的姿势说,“通下来,通下来,通到那地点。”
“三级要把梯子加长了……它通到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从下面通上来,通上去。”包工木匠固执地劝服地说。
“要通到天棚和墙壁了。”
“啊哟!从下面通上来。通上来,通上来刚刚够长。”
列文拿了枪杵开始在尘土上向他画梯子。
“哦,你明白吗?”
“照您的意思,”木匠突然闪亮了眼睛说,显然是终于明白了道理,“似乎,做个新的就行了。”
“好了,那么,就照我吩咐了去做吧!”列文坐上快车时大声说,“走吧!抓住狗啊,非力卜!”
把家庭和田事的一切挂念都丢在身后,列文此刻感觉到那么强烈的人生快乐与希望的情绪,以致他不想说话了。此外,他还感觉到任何猎人在接近猎场时,所感觉到的那种集中的兴奋心情。假若这时候有什么事使他关心,那也只是这样的疑问:他们会不会在考尔平斯基沼地里找到什么,拉斯卡和克拉克比较起来会显得怎么样,以及他自己今天会不会射击得好。怎样才能不使他在生人面前丢丑呢?怎样才能使奥不郎斯基不比他猎获更多呢?这也来到了他的心头。
奥不郎斯基感觉到同样的心情,也不言不语。只有发生卡·维斯洛夫斯基不停地愉快地讲着。此刻听着他讲,列文想起他昨天对他是多么不公道,觉得难为情了。发生卡是确实出色的人,简单,温良,并且很快活。假若列文在未婚时遇见了他,他便会和他要好了。列文有些讨厌他对于生活的悠闲的态度和自命风雅。好像是他认为自己有崇高的无疑的重要性,因为他有长指甲、小帽子和其他相称的东西;但是为了他的好心肠和教养,这是可以原谅的。他由于他的好教养,法语和英语的优美的发音,由于他是他的同一社会里的人而使列文对他满意。
发生卡极其欢喜左边的那匹顿河草原的挽马。他老是赞美它。
“骑着草原的马在草原上飞驰是多痛快啊。啊?对不对?”他说。
他自己想象着骑草原的马乃是一种野蛮的诗意的事情,而结果却不是这样的;然而他的单纯,特别是连同他的美丽,他的可爱的笑容与优雅的举止,是很动人的。或者是因为他的性情投合列文,或者是因为列文为了偿赎昨天的罪而努力寻找他的长处,列文高兴和他在一起。
走了三俚,维斯洛夫斯基突然摸他的雪茄和皮夹,不知道是遗失了它们还是丢在桌上。皮夹里有三百七十卢布,因此不查明了是不行的。
“您知道吗,列文,我要骑这匹顿河的挽马驰回家,这妙极了。啊?”他说,已经准备下车了。
“不,为什么呢?”列文回答,他估量发生卡的体重不会少于六甫得(一甫得约合十六点四公斤),“我派车夫去。”
车夫骑着副挽马回去了,列文自己开始驾驶着双马。
九
“哦,我们的路线怎么样?统统说出来吧,”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说。
“计划是这样的:此刻我们到格佛斯交夫去。在格佛斯交夫这边有个鹑鸡的沼地,在格佛斯交夫那边有异常好的山鹬的沼地,那里也有鹑鸡。现在天气热,我们要走二十俚,傍晚可以到,打晚猎;过了夜,明天到大沼地去。”
“路上有没有什么?”
“有的,但是那要耽搁我们了,并且天气热。有两处小地方,但未必有东西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