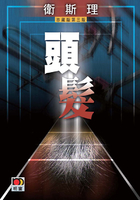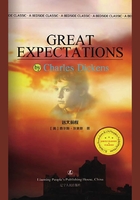“不。您看看他,”老人说,用镶边的帽子指着和参议院里一个有势力的议员站在大厅门口的穿着朝服在肩上挂着新红绶的卡列宁,“又幸福又满意,好像一个铜钱。”他添说,停下来和一个体格健强的美丽的侍从握手。
“不,他显得老了。”侍从说。
“因为工作忙。他近来总是起草计划。他近来不到,他把一切都逐条地说明了,他是不会放走那个可怜虫的。”
“显得老了吗?Il fait des passions(他在谈恋爱啊)。我想,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现在要嫉妒他的妻子了。”
“哦,什么!请您不要说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的坏话了吧。”
“她爱上了卡列宁,这难道是坏吗?”
“可是卡列尼娜果真是在这里吗?”
“并不是在这里,在宫廷里,而是在彼得堡。我昨天碰见她和阿列克塞·佛隆斯基在穆尔斯基街上bras dessus,bras dessous(臂连着臂)。”
“C’est un homme qui n’a pas……(这个人没有……)”侍从正开始说,但是停止了,向一位走过的皇族让着路,鞠躬着。
大家就是这样不停地说到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责难他,嘲笑他,而同时,他拦着被他抓住的参议院议员的路,向他一点一点地说明他的财政计划,片刻也不间断他的谈话,以免放走了他。
几乎是在妻子离开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的同一个时候,他遭遇了那件对于做官的人是最不幸的事——升官的活动停止了。这个停止是成就了,大家都清楚地看到这个,但是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自己还不觉得他的前程已经完结了。无论是由于他和斯特来莫夫的冲突,抑或是由于他和他妻子的不幸,或者只是由于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达到了他的注定的限度,但是在今年大家都明白了他的官场的前途是完结了。他还是占据重要的官位,他是许多董事会和委员会的委员;但他是一个一切都已过去的人,大家对他无所期望了。无论他说什么,提出什么,大家都那样地听着他说,好像是他所提出的意见是早已周知而且正是不必要的。
但是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没有觉得这个,并且相反,被摒弃了直接参与行政的活动,他现在比从前更清楚地看见了别人的活动中的缺点与错误,并且认为指出改正它们的方法是他的本分。在他和妻子分离不久之后,他便开始起草他的关于新式诉讼程序的意见书,这是注定了要他写的关于政府各部门的一串无数的毫不必要的意见书的第一种。
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不但没有注意到他在宦场中的无望的处境,不但不为这个苦恼,而且比以前更加满意自己的活动了。
“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使徒保罗说的(见《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译文借用《新约》译文。——译者),而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现在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受《圣经》的指导,常常想起这段文字。他似乎觉得,自从他没有了妻子以来,他就是用这些计划比以前更多地侍奉上帝。
那个想要离开他的参议院议员的显明的不耐烦,并没有妨碍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直到那个议员趁一位皇族走过的机会从他身边溜走时,他才停止了陈述。
剩下了一个人,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垂着头,聚神思索着,然后不经心地四顾了一下,向门口走去,他希望在那里遇到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
“他们身体都是多么强壮而健康啊。”望着有梳顺的芳香的颊须的强健的侍从,望着公爵的被制服扣紧着的红颈子,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想;他必须从他们身边走过。“说得真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罪恶。”他想,又向侍从的腿腓斜瞥了一眼。
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从容不迫地拔动着两腿,带着往常的疲惫与尊严的神色,向谈论过他的绅士们鞠躬,并望着门口,用眼睛搜寻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
“呵!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那个矮小的老人,在卡列宁和他平齐并用冷淡的姿势点头的时候,恶意地闪动眼睛说,“我还没有贺您。”他指着他的新得的勋绶说。
“谢谢您,”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回答,“今天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啊。”他添说,照他的习惯特别强调“美好的”这字眼。
他们笑他,这个他知道,但是他除了敌意并不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他已经惯于这个了。
看见了走进门的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的凸出胸衣的黄肩膀,和她的向他召唤的美丽的思虑的眼睛,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微笑了,露出齐整的白牙齿,走到她面前。
莉济亚·伊发诺芙娜的服装费了她很大的心思,像近来她的一切的服装那样。现在她的服装的目的是和三十年前她所追求的目的完全相反。那时候她想要用什么东西装饰自己,愈装饰愈好。现在,相反,她必定要装饰得和她的年纪与姿态那么不相称,以致她只挂念着这些装饰和她外貌的对照不要太可怕。就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而论,她达到这个目的了,并且在他看来她是媚人的。对于他,她是在环绕他的敌意与讥诮之海中唯一的不但是好意的而且是爱情的岛。
穿过嘲笑的目光的行列,他自自然然地向她的多情的目光挨近,好像植物向着阳光一样。
“我恭喜您。”她向他说,眼望着他的勋绶。
压制着满意的笑容,他耸了耸肩闭起眼睛,好像是说,这不会令他高兴的。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很明白这是他的一件主要的乐事,不过他决不承认这个。
“我们的天使怎样了?”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意指着塞饶沙说。
“我不能说我对他十分满意,”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抬起着眉毛睁开着眼睛说,“谢特尼考夫也不满意他(谢特尼考夫是担任塞饶沙的世俗教育(是与宗教教育相对而言。——译者)的教师)。我向您说过,他对于那些应该感动每个大人、每个小孩的重要问题都有一些冷淡……”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开始陈述他对于那在官职以外唯一使他发生兴趣的问题——他儿子的教育——的意见。
当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借莉济亚·伊发诺芙娜的帮助,重新回到他的生活与事业上时,他觉得过问留在他手里的儿子的教育是他的义务。以前从没有注意过教育问题,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现在花了些时间,在这个问题的理论的研究上。读过了几册人类学、教育学、教学法的书籍,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拟了一个教育计划,并且请了一个最好的彼得堡的教师来监督,他就开始工作了。这个工作不断地吸取他的注意。
“是的,但是他的心哦!我看到他有他父亲的心,小孩子有这样的心是不会坏的。”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热情地说。
“是的,也许……至于我,我尽我的责任。这是我能做的一切。”
“您到我那里去吧,”沉默了一会,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说,“我们要谈一件对您是悲痛的事情。我愿牺牲一切来使您避免一些回忆,但是别人不这么想。我接到了她写来的信。她在这里,在彼得堡。”
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听到提起他的妻子就发抖了,但是立刻他脸上显出了那种表示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办法的死一般的僵硬。
“我料到了这个。”他说。
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欣喜地望着他,对于他灵魂的伟大而有的倾慕之泪涌上了她的眼睛。
二十五
当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走进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的摆设古瓷、悬挂画像的舒适的小房间时,女主人自己还没有来。她在换衣裳。
圆桌上铺了桌布,摆着中国茶具和烧酒精的银茶壶。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漫不经心地望了望无数的熟悉的装饰房间的画像,就在桌旁坐下,打开摆在桌上的《福音书》,伯爵夫人的绸衣裳的窸窣声引去了他的注意。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安静地坐一坐了,”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说,带着兴奋的笑容连忙地挤进桌子和沙发的当中,“我们在吃茶的时候谈谈吧。”
说了几句准备的话之后,莉济亚·伊发诺芙娜困难地呼吸着,脸红着,把她所接到的信递进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的手里。
看过了信,他沉默很久。
“我并不认为我有权利拒绝她。”他抬起眼睛畏怯地说。
“我的好友!您从来看不见人的邪恶!”
“我,相反,看见一切都是邪恶。但这是公平的吗?……”
他的脸色显出了犹豫不决和要为了他所不了解的事情寻找意见声援与指导。
“不,”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打断他,“凡事都有限度。我明白不道德,”她完全不是由衷地说,因为她从来不能够明白那把妇女引向不道德的东西,“但是我不明白残忍……对谁的呢?对您的!她怎能够停留在您所在的城里呢?啊,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也在学着明白您的高尚和她的卑鄙了。”
“谁能够指摘人呢?”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说,显然是满意他所演的角色,“我饶恕了一切,所以我不能够剥夺她的爱——她对儿子的爱——向她所要求的东西……”
“但是那是爱吗,我的好友?这是诚意的吗?我们假设您已经饶恕了,您还在饶恕……但是我们有权利去影响这个天使的心灵吗?他以为她死了。他为她祷告,求上帝饶恕她的罪恶……这样倒好些。可是现在他会想什么呢?”
“我没有想到这个。”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显然同意着说。
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双手蒙着脸,沉默着。她在祷告。
“假使您征求我的意见,”祷告之后,她放开了脸说,“我就劝你不这么做。难道我不晓得您是多么痛苦,这是怎样地撕裂了您的伤痕吗?但是,假设,您像平常一样,忘记了您自己。但是这会引起什么呢?引起您这方面新的痛苦,引起小孩的痛苦。假若她还有一点人性,她自己就不应该希望这个。不,我毫不踌蹰地劝您不允许,并且,假若您允许我,我便写信给她。”
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同意了,于是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写了如下的法文信:
“亲爱的夫人。
关于您的回忆或许在您儿子方面引起一些问题,若不在小孩的心中,灌输了一种对于那在他看来应该是神圣的东西的责难的精神,就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因此我请求您用基督教徒的爱的精神来理解您丈夫的拒绝。我请求至上的主对您慈悲。莉济亚伯爵夫人。”
这封信达到了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对她自己所隐瞒着的那个秘密的目的。这信伤透了安娜的心。
在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的方面,他从莉济亚·伊发诺芙娜那里回家后,便整天不能够专心于他的通常的事务,不能够找到他原先所感觉的一个有信仰的得救的人的那种心灵的宁静。
他妻子对他犯了那么重大的罪,而他对于她,像莉济亚·伊发诺芙娜伯爵夫人向他公平地所说的,又是那么神圣,关于他妻子的回忆是不应该烦扰他的;但是他不能够宁静:他不能了解他所读的书,他不能赶走那些关于他和她的关系的、关于他现在似乎觉得是他对她所犯的一些错误的、苦恼的回忆。想起了从赛马会里回家时,他怎样接受了她的不贞的自白(特别是他只要求她保持外表的体面,而不挑引决斗),这回想好像后悔一样,使他苦痛。关于他写给她的那封信的回想也使他苦痛;尤其是他的无人需要的饶恕和他对别人的小孩的关怀,用羞耻与懊悔燃烧着他的心。
此刻,重想着他和她的全部的过去,回忆着他在长久的犹豫之后向她求婚时的笨拙的言语,他感到同样的羞耻和懊悔的情绪。
“但是我错在哪里呢?”他向自己说。这个问题总是在他心中引起别的问题——那些别的人们,那些佛隆斯基之流,奥不郎斯基之辈……那些有肥胖腿腓的侍从们,是否感觉的不同,爱的不同,结婚的不同。他想起了整批的那种气盛的、强健的、自信的人们,他们不知不觉地随时随地引起他对于他们的好奇的注意。他驱赶着这些思想,他极力使自己相信,他不是为了现世的一时的生活,而是为了永久的生活而活着,在他心里有和平与爱。但是,他仿佛觉得他在这个一时的无足重轻的生活中做了一些无足重轻的错误,这感觉使他那么痛苦,好像他所相信的那个永久的得救是没有的。但是这个诱惑继续了不久,立刻在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的心中又恢复了那种宁静与高兴,凭着这些他能够忘记他所不愿想起的事情。
二十六
“哦,怎样,卡庇托内奇呢?”在生日的前一天散步归来的红润的快乐的塞饶沙说,把他的有襞折的外衣递给高大的、向这个小人俯着微笑的、年老的司阍,“哦,今天上绷带的书记来过吗?爸爸接见了吗?”
“接见了。秘书长一走,我就通报了,”司阍快活地?了?眼睛说,“请您让我来脱吧。”
“塞饶沙!”站在通达里面房间的门口的斯拉夫教师说,“您自己脱。”
但是塞饶沙虽然听见了教师的微弱的声音,却并没有对它注意。他站着,用手抓住司阍的腰带,望着他的脸。
“那么,爸爸替他做了他要求的事情吗?”
司阍肯定地点了点头。
上绷带的书记已经来过七次,向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有所请求,他引起了塞饶沙和司阍的兴趣。塞饶沙有一次在门廊上遇见了他,听见他可怜地求司阍替他通报,说他和他的小孩们都快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