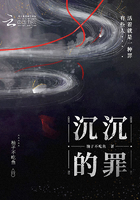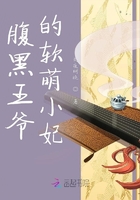人虽然清醒了,可由于长时间卧床,我的身体很虚弱,甚至连自己坐起来都不能。因为先前吃了几个月的蜂蜜和羊奶,肠胃变得羸弱,我只能先吃些粥汤。
唯一令我欣慰的是:我瘦了,瘦成了一道闪电,而且是一马平川的那种!
又在床上躺了两天慢慢有了力气之后,我就让大官儿扶着我下地走走。如果走累了,就坐在炕上按摩手臂和腿上的肌肉,算是开始了复健的旅程。
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以至于我的身体遭受到重创,短时间之内康复不了。但是我有种感觉,病痛已经过去,我会越来越好。
由于大雪封山的缘故,大叔和大官儿都在家猫着。大叔爱说话,故事讲的绘声绘色,我也从他的口中了解了很多事,复健的日子过得倒也不无聊。
半月之后积雪消融的差不多了,我也能自己起身下地了。大官儿每日都很兴奋,大叔和大婶却依旧是忧心忡忡。
在经历了一番十分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大叔和大婶只能硬着头皮的又把宋婆子请了过来。这也是没办法,谁让方圆十里之内只有她这么个半吊子大夫呢。
毕竟当初两方话说的都不好听,如今再去请宋婆子,她便摆着一张臭脸对大叔大婶好一顿冷嘲热讽,一边诊脉还一边嘟囔,“老婆子我就是医者仁心……”
然后她的脸色慢慢变了,万分惊讶的对我道,“你竟…你竟…你竟好了!”
我给了她一个僵硬的微笑,“都是婆婆医术高明。”,当然这完全是奉承话,我都没喝她的药,康复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对…一定是我的药医好的。”宋婆子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娘,阿余她好了。”大官儿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
“真的好了?”大叔和大婶仿佛还是不信。
“好了,好了!”宋婆子一脸喜色,甚至都忘了给这两夫妻摆脸子。
“噢,好了,好了!”大叔和大婶这才有种大梦初醒般惊喜。
一家人正兴奋之时,宋婆子却正了正身子故意的清了清嗓子。大婶马上就明白她这是要邀功了,眼珠子一转立马将她的医术夸上了天还说了许多感谢的话。
宋婆子找回了面子,觉得心情无比舒畅。然后大婶拿了二十个铜板给她,愉快的把她送出了门。
看着她走远了,大婶撇了撇嘴巴,“庸医,早晚会害了人性命!”
隔天宋婆子神医的美名就传扬开来了,这里面大婶还出了一份力,按她的说法是,吹得越神,摔得越死,必须送她一程。
我心里大汗,真是得罪谁也不能得罪女人。
果然,在大半年以后,村里一个猎户被猛虎咬断了腿,宋婆子在医治的时候用错了药,导致伤口迟迟愈合不了继发感染最终丢了性命,宋婆子也因此吃了官司。虽说没坐牢,但也赔的倾家荡产,遭人唾骂不止,最后自己配了一副药,喝药自尽了。大婶为此还觉得自己罪孽深重,连着几个月跑几十里路去庙里烧香赎罪,当然这都是后话。
村里人得了我病好了的消息,看洋景似的上门看我,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装睡,让大婶他们应付那些人。大婶还让我把称呼改了,让我在人前喊他们表舅,表妗子。
之后大约月余的时间,我的行动灵活了一些。为了让身体更结实一些,我开始跟着大叔和大官儿晨练。他们不上山打猎的时候每日清早都要晨练,我就跟着扎扎马步,大叔还教了我一套简单的六合拳。我只为了强身健体,从没想过有所成就,但碍不住时间长了也能学的像模像样。
大官儿力气大,功夫底子已经打好了,如今他主要练习箭术。大叔用干草扎了个圆形靶子,靶心染了红颜色让他练习射击。但是他这个人反应慢不够灵活,准头也不行,射出的羽箭十有八九都远离红心部分,就算我偶尔去射一箭都比他要准的多。气的大叔连打带骂的,他技术也没提高上去,但是这不妨碍他身体强横呀,要说打架估计他一个能打十个。我想这可能就是上帝已经给他开了一扇门,不会再开一扇窗户给他了。
倒是大叔这个人给了我太多惊喜,他的功夫很好,不仅身形灵活,而且出招狠辣,非常适用于实战,尤其是箭术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天上的飞鸟只要他拉弓,没有射不下来的。我估摸着这也许是打猎久了磨练出来的。
他还有一杆铁枪,舞起来那是虎虎生风!作为一个猎户我觉得他的职业素养是太过硬了,让人觉得屈才的过硬。看着他每每在大婶面前伏低做小一副怂样,我都觉得反差太大让人接受不了。他这个人是绝对的不显山不露水的做派,要不是跟着他晨练,我也不知道他有这些本事。
山路好走了之后,大叔和大官儿又开始到山里打猎,我在家帮大婶在家缝制新衣新鞋。大婶说扯布的时候没想到我还能活过来,所以新衣没有我的份儿。最终她给我做了一双新棉靴,还掏出了一件压箱底的枣红色旧冬衣给我改了套袄裙。对于这我觉得无所谓,反正穿她的旧衣服也冻不死。
我和胖大婶做着活计的时候,她还会同我说些闲话,比如说我昏迷时吃的那些好东西她有多可惜;比如说有些时候我缩成一团在炕上尖叫翻滚直吓得她魂飞魄散的;比如说我身上一层一层的出油总让她费力的擦洗;比如说自从我这个病秧子来了之后村里的女人都不来串门了外面见到她恨不得绕道走……
说这些的时候她的语气是要多嫌弃有多嫌弃,可我知道有些人真的是嘴硬心软。
大婶又问我家在哪里,我思索良久脑袋里除了一个叫阿玉名字其余只有一片空白,我和她说我想不起来了,她也没再做声。
我这人睡眠浅,夜里有什么动静都会马上惊醒,继续在外间睡我怕会影响大叔和大婶的夫妻生活,所以我主动和大官儿换了住的地方,换我住到西厢。大官儿睡觉死,天塌下来也醒不了,里屋有动静他听不见,睡外间正好。
腊月二十以后开始忙年了,我跟着大婶蒸馒头、磨豆腐、杀鸡宰鱼好一通忙活。
腊月二十之前,大叔和大官儿隔日就往山里去一趟,也是奇怪,他们二人日日都能得着好东西,别的猎户只能猎着野鸡、兔子这些普通的小东西,他们二人什么野鹿、白狐、麂子、貉子……山里有的都猎了个遍,连大叔自己都纳闷今年这运气怎么这么好。
年二十四宰了猪圈里的黑猪卖了,家里又收入一笔银子。
今年的收入高,年前给亲戚随礼的东西都是河洛城里买的,有点心、有干果、有肉、有酒,大婶觉得自家倍有面子,每日里都笑盈盈的,心情格外好。
桃符对联一贴,红红火火的新年来到了。
年三十早早的吃了年夜饭,大官儿就带着我到山村的高处遥望快要消逝的烟花,然后我脑子里有无数绚丽的烟花绽放,可却我不知道自己曾经在哪里见过那繁华的景象。
除夕的夜里我没有守岁,好像自己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习惯。就在那个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依偎在一个男人的身旁,他在我耳边喃喃细语,我却看不清他的模样。我红着老脸把被子捂到脸上,心道自己真是到了年纪了,春梦都做起来了!虽然我也不清楚自己究竟什么年纪。
年初一天未亮,各家就放了鞭炮,祭拜了天地后出门拜年。大叔他们三口穿着的光鲜亮丽的出去了,我躲在西厢没露面。怕别人见了我问这问那的,我懒得动脑子回答。
因为腰包鼓了,这个年大叔一家人过得可谓底气十足,特别是大婶在拜年的时候昂首挺胸的,都拿鼻孔眼子看人,惹得一些人好一通议论,成日里和她一起洗衣的那几个娘们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测,初一人来人往的就这样过去了。
到了初二,因为大叔这边没有亲人需要伺候,他也跟着大婶和大官儿一起回了娘家。我是没有立场跟着的,所以留在家里看家。他们一大家子住起来不方便,没两日也就回来了。本来这次她回娘家,她母亲属意把自家孙女也就是她哥的闺女说给大官儿,说是要亲上加亲。胖大婶可不傻,摊上她大哥一家子那个吸血鬼似的亲家那还得了,吓得她赶紧找个借口推了。
过了初六,陆陆续续的有人上门给大官儿说亲。附近这几个村子里各家情况大婶都扒的差不多,说的这些闺女最终没有个让她满意的。
春季里万物都需要修养生息,猎户不进山打猎,大叔一家开了一片田种植油菜花,等将来结了菜籽榨油吃。重活自然轮不到我干,我负责撒种子。
各家都忙活开了,也就没有上门说亲的了。农闲时我在堂屋外听见大叔他们夫妻二人商议,大叔说,“反正也没个合适的,我看不如就阿余吧!”
我心里当时就咯噔一下,开始检讨自己是哪里表现的好让他相中了。大叔那厢又说,“找不着她家人倒是更好,日后她没退路服侍我们定会更加尽心。”
这个蔫坏的糟老头子!原来是打的这样的算盘!我内心叹息,大官儿给我做个弟弟还行,我可是一点都没老牛吃嫩草的意思。
我不动声色的继续偷听,那厢大婶眉头微蹙,“她那身板我总觉得不放心,待个一年半载的再说吧!这期间再看看。”
听到这里我拍了拍胸口,觉得自己躲过了一劫。再有个一年半载的时间我的身体应该完全养好了,那时我自会离开。不是我忘恩负义,总有些事需要去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