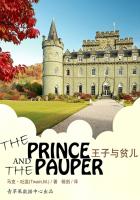坐在背后一排的癫子和牯牛两人连呼吸都被刻意地收敛了起来,仿佛已经凭空消失,让我丝毫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身旁正在开车的雷震子更是连眼珠都不敢向我这边瞟一下,像是一只被点了穴道的鸭子,抻长脖子直愣愣地盯着前方路面。
依然淤积在胸腔的怒火,化为一股又一股的气流从我的鼻孔里面接连喷出,一直喷到了环抱在胸前的双手手臂上。声音粗重而急促,在寂静的车厢中越发被凸显出来,如同牛喘。
大脑渐渐从暴怒之后的放空状态恢复,我意识到了这动静对比之间所带来的突兀和尴尬。想说点什么来化解,但是话到嘴边却还是拿不下那个架子。
干脆一偏头,摇下车窗,我看向了窗外。
绵密的雨丝在天地之间结成了一张无缝的网,窗子的斜上方,有一只鸟孤单地在天上飞翔,可不管怎么飞,也飞不出那张网,但它却仍在努力地摆动翅膀……
把整个头都伸出窗外,仰着脸,面对天空,看着那只鸟,任凭无数雨点劈面打了下来,冰冷的刺痛中,我突然就产生了一种物伤其类的悲凉。
此刻的我与它,又何尝不是一样。
明知道挣不破那张网,可也还要倔强地飞翔。
原本又涨又热的头脑在这一刻彻底变得清晰起来。
缺牙齿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应该继续挥动翅膀,这样,至少能够飞得久一点。
所以,在抵达之前的这段时间,我决定再仔细想想癫子所说的那个故事。
昨天晚上,癫子一如既往没有让我失望,他带回了一个久远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中包含了所有我想要知道的事情。
1958年在与苏联决裂之后,美国与越南的北部湾战争也打到了南中国的门口。
为了在战火一旦真的开启之后保证第一时间进入战争状态,使全中国变成了一个战区,在这个人类文明史中前所未有的巨型战区之上,被布置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位于中国的国境线,所有与外国接壤的省份,如东南沿海、东北三省、广东、新疆西藏等全部包括在内,史称“一线”。
第二道位于一线省份与京广铁路之间的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的东半部,这就是二线。
第三道是西南三省(四川、云南、贵州,含今重庆)、西北三省(陕西、青海、甘肃乌鞘岭以东),以及京广线以西的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的部分,以及广西的河池地区和山西雁门关以南等省自治区,是为三线。
其中,一二线是战略缓冲地带,而第三线处于内陆,大多都是崇山峻岭之中,也是战时总部。所以,第三线最为重要。
“支援三线建设”运动轰轰烈烈在全国上下开展起来。
数不清的战备物资从五湖四海涌向了中国内陆;无数的知识青年、壮年劳力被迫离开一线的大城市,背井离乡,告别家人,走进了荒郊野岭。
其中,就有一个来自山东青岛的青年女工。
这位女工坐着军用卡车,走过千山万水,来到了一个叫作溪镇的小镇。
在这个小镇外十多公里的深山里面,她把她的一生奉献给了一座代号叫作“二五零”的兵工厂,终其一生,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家乡,回到那个美丽的滨海之城。
更讽刺的是,在她死之后没多久,桎梏了她最美丽时光的、神秘的“二五零”也和荒唐的政令一起被彻底废弃。
这是一个小人物的悲伤,也是一个时代的悲伤。
但是,对我而言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故事的关键不是这个女工本人,而是她的儿子。
她在来到溪镇之后,嫁给了一位也在工厂工作的当地人,所生的那个儿子。
最初,工厂管理极为严密。虽然建在我们这里,但是它有自己的医院、学校、保安、住所、食堂,一切的设施都与当地政府没有关系,工厂里面的人也很少和我们当地人打交道。
再过了几年,伟人死了,政策开始慢慢变松,工厂里的很多人都想办法转回了自己的家乡,一批又一批,工厂终于开始败落了。
女工的丈夫是本地人,就算她想走,也已经走不了了,她的孩子也一样。
童年的伙伴都随着父母离开,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老师也纷纷远走。
最后,学校也就没了。
于是,那个青年女工的儿子和其他一部分留下来的儿童转进了溪镇当地的学校。
九镇和溪镇所属的这片十万大山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区。
我们吃最辣的菜,喝最辣的酒,一个汉子不能吃辣,对我们而言那简直是胯里没卵子,不如一个太监;吃辣让我们暴烈,心里不痛快就开口骂娘,骂娘不解恨,那就打架,打架还不行,那就提刀。一刀了恩仇,要死卵朝天。舍得一身剐,皇帝也敢拉下马。
我们贫穷,大山挡住了外面的世界,祖祖辈辈窝在山里穷了千百代,我们穷怕了,更怕别人说我们穷。穷怕了的人最看不得的就是城里人亮丽扎眼的体面衣着,和装腔作势的白眼。
我们霸道,在这穷山恶水的地方,好东西不多,自古以来,不是野兽就是罪犯,遇到好东西了,不霸道,不争夺,忍辱偷生,活不下去。
所以,自古以来我们这里专产全中国最恶的匪,也产全中国最猛的兵!
当一个衣着体面、姿态高傲,就连吃饭口味都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突然出现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如果他不够强大,他会很快就低下高傲的头。
如果他也很强大,那么对于双方而言,都必定会是一种痛苦至极的艰难融合。
女工的儿子强大得超乎预料,所以他的融合也就更加痛苦。
不过,最终,他还是成功了。
他学会了吃辣,也学会了提刀,他用血得到了本地人的尊敬,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他付出的,则是他漫长的未来。
他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一个流子,一个名动一方、无人敢欺的大流子。
不过,他的运气不太好。
一九八六年,在人生的第一个巅峰时期,他被捕入狱。
当蹲完苦窑,于去年出狱之后,他却发现他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
拿走他一切的那个人叫作边海洋。
而边海洋曾经是他底下的小弟。
他在被捕之前,有过很多兄弟。
出事之后,抓的抓,跑的跑,逃的逃。剩下几个还留在溪镇的,也被势不可挡的溪镇十杰先后归拢。
当初跟着他一起白手起家打天下的老弟兄之中,有一个外号叫作九佬的人,只有这个人没有投靠边海洋。而是退隐江湖,在溪镇后街开了一家很小的茶水麻将馆,靠着做周边一些老街坊的生意来求口温饱,聊以度日。
边海洋还没出头的时候,好像欠过九佬一些人情。
所以,小边也就放了九佬一马,让他自生自灭,只要不再踏入江湖就行。
没想到,一年半以前,他刚一出狱,飘零在外几年的头号骨干盖将就立马赶了回来,修身养性的九佬也迅速归位。三人还合着他在狱中新认识的几个朋友,再加上周边几个被归拢的散兵游勇,又一次在道上吹响哨子,扯起了旗。
于是,在一个莫须有的借口之下,边海洋砸掉了九佬的小茶馆,正式开始了对他的全力打压。
这本不是一件值得稀奇惊讶的事情。
狗之所以愿意当狗,是因为它从来没有做过主人。
一旦当上了主人,还有人会愿意当狗吗?
万丈红尘,酒色财气,本来就没有豁达和大度这回事,豁达大度只是因为没有真正试过权力的滋味。
他试过了,边海洋也一样。
他们理所当然地陷入了那条残酷至极却又颠簸不破的江湖至理:一山,容不下二虎。
他输了。
江湖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这是一句老话,也是一句俗话,但又老又俗的话,通常都很有道理。否则,这些话也就不能流传得这么老、这么俗。
所以,他输了。
本来就是刚出狱,根基不稳的团伙再次分裂,除了盖将、九佬等数几人依旧追随之外,曾经不可一世的他沦落到了没钱没人没地盘的可悲地步。
但是,他给自己留下了一条命。
在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之前,他在一个大白天,当着很多人的面找上了边海洋的家门,两人在房里单独谈了一次话,没人知道谈话的内容。
只是从那天开始,二十七八岁的他就过上了七八十岁的退休生活,韬光养晦,再不插手任何江湖事务,与九佬合伙在溪镇中学边上开了一家小录像厅,整天安安心心地待在店子里面,和朋友打打小牌,喝喝小酒,赚点小钱。
溪镇,他可以继续活下去,却再也没有了属于他的容身之地。
但是!
我不信!
我也是一个流子。
所以,我不信。
我从来不信一个人在风光过后,正当壮年却可以心甘情愿归于平凡。
退休?
要退了才会休。但,江湖,是个进了就退不了的地方。
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会试一试。
试一试他对于权力的向往和依恋还有多少?他胸中的仇恨与嫉妒又有几许?
我有一个预感,我知道自己肯定会赢。
“三哥,三哥!到了,就是前面那家店子,他就站在门口的,看到没?”
癫子的话把我从沉思中唤回了现实。
顺着癫子的手指看去,老化的橡皮雨刷一下又一下地刮着车窗,发出了难听的杂音,被雨水模糊的窗玻璃却在每一次的杂音中有了瞬间的清晰,就像是一个接触不良的幻灯机,闪闪烁烁地在我眼前放映出了一张前方的街景照片。
在这张照片里,我第二次看见了洪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