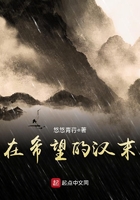相顾无言是痛苦的,姜凡很想快点结束这次纯属巧合却又冥冥中似已注定的偶遇。
时光偷偷在指缝中溜走,惊不起一点涟漪,当人们晃过神来的时候,很多事或许为时已晚。
周梦瑶若有所思的望着姜凡,片刻之后,她察觉到了姜凡微微晃动的眼神,然后低下头咬了咬嘴唇,额间的流海随夜风荡起一个美妙的弧度。
姜凡正要启齿,她已悄然转身,留下一个落寞的背影。
她就这么走了,姜凡感到很意外,于此同时,姜凡似乎感到胸膛深处的某样东西在慢慢融化。
……
翌日,午后的暖阳稍纵即逝,仅过了半个时辰,天空便下起了纷飞不停的雪花,昨日的积雪还未化尽,直至申时,东京城内的雪已经一脚踩不到底了。
姜凡将店里的活儿丢给阿欢阿正之后,朝着繁塔的方向走去。
雪景虽美,但着实冷了些,姜凡将自己捂得结结实实活像个白粽子,要风度不要温度那是大宋风流才子们干的事,姜凡可是万万不愿意的。
姜凡大概想通了,猪队友也是队友,既然遇上了,总该做点什么,若是踟蹰着不敢往前,那便太索然无味了些,何况姜凡真是打心眼里瞧不起繁塔里那些所谓的鸿儒门生,且不说他们是否歪曲了前人的本意,单单是樊楼里那个仕子自以为是的狂妄之言便让姜凡内心一阵狂呕。
即便是汴京八景,一旦遇上了这样漫天飞雪的寒冷天气,闲游之人便也寥寥无几。这就像寒冬腊月里的故宫,除了那些外地游客愿意在此拍照留念之外是没有几个本地人会在故宫门前多停留几分的。
十数庙宇,三两草庐,姜凡一眼望去,尽是白皑皑的一片,前些日子还能见到的一众僧侣,现在却连人影也没了,估计是猫在房间里烧炭火取暖罢,秃驴们没了头发,一阵风雪吹在脑门上,便能将他们冻得直打哆嗦。
繁塔一角,却又是别一番场景。该有的桌椅板凳一样未少,热闹的人气儿在这清冷的寺内突兀出一种鲜明的对比,但这群人,并不是和尚。
姜凡稍稍伸长脖子,远远地瞅了几眼,似乎还能从中认出几个老顾客来,瞧着他们正襟危坐却又因为风寒刺骨而时不时的打几个冷颤的滑稽模样,姜凡差一点就笑出声来。
这些家伙倒还真是群能吃苦的乖学生,姜凡不禁暗暗感叹道。
程先生正讲得酣畅淋漓,拧紧眉目,字字顿出的模样感觉比天清寺主持开坛讲经时的模样还要威严些。
姜凡憋足了性子听了一会,这位程先生吧唧吧唧讲个没完的理学基本上可以用六个字来形容,“存天理、灭人欲”是也。当然了,若仅仅是这样的话是无法吸引这么一帮自视甚高的才子来听讲的,原因很明显,光是要别人禁灭人欲,专一至理,而不把这个“理”字讲好讲透说出个所以然来,并不会有谁心甘情愿冒着漫天大雪来这间破烂小庙听讲,也不会流传出鸿儒“程先生”这个名头来了。
没有人注意到姜凡,程先生讲得很投入,那帮仕子听得也很投入,姜凡零零散散地听着,这帮人从三纲五常讲到阴阳五行,连佛道两家的一些东西都掺杂进去讨论,倒是有种集各家之所长的气势。
有趣的是,程先生也有些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三从四德。
这个词对于台下的某些仕子来说很新鲜,但在姜凡听来,这几个字真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二十一世纪的老婆大人那叫“从不体贴从不温柔从不讲理。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惹不得。”
一千年前的说法那可差远了,姜凡虽然清楚,但听着“程先生”抑扬顿挫的讲出来,竟感觉别有一番独特的“韵味”。
“三从、四德,见于春秋之始,流传千载,是为女子之守也,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德行操守,死之不渝。”
这帮太学两院和国子监出来的自然不是傻子,有那么几个饱读古书的人听到此处便会有些奇怪,于是乎起身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然后问到:“先生,据学生所知,“三从”是古代女子守丧之时的礼节,“四德”是周朝礼官教导宫廷女子的仪范,学生不解,还请先生赐教。”
这个人叫王焕,姜凡很有印象,还记得那次在风月之地喝酒的时候,就是这个家伙在大庭广众之下打翻了醋坛子,搞得姜凡如坐云端的兴致顿时跌入谷底。姜凡微微扬起了嘴角,不禁猜想坐在上边的程先生要是知道了台下听讲的某个家伙竟然流连风尘女子,还争风吃醋,估计他会气得吹胡子瞪眼,然后厉声责骂这个家伙怎么能够被可耻的yin欲冲昏理性。
程颐的脸色有些变化,或许是气愤,也可能是尴尬。毕竟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要是被人拆穿了,那他估摸着得赶紧找个地缝了。
姜凡将两只手塞进袖子里,饶有趣味地望着台上的程颐,看这群人聊天吹牛倒是比昨天的那台《梁祝》来得更有趣儿些。
“非也,非也。古之仪理传之于今,当可延其精髓,广其至理。”程颐的语速变得快了些,语言的条理也差了些,甚至连说话的语气都显得有些急促:“然也,然也,岂不察女子近之不逊,远之则怨乎?!心性使然,尤不可逆。更有先贤仲尼云之: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若不灭其欲,守其德,何以倡天理乎?”
姜凡若不是怕被这群人追着打,此刻他真就放开捂在嘴边的手哈哈大笑起来了。这他娘的一会非也一会然也的,是要扣多大一个帽子在女人头上啊,被贬损得一无是处不说,要是不遵守三从四德,竟连老天都对不起了。
看着一帮仕子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姜凡渐渐感觉这场景和那些搞传销的似乎有些相像了,互相洗脑,然后沉浸在集体营造出的病态精神世界之中。
姜凡的目光寻视了很久,终于见到了那个人,楚墨维的表情很严肃,板着脸跟别人大讲道理的模样竟带了丝泼妇骂街的韵味:“女子从一而终,即为丧寡,不可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饿死都不能再嫁吗?万一她还带了个幼子呢?”
“先生之前才讲过,人就是怕冻死饿死才以饥寒为借口不思进取,更有甚者,为一己之私欲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这就是我们必须摒弃的欲,你难道忘了最关键的那六个字了么!”
或许程颐觉得这句话放在此处太夸张了,当时他只是想提倡一下学生们莫要贪口舌之欲,但话传着传着似乎就变味了,就像他肆无忌惮的曲解先人的东西一样。
“你们先静一静,”他清了清嗓子,又郑重其事的开讲了:“适才楚公子所言确有道理,即便孤寡妇人余生艰苦,可由司农府广惠仓救济,绝不可再嫁。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识理之人观之,当知其不可易也。”
……
姜凡知道,大宋朝很有钱,有钱到宋仁宗的后代子孙们可以用千里江山和万两黄金来换得一隅苟安,然后谱写出西湖歌舞几时休,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样的荒唐。
须臾,姜凡忽然醒悟,这样奇葩的学说能逐渐壮大,只因为它最为核心的东西正是朝廷所需要的。
吏治不清,饥民暴乱,乃至义军造反,都是因为这些人没有摒弃他们的欲。如此想来,朝廷没有任何责任,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帮刁民没有信奉天地君亲师的伦常,没有灭掉自己那些与生俱来的人欲。
世俗并不一定迂腐,但这帮人姜凡却越看越迂腐,不停地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臭脸,自命清高,实则龌龊至极,将来就算发达了,也不过是朝廷用来洗脑平民百姓的一颗棋子而已。
姜凡想到了狂歌五柳前的李太白,逍遥不羁的诗仙若然再世,一定会饮一壶浊酒,赋诗百首,将这群人骂个狗血临头。
夕阳西下,不知何时,它已悄然躲进郊野的山崖,只留下半轮红日,为这座城披上了一层蝉翼般的金纱。
那帮人散了,嘴上说着不怕冻死饿死的楚公子终究还是要回去坐在温暖的炉旁吃饭。姜凡并没有要刻意跟着他,因为附近百十步都能听见他的声音。
临出寺门的时候,姜凡从他和别人的交谈中听到了几个字:正月初九,周家千金。
姜凡感到自己的胸膛在剧烈起伏,然后脑海里一阵闷响,时间,只剩下不到半个月!
他娘的,三小姐嫁给这种人还不如死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