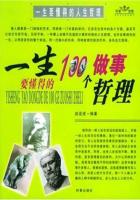一瓣瓣桃花飘落在山间的清泉,一股股清泉结成一条小溪,一条条小溪汇成一条大江。大江之上,浓雾之中,数艘小船整齐划一地在江面上行驶着,中间有一艘大船,沿江而下。两岸春风吹拂,绿草飘曳。
这是晋朝太元七年仲春,当今皇帝是晋朝第十三位、永嘉南渡以后第九位皇帝——司马曜。这司马曜不过二十出头,已在皇位上坐了有好几年。当皇帝的自然有当皇帝的优越,不过也少不了一些平常百姓感受不到的郁闷。这郁闷有朝廷里头的,但更多是因为来自北边的虎视眈眈。这是这个少年天子的恐惧,也是南方所有人的恐惧,尤其是那些多年前从北方逃来的人,或许他们之中很多人已经归为尘土,但是他们的子孙依旧背负着那个噩梦。
司马曜在早朝散后又召见了几位大臣,问到:“诸位爱卿有何看法不妨直言。”几位大臣都是朝中位高权重之人,但此时却吞吐吐吐,如此军国重事,岂敢妄议。众人都在等一个人开口。那人看了看众人,然后回答道:“回禀陛下,臣以为,氐秦虽号称百万雄兵,势在侵我大晋,但其国势未稳,人心不一,若我大晋上下齐心,必能以一当百,击溃强敌。”说这话人是谁?不是别人,正是当今的宰相,侍中、卫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国诸军事的谢安。这谢安字安石,少年时便已有国士之誉,但一直高枕东山,与王羲之等人畅游会稽,兰亭一会,风流无比。后来应桓温所请,成为其幕僚。当时桓温大权在握,晚年时更是传言有僭位野心,幸得谢安从中周旋,国家才免于改名换姓。谢安所说的氐秦、强敌,便是那东灭燕国、西降仇池、北破代国、南夺蜀中的秦国,氐族人在长安建立的国家,一个已经统治了北方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正在谋划着南侵,让晋国上下如坐针毡。司马曜听了谢安的话,心中不安稍有缓解。司马曜很是信赖谢安,当年若不是谢安和王坦之,恐怕自己已经成为了第二个海西公。司马曜问到:“众卿是否赞成谢大人所言?”众人齐声答到:“谢大人所言极是”。司马曜又说到:“甚好,朕意也是如此。朕已诏桓冲入京,数日后便到,诸位先回去想想,若氐秦来犯,我晋国当如何对敌。”众臣回禀到:“谨遵圣旨,臣等告退。”
长江上,浓雾尽散。此时正是午饭时候。大船上,众人依次围坐,其中上首居中者,一身统帅着装,年纪五十开外,约莫三寸胡须,眉宇间英气逼人,不怒自威。此人是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谯国龙亢人桓冲,字幼子。这桓冲可不是一般人,已故大司马、南郡公桓温便是其大哥。桓冲兄弟共五人,大哥桓温、二哥桓云、三哥桓豁、四哥桓秘,桓冲排行老幺。这几兄弟都做过地方大吏,尤其是那桓温,更是拥兵自重、权倾朝野,连皇帝废立也是轻描淡写。当今皇上的先皇司马昱便是由桓温所立。话说回来,大哥、二哥、三哥都已作古,四哥桓秘在大哥桓温死后作乱,被桓冲放逐,已有数年不问世事,因此桓家由桓冲坐镇,其众多子侄中,凡是为将者,都分驻于荆州、豫州各地。桓家儿郎大多出类拔萃,其中桓豁长子桓石虔、三子桓石民乃当世猛将,桓豁次子桓石秀、桓冲长子桓嗣、桓温五子桓伟皆为当世文杰。
饭食过后,小兵倒好热茶,桓冲抿了一口,向众人说道:“陛下此次召我入京,不为别事,氐秦厉兵秣马,况且襄阳已被苻丕攻占,南侵只是时间问题,我晋国已无退路,诸位将军有何看法?”桓冲话音未落,座下一大汉厉声说道:“他苻坚小儿当我晋国无人吗?只管放马过来,看我不杀它个片甲不留。”此人是桓冲帐下猛将朱绰。桓冲笑道:“朱将军快人快语,若我晋国男儿皆似将军这般人物,何愁他秦国兵马。”朱绰嘿嘿笑道:“我老朱只管上阵杀敌,其他事我就管不着了。”旁边另一人说道:“当年曹孟德何等英雄,挟八十万之师,却于赤壁折于孙刘数万联军,致使三分天下,那苻坚可比得了曹孟德?何况王猛王景略已死,苻坚本是志大才疏之人,如今缺了股肱之臣,穷兵黩武,不过是自取灭亡。”桓冲微微点头,说道:“我儿见识果然不凡,你再说说秦国何以会自取灭亡。”原来刚才说话之人便是桓冲长子桓嗣,字恭祖。桓嗣回道:“回父亲,孩儿认为,秦国目前状似强大,其实未必,第一,秦国近年来东征西战,将士疲于奔命,百姓更是苦不堪言;第二,秦国军队中,降人几占半数,如燕国降臣慕容垂、羌人姚苌、丁零人翟斌、赀虏乞伏国仁、河西鲜卑秃发乌孤、匈奴人刘卫辰等人皆是虎狼之辈,如今在秦国身居要职,拥有各自势力,怕也是这些人怂恿苻坚伐晋,不过是唯恐天下不乱,秦国一旦生变,这些人都会各自为战,北方怕是会再次陷入混乱;第三,苻坚的王位也是篡夺而来,其对宗族诸公多是小心提防,不敢委以重任,又将氐人分散于各地,令氐人寒心。如此三点,秦国难成大事,我晋国只要坚壁清野,秦人只会自乱阵脚。儿之愚见,望父亲和诸位将军勿笑。”桓冲尚未开口,那朱绰扯开了嗓门:“大公子说的在理,末将本也是这么想,可是肚子里没啥墨水,说不出个道道。”众人大笑。桓冲说道:“嗣儿所言正中秦国之弊,但苻坚毕竟不是等闲之辈,想当年我随大哥北伐,在蓝田与氐人大战,差点被苻坚所擒,幸有我侄桓石虔才逃过此厄。况且秦国人才辈出,尤其是苻坚幼弟苻融,此人不仅有理政之才,更有军战之谋;苻坚庶长子苻丕有乃父之风,堪称秦国第一猛将;还有大将吕光,可与百多年前的张辽、徐晃相匹。再者,慕容垂等人虽有二心,但一时并无反叛的可能,若此人为伐我之先锋,实为一大劲敌,临敌之时,不可大意。”众将点头称是。桓冲向桓嗣问道:“怎么不见灵宝那小子?”桓嗣回道:“六弟淘气,怕是与大该到其他船上去了。”桓冲不悦:“小子不好好念书,就知玩乐,待会让他来见我。”“是”,桓嗣接着说:“父亲,前面就是寻阳了,我们今晚是留在船上,还是上岸到城中歇歇?”桓冲道:“你堂兄桓石秀现在任职江州刺史,便住在寻阳,我本想见他一见,但陛下急诏,不可耽误,暂且就不上岸了。等过了湖口,改走陆路,三日内便可到京城。”桓嗣等人诺诺。
春天的阳光不似夏日那般毒辣,一个少年躺在船舷上,两眼盯着白云蓝天,此少年便是桓冲口中所说的灵宝,大名桓玄,字敬道,小名灵宝,为桓温第六子,袭爵南郡公。桓温原配为明帝之女南康公主司马兴男,未生子,其诸妾共生六子:长子桓熙、次子桓济在桓温死时不满桓冲掌权,谋乱未成,被幽禁于荆州某地;三子桓歆天资平平,不喜争斗,今为天门太守,吴国孙休时武陵郡稾梁山裂变,万丈峭壁洞开如门,于是把稾梁山改名天门山,分武陵郡西北部设置天门郡,此地开化未久,蛮夷居多,山水奇异,道路险阻,自有一番风景;四子桓祎天生鲁钝,闲散在家;五子桓伟才华出众,少年时更是风流倜傥,但桓温觉得其轻浮于事,因此没有委以重任,桓伟一直隐居于荆州宜都郡,已近三十年;然后便是六子桓玄,得此儿时桓温已五十七岁,因此桓玄与其诸位兄长年岁悬殊。桓玄自幼聪慧,深受桓温宠爱,桓温死后遗命由桓玄继承其爵位,当时桓玄不满五岁,一晃已过去九年。这九年来桓玄跟着叔父桓冲住在荆州,先是住在江陵,后又住在上明。
“大该,你看那朵云像不像一匹马?”桓玄手指着天上的云朵说道。“哪里像马,分明像头牛”,旁边那个叫大该的少年不屑地说道。“我看你像头牛”桓玄不服气地说。那个叫大该的少年本名冯该,冯该之父当年跟随桓温讨伐燕国,战死沙场,桓温便将冯该留在桓府。冯该年长桓玄四岁,桓家人叫冯该为大该,是因为这小子身材魁梧,痴痴傻傻。冯该不喜读书,但力大无穷,又跟着桓石虔学了一身武艺,所以自小便当起了桓玄的护卫。桓冲此次应诏入京,原本只带了桓嗣及朱绰等数位将军,但桓玄知道后非要一起来,桓冲拗不过,便让他和冯该也跟着。“公子啊,这船上好闷啊”大该咕囔着,桓玄小声说道:“大该,要不咱们上岸玩玩去?”大该心里虽然也想,但桓冲吩咐,不许桓玄乱跑,到这小船上来也是不妥,没有桓冲命令,哪敢上岸去,所以大该只是一通摇头。“你怕什么,叔父知道了由我担着,你就说是我逼你的,行不?”桓玄看着大该说到。冯该仍是不允,桓玄也只好叹息。
桓冲小憩了片刻便让桓嗣把桓玄叫来,桓冲跟桓玄说道:“灵宝,你也有几年没有见你石秀哥了吧?”桓玄道:“好像五年前他回过上明一次,我都不记得他样子了,听嗣哥说石秀哥现在住在寻阳,我们是不是要去看他?”桓冲道:“你石秀哥最近身体抱恙,我本想去探望,但要事在身,不便耽误,我想让你跟嗣儿去看看。”桓玄一边点头,一边说道:“叔父要事在身,这次带的护卫又少,嗣哥不在叔父身边,那怎么行,让大该跟我去寻阳就行了。”桓冲笑道:“也好,但你要切记,凡事不可鲁莽,尤其不要与人争斗。你在石秀家住上几日,待我从京城回来再接你一起回荆州。”桓玄回道:“玄儿知道了。”然后桓冲又是再三叮嘱,又对大该一番叮嘱。桓冲派了一队护卫跟着桓玄大该,此时出发,天黑之前能赶到寻阳城。
惠帝元康元年,因扬州、荆州地广,不易管理,于是分扬州之豫章郡、鄱阳郡、庐陵郡、临川郡、南康郡、建安郡、晋安郡和荆州的武昌郡、桂阳郡、安成郡共十郡为江州。永兴元年,又从庐江郡分出寻阳县、从武昌郡分出柴桑县合为寻阳郡。江州州治本在豫章,桓石秀任职江州刺史后,将州治迁到寻阳,此地襟江带湖,处于荆扬之交通要道,桓石秀此举意在拱卫桓家势力的中枢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