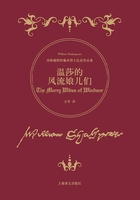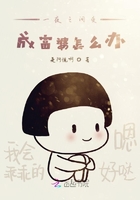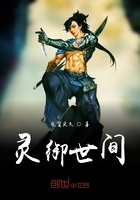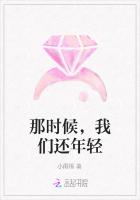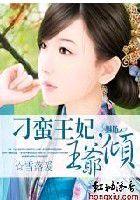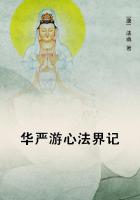济南《老照片》的编辑问我要老照片,我说没有,“****”期间都烧毁了。编辑还是让我找找,万一有“漏网”的呢?我只好翻箱倒柜找起来,但仍一无所获。却意外地找到一九四三年我的一本纪念册,封皮已没有,同普通的小记事本一样。翻了一下,早已忘却的往事涌上心头,把我带回少年时代。
一九四一年先君蓝公武从日本宪兵队释放出来后,全家便从北平城内北沟沿庚二十八号搬到西郊成府街红葫芦二号。宪兵队的拷打并未使父亲屈服,他依然宣传抗日,并誓不与当汉奸的朋友往来。全家靠典当度日,把北洋余孽、大汉奸王揖唐以老朋友身份送来的米面倒在街上。父亲的抗日爱国行动受到华北知识界的敬佩。
父亲要看报,但没钱订报,只好看朋友们的报。我上午到成府街一家店铺取报,拿回家给他看,他看完后下午我再送给订户。我送了半年多报。走到红葫芦胡同口,便看到永远坐在小酒店门前的掌柜郭大胖子,他有个弟弟叫郭二胖子,替燕园住户搬家。郭氏兄弟虽算不得燕大的名人,但燕大师生没有不知道他们的。
拐过小酒店便到槐树街了。顾名思义,街道两旁都是槐树。夏天每棵树上都挂着几条“吊死鬼”。我一边捉“吊死鬼”一边往前走。先到陆志韦先生家。陆先生是著名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担任过燕大代理校长。我按铃,开门的多半是陆太太,但她并不接报,慈祥地把我让到屋里,陆先生走过来接报。他同我没什么可谈的,摸摸头或给我几颗小孩弹的玻璃球。这些玻璃球可能是他孩子们弹过的。陆先生有四子一女,年龄都比我大得多,从来没同我玩过。他们的名字我都记得,但不知怎么写。只会写老三陆卓元的名字,因为他在我的纪念册上画过一幅水彩画,画的是燕大东大地的一角,上面写着:“文泰(我那时的名字)小弟留念。卓元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陆先生除慈祥外没给我留下其他印象,但我却记住了陆太太脚上穿的一双绣花红鞋。一九五二年我在王府井大街上遇见陆先生和陆太太,陆先生仍非常客气,客气到谦卑的地步,一再握着我的手上下摇摆。我低头看陆太太的鞋,仍是绣花红鞋,不过已经很旧了。陆先生告诉我他在语言所工作,并给我留下地址,但我没去看望他们。我当时是进步的大学生,岂肯同司徒雷登的同事交往。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实在幼稚,还有几分内疚,此后再没见过这对慈祥的老夫妻了。
再往前走一段路便到郭绍虞先生家了。郭先生是燕大中文系主任,中国古典文学第一流学者。但那时我对他的学术成就一无所知,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几十年后才翻阅过。我记得郭先生夏天衣服穿得很少,仿佛赤膊。郭先生同样慈祥,接过报也不同我说什么,有时摸摸头。郭伯母倒同我说话。他们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女孩子们都比我大,我称她们为姐姐,小儿子郭泽宏与我同年,我们能玩到一起。但他同我与其他小伙伴的玩法不同,不到河边捉蜻蜓或到圆明园摘酸枣,而是在屋里画画。大概郭伯母不让他到外面玩。那时街上贴着日本人的宣传画《第五次强化治安》,“皇军”的刺刀指着两个小人:“共匪和奸商”。我们便画一个中国人,刺刀指向“日本和满洲”。姐姐们有时过来看看,夸我画得比泽宏好,泽宏便不高兴了。我的纪念册上有两位姐姐写的话:“文泰弟:愿你永远保持着天真孩子的心,并有着永远的可爱。以宁,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以宁是三姐。“文泰小弟:愿你天真活泼的性格永远存在世上,愿你努力读书将来为国争光。之翰志于故都,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黄昏。”之翰应是二姐。从笔迹上看,两位姐姐已经是高中生了。她们现在何处?早已事业有成,儿孙满堂了吧。还记得我这送报的小弟弟吗?一九七七年,我陪同一位先生到上海访问郭先生。郭先生接待了我们,仍那样慈祥,但比我送报的时候苍老多了。我坐在那儿,希望他能认出我来,但他没认出来。我终于忍不住问道:“郭先生,您不认识我了?”他不好意思地说:“年纪大了,开会时认识的年轻朋友记不清了。”“郭先生,我是您住槐树街时给您送报的小孩啊!”“噢,你是……”他想起送报的小孩,却叫不出我的名字,“蓝公武先生的孩子?”说着拉住我的手。我有很多话想对郭先生说,问问郭伯母、姐姐们和泽宏的情况。但访问者问个没完,我是陪他来的,不能喧宾夺主。访谈的时间过长,郭先生显得疲倦了,我们便匆匆离去。郭先生没挽留我,只分手时握了握手。以后再没见到郭先生。偶尔在朋友家见到郭先生写的条幅,我便后悔不迭。我若求郭先生一幅字,他肯定会写的。
我的纪念册里还有张宗颖和张宗烨写的话。宗颖是张伯伯(张东荪,我从小就管他叫张伯伯)第三个儿子,写的是:“愿你长得又高又大志气也高大。文泰小弟留念。宗颖书 二月七日”。字写得漂亮。“****”期间张三哥和张三嫂双双自杀。宗烨是张伯伯的小女儿,与我同岁,写的是:“文泰兄留念:我们要做好儿童,为国家民族争光。妹宗烨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小孩的字体。她叫宗烨,可我们都管她叫大华。宗烨是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是张伯伯唯一在世的子女。我见过张伯伯多次,了解的却极少。北平解放后我亲耳听他说过:“北平和平解放是生平第一快事。”言下之意他是出过力的。他曾是****和傅作义之间的联络员,把****的意思传达给傅作义,再把傅作义的答复转告****。张伯伯对自己的作用有几分得意。一九五〇年,我随父亲从城里到燕大东大地三十四号看他。他吃过午饭说要休息,撇下老友径自上楼了。父亲便到红葫芦旧居看望老房东,等张伯伯睡醒午觉继续谈话。一九五二年突然听说张伯伯出事了,他来看父亲,连连说:“志先,我听你的。”也是我亲耳听见的。这是我同张伯伯的最后见面。
我的纪念册里没有陆先生、郭先生和张伯伯写的话。我根本没想到请他们写,如果请他们写,他们也许会写几句。我的纪念册上就有比我大得多的杨明照先生选录的张华的诗:“水积成渊,载澜载清。土积成山,鄗蒸郁冥。山不让尘,川不辞盈。勉尔含弘,以隆德声。选录张华励诗以诒文泰小友。明照壬午孟春”。上面盖了印章,并贴着照片。还有杨太太写的“自求多福”,上面也贴着他们夫妇抱着一岁多小孩的相片。杨先生英姿勃发,杨太太憨厚慈祥。杨先生录的诗我自然看不懂,但字写得工整有力,我非常佩服。杨先生是陆先生、郭先生和张伯伯的晚辈,我见他时不过三十几岁。杨先生现在桃李满天下,我的一位朋友便是他的高足。两年前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见到杨先生的近影,蓄着长须,俨然美髯公了。
我翻阅纪念册,回首往事,深感人生苦短,须臾间,连我这个送报小孩也步入耄耋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