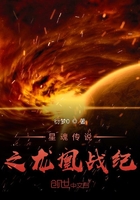苏厉作为魏国的上大夫,本就不像魏齐一党那般奢华,所以设的宴席也是比较简单的,除了一些清酒黍米豸肉之外,就再无别的什么东西了。那盗昇本以为可以借此大吃大喝一番,哪里知道到了才发现这酒食也就不过如此,所以原先的兴致也少了一大半。至于其他的几位,则早就习惯了行走江湖的清苦生涯,所以也并没有太多在意。
苏厉得见荆轲领头入门而来,连忙撩起长袖,加快了步伐直奔门槛处而来。直到临近荆轲才抱拳施礼道:“荆使大驾光临敝舍,苏厉照顾不周之处,还望荆使谅解。”
“苏大夫盛情,荆轲心领了,此番前来打搅了。”荆轲一见苏厉如此客气,便立即抱拳还礼道。
“诶,荆使这是哪里话,若不是荆使救了魏王,获得魏王的赏识,我苏厉苦苦上谏的合纵大计怎能成功?”苏厉一边和荆轲说罢,一边扬手示意众人道,“苏某略备薄酒一杯,还请诸位高人但请入座。”
盗昇看了看这桌上的酒食,不由得轻声嘀咕了一句:“这还真是备的薄酒。”只是他刚吐出这句话来,却被薛伦一把拉住了袖口,转头朝薛伦看去,之间薛伦严肃着脸面,朝他摇了摇头。
盗昇知道这便是让他不要随意放肆,于是只得闭了口舌,闷声不吭地随意选了一处酒案,坐到座位上去了。
可他哪里知道,他这随意一选的位置,却正是那两旁列席酒案的左上位置。左上之位,在主宾相往的交际场合,是最为尊贵的,是具有最高身份的宾客才能就座的位置,换言之,这本就是为荆轲所设的席位。可他盗昇平时在市井里混迹惯了,哪里懂得这些官宦人家的座次礼仪,不假思索便坐了上去。
苏厉一见盗昇这般举动,不由得心头一愣,十分不解地转首询问荆轲道:“这?”
荆轲虽说在什么场合得有什么样的姿态,可他毕竟也是浪迹江湖的浪子,所以也没弄明白这苏厉突然转首询问自己这个字的意思,也便一下子显得满脸茫然。
倒是从旁的公输蓉看懂了苏厉脸上的疑问,立即朝苏厉呵呵一笑:“不碍事不碍事,我家钜子向来礼贤下士,从不计较这尊卑之分,当年的信陵君魏无忌迎接夷门侯生,不也是不顾自己的身份高贵,将左席虚让给了侯生吗?”
苏厉听了公输蓉这一席话,顿时恍然大悟,立即连连向荆轲抱拳致礼道:“荆使果然不愧为人中豪杰,可以如此不拘小节,礼贤下士,难怪能引领这一帮高人相助,实在是令苏某惭愧至极啊。”
苏厉这一番对荆轲的赞誉之词,更是让荆轲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他也是个聪明人,知道是公输蓉从中暗自解了自己的围,所以便随着苏厉的话连连谦虚道:“不敢当不敢当。”
哪知苏厉一见荆轲竟还这般谦虚,更是有所自惭,便随即扭头朝自己门下的侍人交代道:“今后但凡有宾客临门,无需为我特意留下左上之席,一切尽随客人之便即可。”
“诺。”侍人听了苏厉的一番交代,点头答应着记下了。
随后,大家各就各座,也便没了这以往的那一套宴席上的规矩俗套,只要人人坐上自己的位置便可。荆轲也浑然不知这其中的规矩,所以也自行随意找了一处偏僻的地方,坐了下来。
苏厉坐定之后,正要抬头和荆轲寒暄一番,忽然发现荆轲坐了离自己的主位较远,而且双眼似乎在盯着身后的屏风,满脸显现出陷入沉思的样子,不由得心中又生起了疑问,便好生朝荆轲道:“不知是何物让荆使这般有兴趣?”
荆轲正盯着那屏风细看,一时之间竟也没有注意到苏厉的问话,只待身边的公输蓉轻敲了下酒案,才回转过神来。再仔细回想方才的周围的声响动静,才发觉苏厉有此问话。
“哦,苏大夫莫要见怪,荆轲只是想知道这屏风之上所画何人?”荆轲一边说着,目光又移向了这身后的屏风,仔细打量起那屏风来。
苏厉顺着荆轲的话语和视线,也仔细看了看他身后那屏风,只见那屏风上所画之物极其简单,只以水墨寥寥数笔,画的不过一个头戴蓑笭的老者,横跨在一头黝黑水牛的脊背之上,好不悠哉快活。
苏厉得见此画像,才明白了过来,于是便不紧不慢地答道:“此乃苏某的义兄苏代。先前曾在燕国专心事燕,后因喜好田园生活而辞官归隐,从此不再与官场来往。为了一解兄弟之间的思念之情,他临走之时,我命画师简单画了他的一副画像,至于后堂的屏风之上,闲来无事之时可解忧思,却让荆使见笑了。”
“哦,原来如此。”荆轲便听着苏厉的话,边不住地点了点头,只是脸上的表情还在陷入沉思之中。
荆轲为何独对这寥寥数笔的墨画感兴趣,那是因为那画上之人太像之前他遇到过的那个游牧放牛老叟了。而且此时那老叟曾料定魏国此行定有一番波折,临走之时曾有一言:乱纲谁为主?御前第一人。现在荆轲细细想来,他这话说的可不就是邹爽祸乱魏景湣王之事吗?这老叟虽远在魏大梁百里之外,却能洞悉这魏国所发生的一切,岂非世外高人?所以这才引起了荆轲这般聚精会神的细想。
“那家兄定是位能通天理的世外高人。”荆轲细想过之后,又继续接着点头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