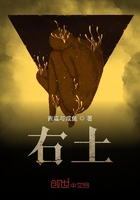十三阿哥临走前居然真的帮闵敏带来了几本书,杂剧、笔记、小说、辑略……居然什么品种都有,更稀奇的是特别带了一本纳兰容若的词集,和仓央嘉措的诗抄。
“听说你对那藏人的诗是另眼相看的,爷帮你弄来这本真是不容易,想来纳兰的词你估摸也喜欢,就一并送来了。”十三阿哥如是说。
闵敏却是一肚子莫名奇妙,现在自己这处境,去读那些咏春叹秋的词,算什么?
然后,上次批了一顿仓央嘉措,怎么就算是另眼相看了呢?阿哥们的脑筋倒底是怎么长的。不过还好,十三阿哥带来其他一些书也算有趣,而且明清时候的书辑也接近半文半白,加之多日来御书房熏陶,闵敏也能看的津津有味,甚至用碳条加了批注,日子竟过的格外轻松惬意了。
不知不觉,就到了九月,忽然称心就跑来了:“姐姐,姐姐。”
“称心?你们回京了呀。你,怎么这样急?”闵敏极少见着称心这样慌慌张张的样子。
“姐姐,这趟出巡,真是出大事了。”称心神色复杂,“我先不和你细说了,师傅让我快马抢在前头回来,让你收拾两间屋子,弄干净就好,太子回京之后,怕是要先住在咸安宫里。”
太子要住在咸安宫?
是了,自己日子太好过,竟完全忘了一废太子这件大事!
那么太子是废了吗?称心依旧口称太子应该是还没有废,所以是先禁足吗?
可是,为什么要放在咸安宫呢?
不几日,太子就被押着来了。
见往日里被倨傲和忐忑拉扯的趾高气扬的他,而今如同一只被遗弃的小猫一样落寞,即便是如闵敏这样置身事外的人,瞧着都觉得有几分可怜。默默地去小厨房里准备了一些吃食送过去,却被落了一顿好心当做驴肝肺的数落,甚至还被他砸地上的碗的碎片,割伤了脚踝。本想回屋里去处理伤口。可是天气阴沉,屋里实在太暗,幸而看守的侍卫都在门外,就挪到院子里,岂知四阿哥和十三阿哥竟来了。
“贝勒爷吉祥,十三爷吉祥。”闵敏一只脚只穿了袜子,还褪到脚心处,露着脚踝,伤口尚未止血,如此站在地上行礼,真是尴尬极了。
“起吧。”四阿哥面无表情,似是完全没看见闵敏的狼狈,“我来看看太子殿下。”
闵敏拿不准康熙把太子放在咸安宫,是让人看呢还是不让人看,不过既然门口的侍卫都放他们进来,自己也只得了照顾太子的吩咐,也就随他们吧:“回贝勒爷,太子殿下心情不好,也没吃什么东西。先头发了些脾气,这会子安静了,估摸是累了歇下了。”
四阿哥似乎没有预料到闵敏回答的这样仔细,看了一眼闵敏的伤口,忽然朗声道:“太子既累了,那臣弟就先回了,改天再来吧。”
四阿哥话音未落,门吱呀打开,须发零乱、眼眶发黑的太子出现在门口。
四阿哥看了一眼十三阿哥,独自进了屋,关上了门。院子里只剩下十三阿哥和闵敏。
“你别站着了,赶紧止血吧。”十三阿哥道,“这样血淋淋的也不知道忌讳,不怕冲撞了主子。”
闵敏脚踝的伤口因为伤的不巧,口子还挺深,站了一会儿已经有些疼的发麻,心里只觉得委屈:“爷说的,好似奴婢故意要这样惹爷生气一样,若是冲撞了主子,责罚便是。”
十三阿哥摇摇头:“四哥和太子估摸要说一会儿话了,你还是先处理好伤口吧。”
躲开十三阿哥递过来的手,闵敏踉跄跌坐,用湿布清理伤口。
十三阿哥见桌上两只小瓶,一只小的应是金创药,另一只不知是什么,拿起来一打量,竟是一壶酒。
闵敏清理了伤口,从十三阿哥手上拿过酒壶,倒在另一块干净布上,给伤口消毒。这湿了酒的布,一按到伤口上,便痛的闵敏倒抽了一口冷气,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嘶”。
十三阿哥这会儿倒通情达理起来,只是眉心皱了皱,没有说话,等闵敏上了药包扎好伤口,又穿好鞋袜之后才问:“你这是怎么弄的?”
闵敏心里头正觉得委屈,抬头见十三阿哥神情温和、双眸之中似有怜悯之意,一时恍惚竟忘乎所以,把午间自己如何好心预备了吃食,给看来疲累不堪的太子送去。谁知道太子却称自己这么个下三旗的奴才,别以为进了御书房就飞上枝头了,他堂堂太子尚未传膳,一个低贱奴婢居然自作主张,又是如何砸了盘子,又是如何被飞溅的碎片割伤了脚腕。
十三阿哥静静听完,叹了口气道:“魏珠不是一直夸你谨言慎行的嘛,这么这件事做的这样冒失。里头的可是太子啊!虽是一时圈禁,但终究还是太子,怎么轮得到你这个奴婢可怜。我也听说你御前伺候,有时不经皇阿玛旨意就传膳,那是皇阿玛信任你,魏珠才由着你,对太子怎么可以一样。况且太子如今心情不好正无处宣泄,你不是正好吗!”
闵敏心里越发火了,但是也知道十三阿哥说的不错,只得强忍了怒气,委委屈屈地回话:“十三爷教训的是,奴婢下次不敢了。”
十三阿哥哪里听不出她话中忿忿之意,正要说话,门又开了,四阿哥出来道:“传膳。”
闵敏愣了愣,应了声,便一瘸一拐的去了小厨房。
送走了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到了晚些时候,一直跟着太子贴身伺候的两个宫女太监由称心领着过来咸安宫,说是奉旨照顾太子。闵敏心里算松了口气,随即又被称心拉过一边说话,道是魏珠问,闵敏打算几时候回御前。
闵敏心知魏珠未尝不是以此试探,按照自己这个未来人的印象,太子这场风波几时候才能过去。看着称心一脸若有似无的期待,忍不住有些叹息,或许魏珠有着为康熙担忧的这份心,称心应该是完全出于对自身的考虑了,或许有一些是为魏珠的,毕竟主子们不顺心,倒霉的还不是近身的奴才。只可惜,这场看似轰轰烈烈的回銮,不过是一场大戏的序曲,后面刀刀见血、拳拳到肉的高潮,还远着呢。
称心和闵敏相处颇久,见她脸色沉沉眼光流转又沉吟不语,便知情况不妙,原先有些期待的眼神,也变的忧心忡忡起来。
闵敏抬眼,便见他一副欲言又止的尴尬样子,便知自己必须说些什么才行,于是把称心拉过一边,避开一应侍卫和闵敏所知大阿哥及四阿哥留着的人,低声道:“你回去告诉师傅,再大的风雨也总有过去的时候。最是吓人的,其实还是看起来相安无事,暗里头却汹涌澎湃。”
话一说完,闵敏又觉得自己好好笑,接着说:“这些浅显道理,师傅哪里需要我来告诉,倒显得我班门弄斧了。你且回师傅,我几时回御前伺候,这件事怕是师傅都拿不了主意的,我想,到了适合我回去的时候,万岁爷自会传我。”
称心的神情并无太大的意外,似是一切状况都早已了然,他道:“嗯,我会好好回师傅的,你也要好好照看自己。我原想让师傅为你指点一二,师傅却说,像你这样心里清明如镜,什么都看的通透,何必要他关照,一定早知如何自处。”
闵敏苦笑了一下,魏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我即便知道如何自处,也是平日里师傅教导的好,你让师傅放心,谨言慎行四个字,我是定然不会忘记的。”
称心点了点头,又去张罗了一番,便走了。闵敏瞧他带来的人,被先头留下的两个太监轮流在盘问,心里便觉得应该真的是太子身边得力的人。回忆起来,大阿哥是最想要拉太子下马的,怕不是他的安排,四阿哥此时还是太子党,莫非是他想送几个体己的人进来,才能好好照顾太子?
也难为他这番心意,只希望太子要把这份善意放在心里,莫要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了。
自打太子被圈禁在咸安宫,闵敏就避去了后头的偏院。想来幸亏以前喜欢躲在这里,所以有认真收拾过,所以现在少许打扫就好了,真正是有种身居风眼的平静——闵敏自嘲着。
这天,又在后头读书,手边只剩下了纳兰和仓央嘉措的集子还不曾读过,便趁着好天气坐在台阶上翻看,正翻到纳兰容若的蝶恋花·出塞,翻了几页只觉得这首还算勉强可以读懂,便小声念了出来:“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网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你喜欢这阙词?”
闵敏正在尽量揣摩这首词的意思,冷不防身边一个声音忽然响起,抬头一看,竟是四阿哥。
“四贝勒爷吉祥。”匆匆站起行礼,腹中自然少不了一顿埋怨,怎么都没有生息,是要吓死活人吗?
“起吧,”四阿哥竟难得和气,“你还没回话。”
闵敏低着头道:“也不是,只是纳兰先生的词,只有这首,还能勉强读懂?”
“哦?”四阿哥道,“十三弟说过多次,你虽文理粗浅,可亦有引经据典的能耐。加之你在御前熏陶已久,怎么会只能勉强读懂这首?”
“回四贝勒爷,奴婢自从四十二年一场大病,之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反正只要有人提到旧时,闵敏已经连脑筋都懒得动,直接就说自己失忆,“御前侍奉也只是学了帖注而已,所以这些书,都是奴婢半蒙半猜的。”
“那你且说说,这句金戈铁马,青冢黄昏路是什么意思。”四阿哥揽了衣服下摆,坐到了闵敏方才坐的位置。
闵敏愣了愣,自己勉强读懂的意思是,还在勉强,尚未读懂啊!怎么办,未来皇帝不好得罪,只能硬着头皮回了:“奴婢并没有十分明白,大约和折戟沉沙铁未销差不多意思吧。”
“你竟知道这个!”四阿哥有些惊讶。
“只是不知道哪里听人说过罢了。”闵敏低着头回话,她说的是实情,确实只记得这一句而已。
四阿哥静静看着闵敏,许久才道:“十三弟还说过,你是个能说几句话的。”
“四贝勒爷有什么吩咐?”闵敏恭恭敬敬。
“皇阿玛下旨了。”
“啊?”闵敏被这没有没尾的一句话弄的莫名其妙。
“皇阿玛要废了太子。”四阿哥两眼放空,不知道看着哪里,“一会儿就要差人过来了。”
闵敏看着四阿哥,一肚子狐疑,太子被废,对于四阿哥来说难道不是好事吗?
“你这样看着我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个结果应该正中爷的下怀?”四阿哥不满闵敏打量的眼光。
闵敏赶紧扑通跪下,膝盖有点疼:“奴婢不敢。”
“那你是什么意思?”四阿哥的声音阴森起来。
“奴婢,奴婢只是觉得,这样的大事,奴婢怎么说得上话。四贝勒爷和奴婢说,似乎,似乎,似乎没什么用。”闵敏低着头回话。
又是沉默,难堪且让人窒息。
过了许久,有一个小太监跑过来,对四阿哥一阵耳语,四阿哥才道:“起来吧。”
闵敏还没来得及谢恩,四阿哥就拂袖而去。
起来揉了揉膝盖,闵敏看着四阿哥的背影,竟然觉得他因为废太子这件事似乎是真的不开心,难道他是货真价实的太子党?不像啊,好像四阿哥培植自己的幕僚也不是一朝一夕的,难道只是为太子谋划?
闵敏觉得事情好复杂,想着想着头都疼了,还是由他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