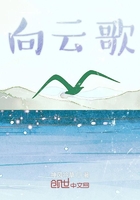一切声音消失殆尽,白茫茫的天地瓦解。他的眼前朦胧出现了一个影子,耳边模模糊糊传来两个人的对话声——
“先生,你看额头这里补得还行吧?”
“唔,还行。”
“他身上这些烧伤的地方,用刚死的人皮补还是用快死的人皮补?”
“……随便。”
“先生啊,他这张脸拉小点吧,这样好看。”
“随便随便随便……!蛛匠你告诉我你话怎么那么多,你到底是手多还是嘴多?!”
“……回先生,我有六只手,一张嘴……”
“……”
白冥莽有些艰难地睁开眼,入眼是一张很模糊的大脸,但他依稀辨得出这张脸不属于人类。奇怪的是,他没有被吓得惊叫起来,若是以前,他不会这么淡然地看着一张非人类的脸离自己那么近。
白冥莽缓了缓,慢慢地想起了发生的一切,心里猛地一痛。
……不是已经死了么?为什么他还活着?
“呀,先生,他醒了!”蛛匠被白冥莽突然睁开的眼吓了一跳,扭头冲身后喊了一声。
“……是吗?我看看。”被称做先生的男人走了过来。
白冥莽尽力睁大眼,稍微试着动了下头,判断出现在是白天,他躺在一个树林的阴影下。开始说话的两个人,一个是被叫做先生的年轻男人,另一个是叫蛛匠的大号蜘蛛。
大号蜘蛛就是一只紫黑色放大版蜘蛛,身上茸茸的须毛清晰可见,有六只长长的腿,两只支撑着它的身体,两只拿着刀、线、药物等工具,最后两只在白冥莽的脸上比比画画。
白冥莽倒是很淡定地看着眼前放大版有些骇人的蛛腿,大蜘蛛似乎被吓到了,窜到男人身后去了,手里还捏着一根连在白冥莽脸上的线。
男人看了看白冥莽,说:“你先别动,你的脸上烧伤部分还没有补好。”
白冥莽把头转了回去,闭上眼。
男人在蛛匠头上一拍,说:“快去接着弄!”
蛛匠用两只腿捂住头,委屈兮兮地回答:“……我不敢……我怕……”
“废话多!快去!”
最后蛛匠还是老大不情愿忸怩着回到白冥莽身边,继续修补他的脸。
白冥莽感觉得到冰冷的针刺过他的脸,并且好像听到了皮肉被拉合的声音——但是他没有觉得痛,很清凉的感觉在他脸上流淌。
过了一会儿,蛛匠如释重负的声音在白冥莽头上响起:“好了。”
白冥莽睁开眼,看见大蜘蛛一下蹦跶到离他很远的地方。男人不知从哪里摸了一块镜子出来,举到白冥莽面前:“看看吧,蛛匠的手艺不错。”
镜子里出现了一张有些陌生又有些熟悉的脸,有些不像他自己了。相比起原来那张脸,这张脸要显得成熟稳重一些,比原来那种光彩夺目,引人注目,要平凡清秀得多。
白冥莽看着镜中的人,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
男人说:“你的脸有一半被烧伤了,身上也烧伤不少,我们就给你补了补,咳,顺便改了改。”
白冥莽并不看他,只是盯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你们救了我?”
开口才发现,他的声音很是沙哑,喉咙痛得厉害,像被烟熏火烤过。
“不算,”男人说,“救你的另有其人。”
白冥莽艰难地挤出一个讽刺的笑:“为什么要救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上凌宗已经毁了,他不指望谁有能力来拯救上凌宗。上凌宗对付不了的敌人,其他人也不可能对付得了。他亲近的人,他认识的人,都是生死不明。
男人没有在意白冥莽近乎嘲讽的语气,他笑了笑,手指在镜子上轻轻一点,又重新举到白冥莽眼前:“你可以看一看,看了你就有自己的答案了,活着或者死去。”
镜中一道白光闪过,远远的,暮云叆叇,出现了庄严肃穆的建筑。白冥莽看着,死寂一般的眼中,终于生起了波澜。
时间在九大宗门来的那一天开始,上凌宗的弟子被人悄悄杀害,植入一团黑烟,他们“醒来”后,像活死人一样攻击上凌宗的其他人。每个长老、师傅、领事,最先遭毒害。白冥莽的父亲白冥容,在关键时候内力尽失,被那只巨大的怪物一口咬掉头,身体甩进燃烧的火堆。美丽温婉的栀夫人,为了救他,失去双腿,被俘回席禹教。他最亲近的朋友,风主,被冗为所杀,尸体拖进火光冲天的宗祠。七哥带着姬元古四处躲避逃跑,身中乱箭。最后不得已,七哥抱着姬元古,纵身跳下上凌宗后山的断崖。
上凌宗的建筑被疯狂地砸毁,珍宝被掠夺一空,珍藏的上凌宗武功古籍、修行内力秘籍都被人群抢走。拼命反抗的上凌宗弟子被大肆屠杀。那些人把尸体堆起来一起烧掉,受伤但还没有死的,也被活生生扔进火里。他们在火中哀嚎着,面孔扭曲绝望而痛苦。那些残忍的刽子手,以听到凄厉的号声为乐,他们大笑着,相互庆祝。
上凌宗里上万的人口,只剩下一千不到。所有的建筑都被烧毁、砸碎。
最后那些人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大火掩盖住上凌宗。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剩下的只有满地尸骨话断壁残垣,疮痍满目,令人触目惊心。
所有他认识的人,都死了,只有他,苟活下来。
男人收起镜子,说:“你也看过了,如果你想死,没有人可以阻止你。如果你想活着,就向北走。”
他转过头,对一旁的蛛匠说:“蛛匠,我们走吧。”
“哦哦。”蛛匠稀里糊涂地点了点头,有些不解。
先生一大早就把他喊来救一个人类,这会儿这么快就走了?不过他还是挪动着六只腿跟着男人身后。
走了几步,蛛匠听见一阵很压抑的呜咽声从后面传来。他好奇地转过头,看见那个仰面躺在草地上的少年,一只手臂横在眼睛上,浑身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蛛匠奇怪地用一只脚戳了戳前面的男人,小声说:“先生,他好像哭了。”
男人没有停下脚步,甚至连头都没有回,只是淡淡地说:“不用管他,走吧。”
蛛匠最后看了一眼那个孤独还有些瘦弱的少年,蹭蹭地跟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