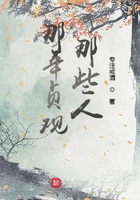“还好是白天生的,要是夜里生的,岂不是得叫夜里赐?”车内传出一道揶揄。
李德贵愣了愣,随即哑然失笑,心说这位公子就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再好的话从他嘴里出来都要变个味道,摇摇头接着说道:“白天赐刚出娘胎,白老爷就迫不及待的探查他的灵脉,结果你猜怎么着,白老爷差点没高兴的晕过去,此子竟然是独灵脉,并且还是最强的雷属性变异灵脉。”
“上天赐下这么一个宝贝,白家自然是倾其全部财产竭尽全力栽培。白天赐也没有让白家失望,十四岁就达到了大劫九重境,修炼速度仅比神剑城当代天才剑追云慢一年。啧啧,真是了不起啊。”
“今年年初又有消息称,白天赐轻松通过神剑城的考核,等春季学院开学,就能去神剑学院进修。神剑学院啊,多少人挤破脑袋连学院大门都看不着一眼,他竟然轻轻松松通过了考核。啧啧,多了不起啊。”
“老李头,你知道大劫九重境是什么意思吗?”车内的人笑问道。
李德贵闻言一愣,然后尴尬的挠挠头,咧嘴道:“俺一个赶车的,哪懂这些啊。不过大家都说白天赐是个天才,想必大劫九重境应该很厉害吧。公子,您知识渊博,给俺说说。”
“十四岁达到大劫九重境确实是个天才。不过——和剑追云比,差的可不是一年。”
“那差多少年?”李德贵好奇问道。
“一千年。”
“啊。一千——一千年。公子,您又开玩笑了,谁能活一千年啊。”李德贵笑着摇头。
“哦,对了,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李德贵突然想起一件事,顿时把白天赐和剑追云差多少这个疑惑抛到了脑后,压低嗓音道:“白无尽,哦,就是白老爷,其实有两个儿子。除了白天赐还有一个大儿子,叫白云辉。白云辉和白天赐是一个爹妈生的,但是你们打死也想不到,白云辉竟然是五脉尽漏之体,也就是不能修炼的废物。哎——”
说到这里,李德贵禁不住叹了口气,道:“白无尽也真够狠心的,明知大儿子白云辉不能修炼,还偏偏给他吃了颗三级妖兽内丹,强逼他修炼,结果白云辉经脉寸断而亡。死就死了吧,或许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可是白无尽觉得白云辉这个废物是白家的耻辱,不准他下葬,竟把他扔进乱葬岗,任由野狗撕食了。”
“你们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还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白无尽怎么就下得了手呢。”
“还有他那个夫人,据说现在天天吃斋念佛,每个月月初还会施粮救济穷人,说是忏悔赎罪。依俺看,纯属惺惺作态,哦,现在知道忏悔了,当初干什么去了。要是俺这么做,俺家那黄脸婆准把俺活撕了。”
“虎毒尚且不食子,人难道比畜生还不如么。哎,世态炎凉,人心难测呐。”
“老李头,稳着点,颠的公子没法练字了。”车内突然响起一道清脆的叱喝,打断李德贵的感慨唠叨。
李德贵忙歉声应道:“公子,对不起对不起,俺走神了。您接着写,俺保证比坐在书房里还稳当。”
“呵呵,没事,不怪你,这个字我手生,所以才没写好。”车内笑应道。
车厢里左手侧,许宁半躺在舒软的兽皮座里。说是座,其实宽敞的像张床。他虽然出生在魏王府,自小穿金戴银,过荣华富贵的生活,却还是头一次做这么豪华高档的马车。
听到丫鬟柳依的娇嗔埋怨,许宁不禁好奇的放下书卷,看向坐在对面习字练笔的许雷,发现许雷手中的毛笔果真在宣纸上点出一个大大的墨点,表情不由得诧异起来。
通过五个多月的相处,许宁对许雷的脾性多少有些了解。这人情感丰富,对什么事都感兴趣,但基本都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唯独两件事他一直很认真。
第一件事,花钱。好家伙,那是有多少花多少,一点都不带心疼的。往往都是许雷在前面大手一挥,许宁在后面泪眼汪汪的掏银子,因为这些银子都是他扒着手指头,扣着脚丫子,一个子一个子赚的。
第二件事,正是许雷现在做的,习字练笔。
每当翻开书卷,拿起毛笔,许雷脸上的那股认真劲都会让许宁自叹不如。
无论多么深涩难懂的字,只要许雷听一遍,就能牢牢记住,比用刀子刻在脑子里还厉害。
另外,许雷写出的字都是一笔一划,极为工整。只要他提起笔,就算是地动山摇,他也能在纸上工工整整的写出来。
这份笔力让自幼提笔练字的许宁自叹不如。
所以许宁看到许雷的毛笔在纸上点出一滩墨点,感觉极为诧异,这可是破天荒头一糟。
许宁瞄了眼许雷的表情,然后若有所思的把目光移回书卷中。
丫鬟柳依揭掉染墨的宣纸,给许雷换上一张新的。
许雷重新提笔,可心中烦躁挥之不去,且距白岩城越近,烦躁感就越强。皱了皱眉,知道今天是静不下心来练笔了,于是将毛笔担到笔架上,朝跪坐在对面认真磨墨的柳依笑道:“柳依,好久没听你唱曲了,来一曲。”
柳依诧异的抬起头,因为每天这个时候许雷都要练笔,雷打不动。可今天才仅仅写了二十六个字,竟放下笔要听她唱曲,很明显有问题。
不过柳依很快收起心中的疑惑,这不是她一个奴婢该想该问的事情,遂眨动修长的睫毛,嫣然笑道:“公子稍等,待奴婢把东西收拾干净。”
“恩”许雷点点头,往后撤了撤身子,慵懒的倚在车窗上。
柳依将纸笔砚墨收拾干净,从行李箱里拿出一架古筝,放到许雷写字的小木桌上,然后跪坐下来,向许雷问道:“公子想听什么曲子?”
“随便。”许雷回道。
“那奴婢唱一首《阿斗三戏秋娘》,给公子解闷。”说完,柳依葱白玉指勾动筝弦,婉转圆润的腔调从白齿红唇间飘出,轻缓时如溪水潺潺,欢快时如黄莺出谷,曲美人更美。
自许雷懂得用男人的目光审视女人,至今为止只见过两个能让男人怦然心动的女人。第一个是咬走他初吻的娇蛮公主李幕焉,第二个便是眼前的柳依。
同样是倾国倾城的容貌,但是如果问许雷哪个更好看,许雷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柳依。
因为李幕焉的美太过骄傲了,她的骄傲不是仙子那种清尘脱俗,不食人间烟火,让人不敢亵渎,而是身份与地位高高在上的骄傲。和她站在一起,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长相配不配得上她,而是要考虑自己的身份地位够不够格。
简单点说就是,和李幕焉站在一起,会让人产生身份地位的自卑感,没几个男人喜欢这种感觉。
而柳依完全不同。或许和她呆过的地方有关,她的声音、眼神、动作都带着勾魂的妖媚,同时又是一副柔柔糯糯、任君采摘的小女人姿态,绝对是男人金屋藏娇的首选。
许雷听着曲子,心中的烦躁丝丝抽去,禁不住暗赞柳依生有一颗玲珑心,只看不问就知道什么曲子能解他心中烦闷。
柳依是他三个月前途径二级主城沧洛城,从城里最有名的青楼里偷来的花魁。
这柳依倒也奇怪,许雷把她从青楼里偷出来,她不惊不惧、不哭不闹也不跑,而是留了下来,并以奴婢自称,贴身伺候起许雷。
许雷虽然从未问过她的来历身份,却也能瞧得出此女出生不简单,无论谈吐还是举止,又或是学识才艺,都不是普通人家女子能具有的。
柳依不说,许雷便不问。柳依已奴婢自居,许雷便已主子的身份享受。
倒是许宁忍不住问了几次柳依老家哪里,可每次柳依不是含糊其词,就是不吭声的掉眼泪。
问不出个所以然,许宁索性就不问了。谁心里没个不愿告人的秘密,何必非要残忍的把人扒得赤条条的放在阳光下晒呢。何况他自己不就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不敢让任何人知道么。
将心比心,许宁觉得柳依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可怜人。
说到秘密,许宁恨不得撬开许雷的脑子,看看这货是不是早把他敏感的身份忘得一干二净了,不然为何走到哪里都要出风头,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呢。好似生怕别人发现不了他是魏王的儿子似的。
一曲唱罢,柳依见许雷似乎倚在车窗上睡着了,她没有叫醒许雷让他换一个舒服的睡姿,而是扯过一旁的绒毛毯轻轻的盖在许雷身上,然后收起古筝和小木桌,走到许雷左手侧,后背依着车壁坐下,双臂环膝,头埋在修长的双腿里,像只受惊的小兔子蜷缩起来。
……
正午时分,一辆豪华气派的六驾马车出现在了白岩城的城门前。
守城官兵顿时为之动容,忙扔掉面前两个背着大包小包,费了一堆口水也没榨出几个子的贱民,脸上堆起如春风般温暖的笑容,屁颠屁颠迎了上去。
乖乖,这么豪华的马车,白家白老爷的座驾也没这么威风呀。不知是哪里来的达官贵人,赶紧过去伺候起来。如果讨得车里的老爷太太公子小姐高兴,随便扔俩赏钱就够我们吃好几个月的花酒了。
几人眼珠子放光,就跟白花花的银子已经揣进他们口袋一般,心里那个美哟,都要冒鼻涕泡了。
然而驾车的马夫竟然鸟也不鸟他们,甚至经过他们身边时还扬起鞭子狠抽了下马屁股,马车呜的一声从他们面前呼啸而过,卷起漫天尘土灌了他们一嘴。
几人赏钱没讨到,却讨到一嘴的灰尘,大眼瞪小眼了一会,旋即面如猪肝的瞪向来往的行人,欲找一个好欺负的宣泄心中的怒火。
“呸!一群看门狗,就他娘的知道欺负穷苦老百姓。穿了一身狗皮,就他娘的忘记自己是人了。”李德贵甩着马鞭,斜着白眼珠子骂骂咧咧,不过很快他就咧嘴笑了,挺直腰杆使劲甩了两个鞭响。
要不是怕车里的阔少爷不高兴,他真想调转车头,在城门口进进出出跑一天,喂这些逮到穷人就勒索进城费,遇到达官贵人就伸舌头摇尾巴的哈巴狗吃一天的灰尘。
“公子,白岩城到了,您想去哪里落脚?”李德贵嘴上虽然这么问,可他的眼睛早已四面八方的乱瞟了,寻找白岩城最气派的酒楼客栈。
果不其然,许雷应声道:“听说白岩城最好的酒楼是落仙阁,去见识见识。”
“好嘞,落仙阁。”李德贵使足了劲吆喝了声,顿时引来许多目光,他立马抬头挺胸直腰,享受每一道目光的注视,直至老腰挺的发麻了,他才放缓车速,道:“公子,俺也是第一次来白岩城,等俺找个人问问落仙阁怎么走。”
不料许雷应道:“一直往前走,中心路口左转,右手边第三家就是。”
李德贵愣了愣,随即恍然笑道:“公子原来来过白岩城啊。”
车内,许宁再次放下书卷,掀开车帘看了窗外一眼,然后又转头看了许雷一眼,直觉及对许雷一路的观察与推测告诉他,许雷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这个故事即将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