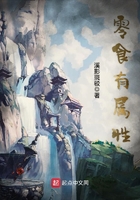我醒来的时候,屋子里亮着灯烛,窗外的天已经黑尽了。我只觉得身后还有些疼。莫离那一下使足气力,那一击下来足够我睡下好几个时辰了。
我想坐起身来,可是被点了穴道,根本动弹不得。只能在视线所及范围内看着这屋子里的布置,想确定一下自己现下是在何处。
屋子的墙角没有盆栽,但是却有一处小榻,榻上放着小火炉,小火炉上放着玲珑剔透的小壶,炉子旁边放着三两个茶色的瓷碗,因为太长时间无人问津,所以上面落满了灰尘……晚风吹过,顺着半扇未关的窗子看出去,几棵竹树倾斜着,竹叶飒飒作响……
百草轩……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又进来了这间曾经让我觉得有家的温暖的地方。
下雨的时候,我和禾回坐在那小榻上,燃着火炉,煮着茶,听着雨声。那些岁月已经泛黄了,可在我的脑海中却仿似在昨日。
灯火跳动一下,我方才注意到落地帘帐上的一抹影子。
我静静闭上眼睛,淡淡道:“莫离,我知道你在!”
茶杯被放在桌子上的声响跟着打破夜的寂静。我听到他的脚步声慢慢靠近,目光落在地上,追随着那白色的长袍袍脚。
他走到我床边的时候,我撇开头看着里面。床帐被摘了,我只看到有些斑驳的墙壁,那里还有着细细的裂纹,只是很细微,不仔细看便不易察觉。
“你醒了!”莫离的声音中满是疲惫,想是送我回来之后一直守在这里。
我无甚起伏道:“放开我!”
莫离坐在床边,声音清冷:“放开你,让你去送死吗?”
“我要救她,我不能让琴弄杀了她……她可是禾回在意的人……莫离,你不知道,你还什么都不知道……”我一边同他说着,一边暗暗冲着穴道。
“你连自己都救不了,又怎么去救别人?你以为琴弄就那么随意下山了吗?玄月说,他可是见琴弄从云间阁出来的……就算你斗得过琴弄,你又能奈何得了宗主吗?”
“我只想下山,只要一下山,我就可以寻到那个人所说的锦囊,或许那里面真得有血蛊的驱除方法,那样一来,我就可以离开悲鸣……”我说得激动,低吼道,“我要查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不能言而无信,不能放任琴弄将拂音杀死!”
“还是好好担心一下你自己吧!”另一个声音从窗外钻了进来,“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才能不这么任性呢?”
默了一会儿,又道:“右使,你还是把她放开吧!省得她日后又因为这件事情记恨你!她的脾气真是越来越差了!”
莫离叹一声,竟然真得将我的穴道解开了。
我方一转身坐起来,便看到窗边落下一袭红影,他正坐在那里摆弄着他那把玉箫。
我正要说话,他却抢先开口:“先别急着骂我!你可知道,你今天的举动已经传到宗主耳中了吗?你也不想想,那么重要的犯人,琴弄明明知道和禾回有关,还让你靠近是为什么?人家就是等着挖个坑,让你往里跳,让宗主看看他一向纵容的左使,完全可以因为一个死人背弃他!”
我坐在床边,没有说话。
我真是一时急昏了头,心中只想着禾回和拂音,竟然没有仔细想过这背后的牵连。
当初丢了入山令那么大的事情,琴弄都可以免于责罚,定然是宗主没有追究。那便是说,这整件事情宗主都是知情的,甚至是他让琴弄这么做的?
“你以为宗主眼瞎耳聋吗?你在悲鸣这么多年,可曾见过哪件事情是能瞒过他的?知不知道你的自以为是已经害死了那个尘灭!”非欢走过来,站在莫离身边,瞧着我,“你下山之前要不要看看他?他可是因为你被活活扒了皮,现在挂在南山山门由你的两个好下属守着呢!”
尘灭……被活活扒了皮……不可能,不……
非欢勾唇冷笑:“别那么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我很容易理解为你第一天认识宗主!”
我抬头看向莫离,莫离对我点了点头。“过缘,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悲鸣比你想象得要可怕很多!”
我倒吸一口冷气,眼睛一闭,便是尘灭血淋淋的模样……若莫离当时没拦住我,想必挂在那里的人就是我了。我怎么忘记了宗主是怎样的人,我怎么会因为他曾对我温柔,他曾对我微笑,他曾将我压在身下,就忘记了他是一个杀人魔头的现实呢?
我怎么会忘记了……自己从一开始便是他的提线木偶,是他满足私欲的杀人工具!
我失了力气,瘫倒在床栏杆处,窗外的风吹进来,我只觉得冰寒入骨!
“右使,夜深了。我们两个和宗主的女人共处一室,似乎有些不大合适!”非欢万年不变的嘲弄口吻,今日听起来忽然觉得字字珠玑。他总还是那么放荡不羁,一副无所事事的无赖模样,可是他却比我们都清醒,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身份,而且总是那么冷静!
他总说我意气用事,我总骂他没心没肺。可他却说,在悲鸣生存,没心没肺才是最保险的,因为永远不会被抓住软肋……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将禾回从我的生命中抹去,所以我这辈子身不自由,心也不会自由,天大地大,哪里都是我的囚笼。
“过缘,你……”
非欢打断他,“好了,让她自己想想吧!”
说完,便推搡着出门去了。
“霖零,你去烧些洗澡水,让左使洗个热水澡!”
“是,非欢大人!”
“还有,她那个样子应该是吃不进饭去了,你随意煮些粥温着,等她饿了,也好应付!”
“好。”
“还有,没什么事情别去烦她……”之后不知道又说了些什么,声音刻意压低了,只听到霖零连声称是。
没过多久,便听到百草轩的门被关上了。
“霖零!”
那小婢女听到我叫她,慌忙进来跪在外间,颤声道:“左使有何吩咐?”
我看着天花板上的影子,无力道:“把灯烛熄了!”
“是!”话语刚落下没一会儿,整间屋子就陷进了黑暗之中。
“左使还有别的吩咐嘛?”
“我累了。明天不用叫我。”我躺在床上,盖上被子,闭上眼睛,“从现在开始无论谁来百草轩,一概不见!”
“是!”她应承一会儿,正要关上门时,又轻声加一句,“属下就在门外候着,左使若有吩咐,随时唤属下就好!”
“嗯,”我一边应着一边习惯性地去落帘帐,可是却什么都没摸到,方才记起帘帐暂时没有,便又道:“我喜欢紫色的东西,若是那帘帐不能用了,你便去茗雪那里领新的来。从今往后,百草轩的家务事你全权管理,不必再向我汇报!”
她默了好一会儿,才应道:“是!”
我知道她是不相信现在我会是如此的好脾性。
“你一有时间就去学做饭菜,以后在悲鸣,我只吃你做的饭菜!”我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黑暗,可是眼泪依旧沿着面颊滑落,“我不喜欢肉食,你尽量多做些素菜……”
“是,属下记住了!”
“就这些。”我拉过被子胡乱抹着眼泪,“我睡了!”
“好,左使好生歇息!属下告退!”
……
我胡乱揪着自己的头发,拍着自己的头,可是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死在我剑下的那个人,还有禾回坟茔中的空席子,再有便是尘灭脸上的那块疤痕,那疤痕被撕裂开,然后一点点扩大,露出里面的新鲜血肉来,最后整张面皮全部被揭了下来,尘灭一阵惨叫,声音在我耳边一圈圈回响……我心里想着他被挂在南山门上的尸身,胃里就一阵翻江倒海,起来时候吃得那些东西消化的差不多了,没什么可吐的,便吐出酸水来……我撑在床边呕着,到最后感觉要把自己的心肝脾肺肾一并吐出来。
那不是我的真心,我是想保护他的,却没料到我竟然亲自将他推向了死地。
他还那么年轻,却被我轻易葬送了。
他在牢洞中呆了那么久,都不曾见谁被施以这种悲鸣不准随意动用的刑罚,可到最后自己却成了这残酷刑罚的祭品!
我现在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也是琴弄早就预谋好的,明知道我会去牢洞,却还让尘灭出现在我面前,还刻意提供机会让他将那些事情告诉我……
他此次下山是奉了宗主令,几年前布的局今日才开始下,这到底是怎样一场棋局,竟然能够让宗主这般上心?南华蛊术派系多得是,这烬阙又因为什么而令悲鸣如此大费周章?当初禾回去了南华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又怎么和拂音在一起了?那拂音又是谁,既然和禾回之间有那么重要的约定,又为什么只派一个属下来,而自己却不亲自来寻禾回呢?
这些疑惑,像是一块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
我不可能守株待兔,坐以待毙。为今之计便是想出下山的办法,琴弄已经寻到烬阙所在,又走得如此着急,想必要不得多少时日,便能找到拂音,以琴弄的手段,也不知拂音是否能敌得过他。倘若这拂音一死,那这些事情就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死结!
怎奈我现在越是着急想出办法,脑子里就越乱,根本理不出头绪来。而且不知为何,我觉得自我方才运功试图冲开穴道之后,便觉得自己浑身无力,刚才一想这些,头也跟着疼了起来。
我只以为是我动用了无生卷中功夫的缘故,一时之间没能调息过来,所以才会如此,便不再多想,想着或许明天早上一觉醒来,便会好些。可是还没躺一会儿,便觉得肚子也跟着疼起来,好像有一股气在那里腾挪,一下下撞击着我,我手抚在肚子上,这一碰便是一惊:哪里是真气紊乱,分明是有什么东西在我肚子里乱动,那东西一起一伏,一重一缓,痛得我只想打滚。
我这才觉得恐惧!
纵使我再如何愚钝,也猜到了那东西是什么。
潜在我体内多年的血蛊,终于被唤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