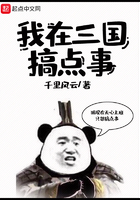尽管没有立即将整支队伍都集合起来,但考虑到奥拉夫二世的军队很快就会到达并对西居尔的据点展开突袭的事实,卡努特还是派出了信使,让战士们在附近的庄园里聚集。
当天晚上,尽管慷慨的主人毫不吝惜的拿出酒肉盛情款待,卡努特和他的战士们却都吃得很节制。面包熏肉和鳕鱼自然是吃了个饱,酒却没喝多少。
吃饱之后,一群人又在由仓库改成的大厅里闲扯了一会,便在大厅里纷纷入睡。只要等到奥拉夫二世和西居尔的残兵火拼之后,他们就可以顺势将胜者拿下,完成征服挪威的战争。
朦胧中,卡努特又做起了同样的梦——在回到北地后,这还是第一次。
同样是那个温暖湿润,令人昏昏欲睡的午后。
同样是那间有着彩色玻璃窗、银烛台、大书架、精巧的高脚镶金小圆桌和令人心旷神怡的熏香气息的小屋。
同样是那个轻佻的、夸张得尖刻的女人的声音:“教子?托尼你一定是疯了——他只是个野蛮人,而且还不洗澡!你会成为整个君士坦丁堡的笑料的。”
然后,那个博学多知的学者、品格高尚的教士、温和谦厚的长者,那个被他叫做“爸爸”的男人,就带着他那一如往常的温和谦厚的笑容摆了摆手:“放松,爱娜宝贝儿,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策略。”
紧接着,尽管已经在梦境中听过无数次,再听到那个男人的话时,卡努特还是感到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完全同意,他只是个和他的族人一样粗鄙、肮脏而且愚蠢的野蛮人。但他对我有那么点用处。”
“这些野蛮人总是比较看重同族,而皇帝则很看重他们的武力。成为他的教父会为我在宫廷里赢得很大的便利,也会让我在教会里更进一步。”
“至于别人的嘲笑……那正好——那些野蛮人会用刀剑让所有人闭嘴,而他正是所有那些野蛮人中最野蛮的一个。”
自始至终,那男人都没有提“他”的名字,没有说“他”是谁。但谈话的两人,和卡努特自己,都很清楚他们在谈论谁。
只是个野蛮人而已,所有那些野蛮人中最野蛮的一个。
这就是他的“爸爸”对他的看法。
他以为“爸爸”爱他,也爱他的族人,一如父爱世人;他以为“爸爸”愿意教导他,也愿意教导他的族人,一如子为了为世人赎罪而流自己的血;他以为皈依就会被接纳,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而信主的罪人都会得到赦免,他们并无差别……
但是……
都是,谎言。
最后,当那两具白花花的肉体开始相互纠缠、碰撞,让暧昧**的气息伴随着压抑和放松的呻吟喘息弥漫了整间小屋之后,这个梦的第一段就结束了——在那神圣的冠冕和典雅的袍服之下潜藏着的,和他们这些野蛮人,并无差别。
即便是在梦中,卡努特也记得,当时自己强压怒火,一声不出,悄悄的从厚重的纱帘之后离开,假装自己从没去过那里。
而第二部分,则是在海边。
湿热的海风带着咸腥的气息,在整个大理石铺就的长堤上轻轻回荡,让所有人都昏昏欲睡。而他则走在那个人身边。
“为什么你又改变主意了,发生了什么事吗?”尽管卡努特的决定突然而且“毫无道理”,但那人仍旧和蔼可亲,丝毫看不出为此感到着急和气急败坏的样子。
因为我不想成为你愚弄和利用的对象。
尽管心里仍旧满腔怒火而且咬牙切齿,卡努特却仍旧一脸的愚蠢,或者说天真单纯。在经历了那一天后,卡努特突然成长起来,开始欺骗和隐瞒:“我只是有些怀疑……我们只是些北地野蛮人而已……也许,我并没有资格称为您的教子……”
这句话让那个人停了下来,看着卡努特。
“我的孩子。”
这个词不是在君士坦丁堡常用的轻快活泼的希腊语,而是更加庄重、严谨和正式的拉丁语。
“我的孩子,看来你也听到了一些议论。但是没必要在意。他们只是妒忌。”将双手轻轻地按在卡努特肩上,那人温和的笑着,“妒忌你能成为我的教子,也妒忌我成为你的教父。”
“可我只是个野蛮人……”说着,卡努特停顿了一下,“有的时候,我在怀疑,我们这一族还从来没有见过先知,没有出过圣人,也没有听过福音,也许是因为主也认为我们是一群不值得救赎的野蛮人?”
这句卡努特琢磨、准备了许久的话,让那个人也愣了一下。
皱起眉,那人思索了片刻之后,才缓慢的开口:“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
那人所说的,是《罗马书》里的一段,卡努特也学过。而那人在此引这一段来回答卡努特,他的意思,卡努特也知道。
但是,在那间小屋里亲耳听到那人对情人所说的话,亲眼见到他们的作为之后,再听到这样的话,卡努特只想发笑。
然后,卡努特就笑了出来——和他心底里的冷笑不同,表露在脸上的,是一个愚蠢而粗鄙、没什么心机的野蛮人少年所应有的单纯而羞涩的傻笑——卡努特突然发现,其实,和那人比起来,自己伪装欺骗的本事也未必就差多少。
而看到卡努特的笑容,那人就认为自己的劝解已经取得了完美的成功,于是一如既往的温和的微笑着,爱抚卡努特的金发:“主保佑你。”
卡努特也很顺从的低下头,藏起自己的眼神,和心底里的冷笑——如果他平时赐福的那些人知道他们的“爸爸”是怎样和他的情人尽享欢娱的,不知道是否还会一如既往的爱戴他?
而到了这里,卡努特也很清楚,就到了梦境的最后一段。
梦境的最后一段,在君士坦丁堡西边十里左右的一座庄园外。
庄园上下,死伤狼藉。而卡努特的兄弟们则肆无忌惮的在四处搜寻劫掠着一切金银财宝,只有西格特等几人还提盾持剑的站在卡努特身边护卫。
而那个人,正一脸惊恐的躺在卡努特面前,瞪大眼睛看着卡努特,庄严肃穆的教袍上沾满了鲜血。
“你……你怎么能……”
“我做事,是谁的意思,你不会知道。可是谁在中间牵线,你该知道。”看着那个人,卡努特面无表情,却宣告了对方的死刑。
“这不可能!我并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这句话是实话,实在得连卡努特都忍不住笑了出来:“是啊。本来这次也不是对你,是对这里的主人——你不过是被牵连进来了而已。”
这句话让惊慌失措的人终于冷静下来,并露出绝处逢生的欣喜:“不是对我……我只是被牵连进来……”
下一刻,那人脸色惨白,震惊而且怀疑的看着卡努特:“为什么!”
皱着眉,看着那个人,卡努特也升起一种怪异的感觉。
从那一天之后,他忍耐了很多天,准备了很多天,直到今天才可以为自己所受到的侮辱和欺骗复仇——只要一剑,就都解决了。
但他丝毫都不感到高兴,也感受不到半点大仇得报的快乐和解脱——甚至,他有种“我到底在干什么”的困惑。
“放松,爱娜宝贝儿,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策略。”卡努特一开口,震惊和绝望的神情再次同时出现在那人脸上,但卡努特全不怜悯的继续说下去:“我完全同意,他只是个和他的族人一样粗鄙、肮脏而且愚蠢的野蛮人。但他对我有那么点用处。这些野蛮人总是比较看重同族,而皇帝则很看重他们的武力。成为他的教父会为我在宫廷里赢得很大的便利,也会让我在教会里更进一步。”
听到这些话,周围的兄弟们也立即露出了愤怒的表情。但卡努特只是摆摆手,仍旧看着那人:“所以,你说,为什么?”
“我……我可以解释……”
卡努特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没那个必要。”
“我……我……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教你……修希底德、希罗多德、李维、塔西托……”
这个挣扎让卡努特迟疑了一个瞬间。有那么一个瞬间,卡努特想到,尽管对面的人是个骗子,但他终究还是个博学的学者;尽管那人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很多人,但他终归还是教会了自己许多东西——拉丁文、希腊文、修辞学、历史学……
然后,下一个瞬间,想到远在北地的父亲“做事要有始有终”的教育,卡努特解脱的轻笑,俯下身,用宝剑狠狠地将对方当胸刺穿:“不必了。”
再然后,猩红的鲜血就伴随着那人惊愕而瞪大的双眼喷涌而出,淹没了整个世界……
在这样的猩红之后,卡努特猛然坐起,从睡梦中惊醒。
紧接着,他就听到大厅外的远处,传来了喊杀声和惊慌失措的叫喊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