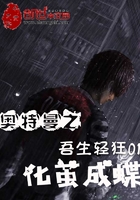“还是不说你怎么得罪四爷的吗?”封氏冷冷看着跪在地上的慎芮。
“奴婢真的不清楚。第一次见四爷时,他在池塘里的石头上晒肚皮,二爷就把他骂了一顿。当时他看了奴婢一眼,说我碍着他了,然后就走了。第二次见面,他用冰水浇了奴婢的衣服。第三次见面,是我在池塘边捏泥偶,他好像一时收不住脚,把泥偶都踢到了池塘里。也是那一次,他听到了奴婢乱哼的小调。这第二次和第三次,菊儿都在场。”慎芮真真假假地说完,就偷偷翻着眼皮看封氏。因为封氏不准慎芮直眉楞眼地看她的脸。
封氏对这个弓柏很无语,嫌恶地皱皱眉,挥手让慎芮出去。
这天,慎芮一大早起来,就被封氏指挥着扫地擦窗子,累了个满头大汗。好不容易干完活,刚坐下歇口气,一个平日里浇花除虫的粗使婆子笑咪咪地过来说道:“三姑娘,花树还没浇水呢。大热天的,一天不浇水,叶子就蔫了。”
这几天,花树浇水的活都是慎芮在干。
“混帐东西!还指使起三姑娘干活来了,也不看看你有几斤几两重!”金嬷嬷忽然一掀正屋的帘子,走到廊下,虎着脸骂那个婆子。
婆子吓了一大跳,赶紧赔着罪,去花园里挑水去了。
金嬷嬷板着脸看了一圈听荷院的下人,继续冷着声音说:“二奶奶教三姑娘规矩,不需要别人插手帮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位置,任何人敢做超越本分的事,听荷院可就留不下了。”
说完,金嬷嬷又进了正屋。众丫鬟婆子们互相看看,都默不作声地做起活来。在廊下做针线活的菊儿听完金嬷嬷的话,愣了半晌,脸上若有所思,看向慎芮的眼睛里含了更多的嫉妒。
“嬷嬷,二爷走了有一个多月了吧?你说她到底怀上没有?”
“还真不好说。没听到菊儿报告她来月信的事。来弓府马上就满两个月了。”
封氏捏帕子的手不自觉地紧了紧,眼神陡然凌厉了一下,又恢复了正常,说道:“嬷嬷确定后,就让她搬到南院去吧。眼不见为净。”
“也好。”金嬷嬷也不想再看着二奶奶折磨慎芮。她年龄越大,胆子越小,时常在封氏面前念叨积德行善得善果的事。
慎芮歇完气,又提起一桶衣服,去洗衣房。金嬷嬷虽然阻止了别人派的活,但没胆子免掉封氏早就吩咐下的活。
菊儿扔掉手里的针线活,急忙跟上慎芮。
从听荷院到后门口的洗衣房,要经过大爷和四爷的院门口。弓柏在院子里与弓杉比划招式时,看到慎芮一闪而过,急忙一下蹿到院门口喊道:“吆——,这不是三姑娘吗?好久不见啊。”两日没见了,二十四个时辰,的确很久了。
慎芮回过身,恭敬地行个礼,低眉顺眼,声音不高不低,“奴婢见过四爷。”说完,不待弓柏说话,提起地上的桶,转身继续走。菊儿略微弯下腰,就算行了礼,也跟着走了。
“哎——”弓柏抬抬手,不知道该说什么。慎芮冷淡疏离的态度中含着恭谨,也含着鄙视,摆明了要和他划清界限。
弓杉看看四哥尴尬的样子,有点好笑,疾走几步,赶上慎芮,说道:“三姑娘,你还在生四哥的气?”
“五爷说笑了。奴婢明白自己的地位,怎敢生主子的气。”慎芮冷淡地看看弓杉,同样恭谨地行了个礼。
“四哥只是跟你开个玩笑。他给我绑的纱巾用的单层。”
慎芮的神色顿了顿,眼中依然冷清一片。
“唉,没想到三姑娘的气性这么大。”
“五爷何以认为奴婢在生气?奴婢不过是谨守规矩而已。”
“我虽然见三姑娘的次数不多,但你眼睛里每每都是含着笑的。这次却没有了。”
“五爷敏锐。那是奴婢以前不懂规矩。谢谢五爷的提醒,奴婢以后不会了。”慎芮语气中的冷淡更甚。说完,再不停留,提着衣服急忙往洗衣房走。
弓杉在她身后有些结舌,同样抬抬手,想叫住她,但又没有可说的话了。
弓柏暗自懊恼不已。他捉弄她,并不是因为那次被她调侃而生气,是发觉她很特别。慎芮的特别,有眼睛的没眼睛的,都看得出来。一个人外在的气质、举止,深受她的生活习惯及所受教养等的影响,是根植在骨子里的,除非受过特殊的训练,懂得隐藏自己。
慎芮受了几十年的平等自由等理念的教育,她的言行中自然会带出来。比如,她在说‘奴婢’两个字时,一开始特别生硬,后来就像念别人的外号,语气中含着讥讽。她自己不知道,其他人却能听出来。还有很多方面,都能看出这个三姑娘与众不同,而且为人豁达,聪明且调皮。这也就是弓家几个兄弟都对她好奇的原因。
当然女人们那里,受着同性相斥原则的支配,嫉妒她的比较多,比如菊儿等。一个乡下丫头,凭什么这么与众不同?
慎芮可以不在乎别的,唯独对好不容易得到的生命特别珍惜。弓柏的玩笑,直接威胁她的生命,在她眼里就成了不可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