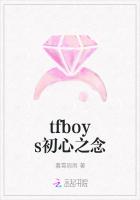蒋凤麟又往工作里间走去。随手开了照明,还没仔细看布置,就被墙上贴的照片吸走了全部的注意力,待他走近了看清了,手指无意识地松了松,手机“啪”的掉到了地上。
他怔忡了很久,很久。
壁橱的玻璃上贴了两张用立得拍照的照片,一张拍的是蛋糕,另一张则是两杯香槟,这是连翘的习惯,随身经常带着立得拍,遇到喜欢的人和景都会拍下来。
结婚快乐——那心形蛋糕上写的几个字几乎要把他的眼睛刺瞎。
时间居然是在她去上海前。
她,难道是早就知道了?
怎么会……
那种窒息的感觉再一次袭来,气势汹汹。
蒋凤麟倒退了一步,大口大口的喘气,想叫,想喊,可是半点儿声音都发不出来,都哽在了喉咙,眼睛涩涩的,里头藏着从未有过的失措和恐惧。
连翘……连翘……
他大叫了一声,抬手就把壁橱那面玻璃一拳敲裂,鲜红的血立马从指关节蹦出来,碎玻璃掉了一地。他感觉不到疼,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渐渐滑坐在地上,双眸已然失去了神彩,木然的眼神看着脚边躺着的手机发呆。
他还以为自己瞒得很好,可原来她都知道他做了什么。他比谁都了解连翘的性子,他等的电话也许不会再来了。
蒋凤麟突然放声大笑,他笑自己自以为是,笑自己什么都想要,结果很有可能把最重要的人失去了。
蓦地,他发现随着碎玻璃飞溅到地上的照片背后好像写了字,像是盲人重见了光明,他颓废的脸一下子鲜活了,肯定是连翘留下的!
他爬了几次,才狼狈地爬过去捡起来,照片背后果然是他熟悉的娟秀的字体。
——蒋凤麟,祝福的话我说不出口,只能给你做个蛋糕了。
——我不怪你。
秀气的字此时像凌迟的刀,伤得蒋凤麟体无完肤,感觉浑身的血都冷了。他情愿她怪他、骂他、恨他,冲到他跟前质问他打他,也不要这冷冰冰的几个字。
是他错了,大错特错。
人为什么总要等到失去了,才学会珍惜呢?
这几天刘胜斌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不是忙着谈什么大案子,而是动用到所有的关系,没日没夜地跑去各个地方联系找人,找连翘。不过连翘的社会关系太简单了,朋友没几个,没回老家,也没有用身份证乘机或者坐火车,甚至连银行的交易记录都没有,就连她妈妈的也一样,让刘胜斌的浑身解数都打在了棉花上。
而他的老板,公司不管,电话不接。要不是他还每天一通的汇报电话他还肯听,真不知道他是否还安好。这边一团乱麻,估计蒋家那边就更乱了,蒋苏联姻消息可是早上了报的,现在却面临新郎缺席的危机。
有些人却是等着看好戏,巴不得这桩婚事不成。
亲朋好友都急疯了,可蒋凤麟什么人都不见。
这天他在公寓里翻出了连翘给他织的毛衣,和他生日送她的项链,还有蛋糕店的钥匙放一起。钥匙和项链他都随手丢在地上,却把毛衣直接套在身上,大热天穿也不嫌热。
羊毛很软很舒服,尺寸也合适,蒋凤麟穿是刚刚好。
镜子里的男人眉眼冷漠,头发蓬乱胡子没刮,样子十分颓废,此时却摸着身上的毛衣又笑又哭。他早就该发现了,她给了他那么多的提示,给了他那么多次机会,他都没有抓住。
他从前觉得事业和感情是并存的,他都可以牢牢抓在手里,甚至事业心重的他会觉得把住蒋氏更加重要。
可是现在发现古人说得好,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想得到什么,就必须先付出什么,所以是他亲手把连翘给推开的,能怪谁?
床头柜上的手机呜呜地响起,他撇了一眼,亮起的屏幕没有显示号码,本来不想理会的,可是又怕是有连翘的消息,就鬼使神差地接了。
电话通了,那边一直没有声响。
蒋凤麟觉得奇怪,他想起了什么,死寂的心突然跳得很快。
“翘翘……是你吗?”开了口才发现他的声音很沙哑,好像很久没说过话似的艰涩。
还是没有声音。
不知道为什么,蒋凤麟却认定了似的,一直在说话,一直在叫连翘的名字。根本不考虑是不是打错电话或者认错人。
“你在哪里?我去接你好不好?”
“翘翘,你说说话,骂我也行……”
“我没结婚,不敢骗你了,你回来好不好?”
“我们,我们重新开始,好好过日子……”
“翘翘?”
说了那么多那么多,都没得到回应。
蒋凤麟都要怀疑自己的第六感,不过下一秒就听到隐隐的哭声。
再然后,是他挂念许久的声音说:“蒋凤麟,我们……分手吧。”
她一说完这句话,通信就切断了,嘟嘟嘟的声音让蒋凤麟脑袋发懵,他得用多大的自控力,才压住自己不要爆发出来。
她说分手,说得那么决绝,连让他挽回的余地都没有就断了联系。
蒋凤麟怎么甘心。
心里跟泡了黄连水似的又苦又涩,他几番深呼吸,才勉强冷静下来地打电话给小刘,让他查通话记录,看能不能查出连翘现在在哪里。
可又不是拍电影,查归查,好消息却是那么少。查出来不过是一个没有登记的号码,已经弃用了,线索再次中断。
刘胜斌觉得,他的老板已经濒临发疯的边缘。
也许是知道蒋凤麟没有放弃找人,也许是了解他的为人,又过了几天,一直没消息的连翘用原来的号码发了最后一条短信给他。
——凤麟,不要浪费时间找我了,到此为止吧。
这条信息有两层意思。
其实是告诉他,找她这事到此为止,他们的关系也到此为止。
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