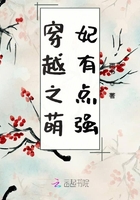第二日早上,二人问了楼里的姑娘,发觉外头还是不安生,便也只能在楼里多待上几日。等着风头过去,二人方能回府。
洛依尘揣度着无趣,又听闻春帆楼的头牌清倌水秀姑娘今儿出台献曲,便拉了陈子离使银子买了两个厅里的座。
好容易熬到了天色将晚,春帆楼一如既往的上了座,洛依尘终于拉着陈子离从房里出来,坐到了大厅正中的一桌,准备听听那水秀的曲子。
等了半天,却只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那头牌姑娘还不出来。洛依尘游目四周,叹道:“这般零乱浮躁,还有何音可赏,何乐可鉴?”
“也不能这么说,”陈子离又一次反驳她的话,“听说这个水秀姑娘是压得住场子的,等她一出来,修罗场也成清静地,你担心什么?”
他话音方落,突然两声云板轻响,不轻不重,却咻然穿透了满堂哗语,仿佛敲在人心跳的两拍之间,令人的心绪随之沉甸甸地一稳。
洛依尘眉睫微动,看向大厅南向的云台之上,走出两名垂髫小童,将朱红丝绒所制的垂幕缓缓拉向两边,幕后所设,不过一琴一几一凳而已。
众人的目光纷纷向云台左侧的出口望去,因为以前水秀姑娘少有的几次大厅演乐时,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果然,片刻之后,粉色裙裾出现在幕边,绣鞋尖角上一团黄绒球颤颤巍巍,停顿了片刻方向前迈出,整个身影也随之映入大家的眼帘中。
演乐厅内顿时一片失望之声,那出来的人也不恼,只是娇笑道:“各位都是时常光顾春帆楼的熟朋友了,拜托给妈妈我一个面子吧!”当家妈妈手帕一飞,接着笑道:“水秀姑娘马上就出来,各位爷用不着摆这样的脸色给我看啊!”
这妈妈虽是徐娘半老,但仍是风韵犹存,游走于各座之间,插科打诨,所到之处无不带来阵阵欢笑。众人被引着看她打趣了半日,一回神,才发现水秀姑娘已端坐于琴台之前,谁也没注意到她到底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身为春帆楼的当家红牌,卖艺不卖身的水秀绝对是整个花街最难求一见的姑娘,尽管她并不以美貌著称,但那只是因为她的乐技实在过于耀眼,实际上水秀的容颜也生得十分出色,柳眉凤眼,玉肌雪肤,眉宇间气质端凝,毫无娇弱之态。
洛依尘看了嫉妒,跟陈子离嘟哝道:“怪不得说男人都爱往窑子里跑,果然是美人儿多。”她说完,像是没骨头一般躺在坐的一本正经陈子离腿上。
看到大家都注意到水秀已经出场,鸨母便悄然退到了一边,坐到侧廊上的一把交椅上,无言地关注着厅上的情况。与方才的笑语晏晏不同,那水秀姑娘出场后并无一言客套串场,调好琴徵后,只盈盈一笑,便素手轻抬,开始演乐。
最初三首,是大家都熟知的古曲《阳关三叠》、《平沙落雁》与《渔樵问答》,但正因为是熟曲,更能显示出人的技艺是否达到炉火纯青、乐以载情的程度。
三首琴曲后,侍儿又抱来琵琶。怅然幽怨的《汉宫秋月》之后,便是清丽澄明的《春江花月夜》,一曲既终,余音袅袅,人人都仿佛浸入明月春江的意境之中,悠然回味,神思不归。
洛依尘仿佛没听到一般,听着那人的曲子,心神飘摇之下,手执玉簪,击节吟道:“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清吟未罢,台上水秀秋波轻闪,如葱玉指重拔丝弦,以曲映诗,以诗衬曲,两相融合,仿若早已多次演练过一般,竟无一丝的不谐。
又是一曲终了,水秀缓缓起身,裣衽为礼,厅上凝滞片刻后,顿时采声大作。旁边一桌上一个看似风流的公子不自禁地连饮了两杯,叹道:“今夜便只闻这最后一曲,也已心足。”
“能有此悟,亦可谓知音。”又是一个坐在旁边的公子,举杯就唇,浅浅啄了一口,目光转向台上的水秀,眸色微微一凝。
洛依尘看了看话音刚落的那个男子,跟陈子离小声道:“那人是谁?我怎么瞧着像户部尚书家的公子,穆丰光?”
“正是他,你倒是好记性,刚刚说话的那个,是吏部尚书家的嫡出公子韦明磊。”陈子离小声一个一个说着,话音未落,便又听到后面一桌上有人开口了。
“水秀姑娘果然音律大家,令人拜服。”开口的也是个贵公子,洛依尘回头一看,心里就有了个影子。这人正是右相才正信的长子才如廉,素日里混迹在这花丛中,恨不得气死他老子。
陈子离知道洛依尘又想到哪里去了,就算在这里听曲儿,这人也忘不了想着朝廷上的事情。他想到这里,忽然发觉自己刚刚也在算计,若是今日这几人的行迹都传到御史台,那么他们的父辈又当如何?
他怔怔的想着,目光便有些失焦的看着前面,而他们两人正好坐在正中的头一桌,目光便似直直的看着水秀了。
只是短暂的视线接触,水秀的面上便微现红晕,薄薄一层春色,更添情韵。在起身连回数礼,答谢厅上一片掌声后,她步履盈盈踏前一步,朱唇含笑,轻声道:“请诸位稍静。”
这娇娇柔柔的声音隐于堂下的沸然声中,本应毫无效果,但与此同时,云板声再次敲响,一下子便安定了整个场面。
“今日承蒙诸位捧场,光临我春帆楼,小女子甚感荣幸。”水秀眉带笑意,声如银磬,大家不自禁地便开始凝神细听:“为让各位尽欢,水秀特设一游戏,不知诸君可愿同乐?”
一听说还有余兴节目,客人们都喜出望外,立即七嘴八舌应道:“愿意!愿意!”
“此游戏名为‘听音辨器’,因为客人们众多,难免嘈杂,故而以现有的座位,每一桌为一队,我在帘幕之后奏音,大家分辨此音为何种器乐所出,答对最多的一队,水秀有大礼奉上。”在座的都是通晓乐律之人,皆不畏难,顿时一片赞同之声。
水秀一笑后退,先前那两名垂髫小童再上,将帘幕合拢。厅上慢慢安静下来,每一个人都凝神细听。
少顷,帘内传来第一声乐响。因为面对的都是赏乐之人,如奏出整节乐章便会太简单,所以只发出了单音。场面微凝之后,靠东窗有一桌站起一人大声道:“胡琴!”
一个才束发的小丫头跑了过去,赠绢制牡丹一朵,那人甚是得意地坐下。第二声响过。洛依尘立即扬了扬手笑道:“琵琶。”
小丫头又忙着过来送牡丹,陈子离见洛依尘并没有起身的意思,便伸手接了牡丹,道:“嘴怎么这么快?”
第三声响过,洛依尘百无聊赖的敲着桌面,道:“芦管。”于是再得牡丹一朵,又是陈子离替她接了,放在桌上。
第四声响过,洛依尘并没听出来,陈子离刚对她耳语过,身后才如廉一桌有一人喊道:“箜篌!”
第五声响过。略有片刻冷场,陈子离又轻轻在她耳边低语了一声,洛依尘立即答道:“铜角!”
“铜角是什么?”话音刚落,看着新到手的牡丹,洛依尘愣愣地问了这么一句。她鲜少有不认识的乐器,这次可是丢人了。
“常用于边塞军中的一种仪乐和军乐,多以动物角制成,你自然少见。”陈子离刚解释完毕,第六声又响起,洛依尘正在听他说话,一闪神间,隔壁桌的韦明磊已大叫道:“古埙!”
接下来,横笛、梆鼓、奚琴、桐瑟、石磬、方响、排箫等乐器相继奏过,洛依尘的鉴音力不过一般,故而在思索间被人抢去不少答案。但幸而陈子离帮着,二人也算战果颇丰。
最后,幕布轻轻飘动了一下,传出锵然一声脆响。大厅内沉寂了片刻,相继有人站起来,最后张张嘴又拿不准地坐下。洛依尘想了半天,最后还是放低姿态询问道:“子离,你听出那是什么了吗?”
陈子离忍了忍笑,低低就耳说了两个字,洛依尘一听就睁大了双眼,脱口失声道:“木鱼?”
话音刚落,小丫头便跑了过来,与此同时帘幕再次拉开,水秀轻转秋水环视了一下整个大厅,见到这边牡丹数朵,不由嫣然一笑。
洛依尘见水秀走来,不由笑道:“水秀姑娘打算给我们什么大礼?”她只看着手中的牡丹,一边说话一边撕扯着花瓣。
只见水秀眼波流动,也不看洛依尘,粉面上笑靥如花,只盯着陈子离不疾不徐地道:“水秀虽是艺伎,但素来演乐不出春帆楼,不过为答谢胜者,你们谁家府第近期有饮宴聚会,水秀愿携琴前去,助兴整日。”
此言一出,满厅大哗。水秀不是官伎,又兼性情高傲,确实从来没有奉过任何府第召陪,哪怕王公贵族,也休想她挪动莲步离开过花街,外出侍宴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众人皆是又惊又羡。
穆丰光虽是嫉妒,却还是笑得眼睛都成了一条缝儿,道:“水秀姑娘肯来,没有宴会也要开它一个!”
洛依尘心道,这礼算什么,她才不稀罕什么妓女往王府去。只是还未开口拒绝,便听到不远处有人道:“那就请水秀姑娘,端午节申时,移步端王府。”
一听这声音,许多人都愣住了,尤其是洛依尘,赶忙从陈子离腿上爬起来,看着刚走进来的人,恨不得赶紧跑出去,只当刚刚不是她躺在那里。
“王爷,属下失礼,原是不该来这里的。”陈子离知道这会儿只能如此解围,否则还不定要闹出什么来。
他一边说,一边往洛依尘前面跨了一步,仿佛只是为了行礼一般。洛依尘站在他身后,看着四周都是行礼的人,自己也跟着行礼,只是眼睛往上偷偷瞧着段凌肃的神情。
水秀也知道这来的人是谁,心里一动,若是刚刚这人是端亲王的手下,那身份也算不得尊贵,若是真的能去王府讨了王爷欢心,让那王妃嫉妒起来,未必就不能赐给一个侍卫。
要说水秀在那里百转千回的转心思,段凌肃脸色变有些难看了,只是冷冷的开口道:“都免礼,你们二人随本王回去,往后若是再叫本王见着你们往花街闲逛,可要仔细自己的皮!”
洛依尘没办法,只能跟在陈子离后面,希望段凌肃不要注意到她。又听一旁的韦明磊道:“真是无趣,好端端的来了这么个煞星,水秀还给召到他王府里去了。”
“可不怎的,十六爷素来是个诗酒风流的,若是水秀姑娘去了,没准儿就迷上他了。当年那丞相府的张小姐,可不就是这样?”穆丰光也不落后,心里对段凌肃便是极其不满。
洛依尘只听到这里,便出了春帆楼的门。还没等走出花街,段凌肃就一脸肃色的把她塞进了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