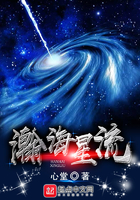晏秋趁机握住,牵着她往隔间走去,反正门已经被关上,不怕被人嚼舌头。直走到隔间,他将丁柔按在小床上,自己搬了凳子坐在她脚下,仍旧握着她的手不肯松开,微微垂了眼,片刻之后,抬头看她:“如果一个人莫名其妙失去一段记忆,还能不能找回来?”
终于到
这一步了,丁柔心中咚咚跳起来,几乎要忍不住,眸子一闪,几乎要喷出光来。她天生不是聪明的人,性子又极冲动,若非这些年吃了大苦,才不会这般隐忍。想了想,道:“你把详细情形说来,我才能诊断。”
晏秋抿了抿唇,还有几分犹豫。这件事情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提起,就连叶总管都没有。此时竟想对她和盘托出,他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份信任。似乎她就是值得他相信。
想了想,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十四岁到十九岁五年之中的记忆全然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我十四岁最后的记忆是在野外被狼袭击,伤重几乎丧命。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不知为何醒来却在家中,竟然已是五年后。”
他醒来时躺在家中的床上,叶总管被父亲派来照顾他。他发现自己的左腿断了,额头也有伤。下意识摸了摸肚子,却发现肚皮一片凹凸不平。他才知道那并不是梦,而是真切发生过。只是无论他怎样回想,最后的记忆都是被狼袭击那一段。
他很害怕,不敢对任何人提起。后来经过多方旁敲侧击,才知道已是五年后。而那五年他似是去了外面,只是谁不知是哪里,又发生了什么。问急了,都说他在外历练,终于学成归来。他不敢再深问,生怕露馅。后见大家对他一点怀疑也没有,渐渐知道问不出什么来,只这五年,终成了谜。
“然而这些日子,我却总做一些奇怪的梦。梦里的地方是我没到过的,但是又隐隐觉得熟悉。还有那些人,我总也看不清他们的面孔。有些发生的事,总是一遍一遍出现在梦里,有始无终。”
晏秋求助地看着丁柔,希望她能给出他想要的答案。
丁柔沉吟片刻,道:“你怀疑,你这些日子做过的梦,是你忘掉的记忆?”
晏秋点头:“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
丁柔的手心凶猛地出汗,几乎要颤抖起来。又怕被他发现异样,功亏一篑,只能强自忍着。克制自己的嗓音如往常一般平静,问道:“你想找回那些记忆?只是时间久远,又是这等诡秘的病症,我也没有把握。”
晏秋急切地望着她:“若有办法,只管试一试。我不怕的。”
他最怕的却是这五年间发生过什么不该忘的,却被他忘记了。那句“我走了,你不必等我,就当我对不起你”,以及少女尖利的叫喊,时常让他梦中惊醒,心中彷徨。他内心深处隐隐恐惧着,总觉不安。
“这段记忆我一定要找回来。请你帮帮
我!”晏秋恳切地道。
丁柔望着他认真而热切地目光,几乎立时就要疯掉:你现在想找回来了?早干什么去了?若你早就像现在一样,我何至于受那些苦?
然而千金难买早知道。事情到底发展到这样了。什么也挽回不来。她用力咬牙:“好,我尽力一试。”
晏秋此时还想着,丁柔帮了他这么大的忙,若他真的找回失去的记忆,了却前事,即刻就同她成亲,必不辜负她。
他却没想过,若前事无法了却,又置丁柔于何地?他更没想过,前事与丁柔之间有着那样无法剥离的关系。
他只陷入激动之中,任由丁柔为他施针,熬药。再不嫌弃药苦,每一碗都喝得干干净净。
不得不说,丁柔的医术继承自其父,着实有几分功底。晏秋分明感到脑中时常闪过片片场景,与梦中人物叠加,耦合度极高。他陷入即将找回记忆的兴奋中,忽略了丁柔眼中时常划过的疯狂与恨意。
终于有一晚,晏秋再做梦时,那一幕重复了无数遍的场景连贯起来。蓝衣少年对女孩子说出“我走了,你不必等我,就当我对不起你”之后,牵了一匹马飞身而上,纵弛而去。穿过城门时,他不由激动起来,拼命地喊,快回头,快回头!
蓝衣少年不负所望,冲出百米之后勒住马,缓缓回头。不远处的城门之上,刻着三个字,飞花镇。
“飞花镇!”晏秋大喊一声,猛地从梦中醒来。寂静的黑暗中,他粗重地喘息着,因为激动而内心砰砰直跳。飞花镇,他终于知道梦中那清秀明丽的地方是哪里了!
他再也睡不着,翻身下床,摸索着穿戴好,又找出一包碎银子系在身上,便坐在床头等着天亮。
他一动不动盯着窗外,终于等到天际泛起一丝鱼肚白,再也忍不住。到外院牵过自己的马,急不可待地翻身而上。
天刚蒙蒙亮,哒哒的马蹄声在街上急促响起。
为了这丢失的五年的记忆,晏秋是拼了命的。往常是不敢探测,如今既然下定心思,那必是要找回不可。而且他一刻也等不得。于是此行三日,昼夜不歇,终于在第四日午时来到飞花镇。
古朴厚重的城墙,清秀明丽的风景,如梦中所见一样。晏秋心中激动,几乎片刻也等不得。
他很快进了城,依照梦中的记忆,一条街一条街地走着。然后他发现,他意识深处对此地有着深深的印象,几乎是不由自主地,他走到一个胡同口。
左边
,第二家。晏秋的脚步像有自己的意识,来到一扇破旧的,几乎轻轻一碰便能散架的木门前。
他看着这扇木门,只觉脑中有一大团记忆奔腾翻涌着,撞得他头晕眼花,浑身发颤。他抖着手,推开结满蛛网的木门。
吱呀一声,门开了。他进了院子,在院中站定。院子很破旧,绿色的草尖从长到他膝盖处的荒草中冒出来,一地厚厚的积叶,右边栽种着两棵桃树,已经结了青色的果子。
他眨眨眼,似乎看到一个梳着双丫髻的少女尖声叫着,抱着头满院子乱跑。桃树上坐着一个少年,手中团着一团黄的绿的花的毛虫,有一只没一只的朝少女身上扔。少女躲不过,偶尔会一脚踩在少年没扔准的虫子上,吧唧一声,虫子被踩得肚破肠流,迸出的内脏将她滑倒在地上。
少女看着鞋底上沾着的虫子尸首,受不住地尖声嚎叫。她的声音又尖又亮,一嗓子嚎出来,二里外都听得见。于是从屋里走出来一个身材有些佝偻的老人,咳嗽一声,将少女训斥一顿。然而威吓的眼神却落在少年身上,那才是真正的责备。
突如其来地,晏秋眼前模糊起来,两行清泪顺着脸庞滑下。
晏秋在记忆最深的街上来来回回走着。他记不得曾经认得的人,只希望有人能记得他,从而能将他喊住。
事实证明,他这张脸给人留下的记忆还是比较深刻的。他在一条街上走了两遍,就有几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看他,探头探脑,一边看他一边不知道商量什么。他装作没看见,静观其变。不一会儿,走过来一个身高到他眉毛处的少年,皮肤很黑,浓眉毛,细眼睛,嘴唇很厚,长得很有特色。少年走到他身边,试探地问:“山哥?是你回来了?”
晏秋一愣,山哥?微微一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很有亲和力:“小兄弟,你认得我?”
少年如见了鬼似的蹬蹬后退,拨浪鼓似的摇头:“不,不,我不认得你。对不起,我认错人了。”他又看了晏秋一眼,才转身走了。走之前嘟囔一句:“怎么跟山哥长这么像?不过山哥才不会这么彬彬有礼,早一爪子伸过来了。”
晏秋听到之后,更加愣住。看着少年回到那堆男孩子里头,叽叽咕咕一阵,仍不肯散去,只看向他的眼神更富有挑战性了些。紧接着,一个长得稍白的少年走过来,约莫小一些,只到他下巴高。斯斯文文,举止很秀气,走到他身前先作了个揖,然后道:“冒昧打扰。请问公子尊姓大名?”
晏秋挑了挑眉:“敝姓晏,名秋。不知你们是?”
少年听到他的名字,神情有些失望:“我们是这镇上的人。刚才看到公子,以为看到了故人,冒然错认,还请公子勿怪。”
晏秋听他这么说,心中有了谱。想了想,扬眉道:“你说的那个人,多半是我的孪生兄弟。他幼时被抱给亲戚抚养,我听说他曾经到过这里,不知道现在还住这里吗?”
少年将他上上下下打量半晌,最终视线落到他鼻子上,似乎要瞧出个花来。片刻后,古怪地笑了:“山哥,别装了。你右耳垂上有一颗痣,而你鼻子上那个小坑还是我抓的。”
晏秋一愣,话还没套出来,已经被人认出来了。他摸摸鼻尖,挑眉笑道:“几年不见,最聪明的还是你。黑大壮就没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