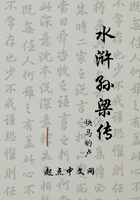不知我们靠车上微薄的粮食和淡水撑了多少天,到现在裝粮食的背囊已空空如也。两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向城里或避难所挺进,经过我几天的“洗脑,”其余四人都很向往村中的避难所的生活;还有一种是进山捕猎。前者毫不犹豫地被我们否认,因为在我们眼里那不过是自杀式的作死,我们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第二方案。
但虽是人迹罕至的郊外林子,在末世中同样危险。
四个男人又挤在帐篷里度过了一天。太阳升到树梢顶时,我和那个微胖的士官以及那个机车连的士兵,准备进山试一试,到日落时再回来。
温柱茗扔给我一套标准的军事装备,当我问起这哪来时,回应我的只是:“那是我从一个大兵尸体上剥下来的。”
我们进林了,离开了车所停靠的空地。
夏天的茂林里湿气很重,更何况刚下过一场雨,刚踏进半步汗就已浸湿了衣服,手心捏出了汗。继续走着,连踩断一根树枝都会吓一跳。每过一段都做下记号,每到一个岔道是总会蹲下布置陷阱,就这样,紧张着顺利进行。
又到了一段由山中动物踩出的一条小道,当温柱茗附身布置猥琐的陷阱时,我听到了动物咀嚼的声音,不止是我,其他人也紧张地环视。虽然声音很小,但声声入耳,让人心惊肉跳。我轻轻拨开了声音发出的草丛,而后面两人则握紧了手中的自动步枪,准备开枪射击。
而映入眼帘的只不过是一只灰褐色的野狗在啃食一具腐烂的尸体罢了,但那味道……“呕~~”已经有人忍不住了,这实在恶心得让人发呕。但这让我们轻松了不少,甚至有人吹起了口哨。
“那个……谢谢你、救了我。”在路上,我垂头轻轻地说道。迎接的是他的笑声:“呵呵,只要你记住,多救一个人,今后少一个丧尸要对付。”……从交谈间得出,他是本地人,父亲当过兵,按现在来讲,他是随父选业。
“对了你为什么当兵?”
为什么当兵?为什么?虽是他的随口一问,但在我心中却犹如万斤铅块。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一直深深地问过我自己,但从未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我当兵的志愿一提出,虽收到了家里人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外人的看不起。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大概是觉得军人是世界的救世主吧!”我用以往安慰我的理由回答。
“救世主?哼!……”回应我的是另一个士兵的苦笑和冷哼,“在末日开始之前,那些我们拼死拼活保卫的人们把我们当做什么?杀人魔,吃国家饭的闲人?他们放着我们不管不顾,心理只想着那些明星、明星、明星!炒作、炒作、炒作!难道他们所崇拜的偶像会在战争或灾难第一时间救她们吗?现在倒好了,他们才知道我们这些吃国家粮的‘软蛋’的重要。哼呵呵。”他越说越激动,直到最后的冷笑才恢复平静,而他却把我们的心里话倾述出来了。
沉默…………
继续走着,正当决定返回之际,可怕的咀嚼声又再次响起,但是这次的非同一般,这声音比之前的还要大。
拨开草丛,这回不一样了。只见一身西装打扮的上班族正在撕咬一只山鸡,鲜血沿着“他”的下巴泊泊地流着,羽毛四处飞落。但他脸上已经毫无血色,“他”那翻白地眼珠子透过破碎的眼镜紧盯着我们,在我们惊恐的目光下狠狠地撕下一块血淋淋的鸡肉,吞下去,然后向站在最前面的我扑来。
它这一扑很有力度,把我整个人扑倒在地,手里的自动步枪掉落在一旁,我用手狠狠地掐着它的喉咙,丧尸的牙齿始终咬不到我,但却贴紧着我的脸,那样的近。它狰狞地向我咬去。我愈加努力地反抗,它就愈加疯狂。它的牙齿一张一合,作撕咬状,口鼻中的鲜血滴到了我的脸上,丧尸用手臂挥打着我,我只好不停地翻转以便应付。站在我旁边的两个人不知所措,在如此快速地翻转下,他们无法瞄准丧尸。
这样僵持了很久,一直翻到了一旁的树桩上。我瞅准机会,左手使劲地掐着它的脖子,右手则抓住丧尸的额头,使劲地向树桩撞去……直到撞得脑浆飞溅才停止,喘着粗气扭头望着已经惊呆的两人。
这是我离丧尸如此近,又是如此的惊险。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对面两人尴尬地笑了笑,陈宽政过去拾起我沾满血的武器。而我的目光又落在倒下的丧尸身上。
直到那个丧尸头被我砸开是我才发现,丧尸体内的血还是殷红且温暖的,通常情况下,感染了很久的丧尸体内由于身体机能被病毒摧毁导致瘫痪,所以血液循环失效,血液会在体内凝固,变黑,温度也会下降。而这只丧尸没有达到前提要求,只能说明它感染不久,而就算是从别处到这来的,但这荒无人烟,只能从距离数百里的村落来到这里,那也要很长时间。这表明了,它生前是一个掉队的幸存者,逃到这来,不知原因地被感染;再者就是它来至不远的地方,换句话说,它生前曾跟随一支幸存者团队到来这里或它曾经住在这里。
我把我的发现告诉了其余二人,六目对视了一下,决定寻找到这里的任何人类并给予帮助。
那具丧尸的感染源来至它小腿上的清晰咬痕,到现在还流着血,但是可观的是,丧尸是边流血边走的,一路上留下的血迹更触目惊心。
我们一直跟着血迹一直走着,湿气混着血腥味扑入鼻腔,鲜血挥发出的味道在肺腑里散开来,让人头昏脑胀。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留下了多少的记号,更不知呕了多少次,我们才终于看见心中的目的地。
那是在一片粘土沾满落叶的空地,上面挤满了车,车与车之间相围,圈出的空地上停着两辆旅游车,再过就是篝火,以及正在玩沙的孩子。
他们对我们的到来很惊讶。
我们一出来,空地上面的人的目光便死死地盯着我们一行人。接着,从旅行车走出来了不少的人,甚至还车顶还冒出了一个手持散弹枪的两发鬓白的老人,全息地瞄准着我。我们没有说话,只是神同步地举起手,环顾四周。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走了出来。
“你们谁是长官?”他冷不丁的冒出一句。“我!”温柱茗道。紧接着他上前跟那个脸上胡子拉碴的青年男子嘀嘀咕咕地说了两句。随之的是男子对我们的微微一笑,然后挥挥手,领着我们进入了他所说的营地。
“其实爆发前几天我们早已做出了准备,爆发时我们听从广播的提议和警告,到附近的庇护所,但是他们不让我们进去,迫不得已,我们只好驱车来到这里。还有,这一辆旅行车是我提前买的,而这一辆是老罗的。”青年边走边指了指另一辆旅行车和在车顶上那个持枪的老人,“老罗是外国人,他是到我们这旅游的,他是一位退伍老兵,来这旅游的,特意买的车,方便旅游。在这他负责警戒”青年说完,向老罗挥了挥手,老罗手上的枪也跟着挥了挥,又放下了。“这些是我在路上认识的人,他们急需帮助,所以他们跟着我们来了。”青年又挥了挥手,让警惕的人们放下心来,“对了,我叫张斩,在这里有事就叫我。还有我们希望你们的加入,或者……你们成为我的盟友也可以。”说完,他自顾自地走向人群,向人们说了什么,然后就跑开了。
不知他道了什么,人们放下心来,各自又开始忙活自己的事情,我们三个人尴尬地站在空地上,没有说话。
青年拾了一把柴火,见我们还站在那,笑了笑,拉我们进了他的旅行车上。
而我们也尴尬地坐在车上的沙发上,依旧沉默。“你们在外面还有其他人吗?”每当这时候都是张斩破除了令人窒息的尴尬气氛。“……有、有。”我说道。张斩点了点头。而这更打开了陈宽政的话匣子,他一向是个多嘴之人,整天叨叨个不完,他开始跟张斩大侃大聊。我和温柱茗也无心听着,走出车,望着油绿油绿的林子和落日凑成的美景,心中充满了欣慰,但不知危机却已悄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