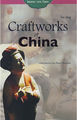布罗德卡总共抄下十二位女士的号码——亨利希就是这样称呼她们的。在打过十二通电话之后他获知,一晚上的价格是一万先令,而且没有一位从事此项职业的女人用的是真名字。有两个女士听说过诺拉·莫娜,其中一人还告诉他,诺拉偏爱在一个叫奥斯登的酒店出入,这家酒店地处热闹的娱乐场所,离斯特凡大教堂不远。
布罗德卡草草地完成拍摄采访任务,了结手头的工作之后,他终于有时间去找诺拉以及查清她背后的主使。
奥斯登酒店在维也纳比较有名,人们会称它为计时酒店,如果这个冠名不是和******、低俗的娱乐以及犯罪联系在一起的话。其实奥斯登原本是一家体面的几乎算得上考究的酒店,即便它的二十六套客房论小时付费,也不会被人想歪了。又因为娱乐场所的消费群体人数并不随季节变换而起伏涨落,所以奥斯登是维也纳惟一一家房价在夏天和冬天一致的酒店。
守在酒店里的老板娘告诉布罗德卡,她并不认识一个叫诺拉·莫娜的客人。布罗德卡明白,老板娘当然不会轻易张嘴,谨小慎微才能在这种娱乐场所中存活,不过守口如瓶是钱袋的头号敌人。在掏出一千先令的钞票之后,布罗德卡从这个容颜憔悴的老板娘那里得知,诺拉·莫娜的真名叫做玛寇维茨,每个礼拜三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会在24号房间——依墙纸的图案被称为“丁香花房”一一出现,与之约会的是一个外地的有钱人,他在歌剧院定下包厢打发晚上的时光——整整一年都是如此,除非歌剧院歇业。
眼下正是好时机,礼拜三,夜浓时分。布罗德卡瞧见一辆出租车在街角停下,就紧上几步钻进车里,给了司机一笔阔绰的小费,向他漏洞百出地解释说自己为等某个人必须得停留好一会儿。布罗德卡透过车窗注视着奥斯登酒店的大门人口。
一位衣着不凡的先生刚走进酒店,十一点整诺拉也随后到了。
一个钟头之后诺拉走出来,穿过街道招呼出租车,布罗德卡示意司机跟上诺拉的那辆车。车向南开去,绕过环形路,途经塞斯松展览馆和维也纳国家剧院,直奔东南方向,进入一片居民住宅楼,这些楼房大都建于十五、十六世纪,十九世纪被重新修缮,面积庞大,就像是象群。
出租车停在便道上,后面就是一排排房子。诺拉下了车,布罗德卡以安全的距离尾随在她身后。
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一栋破败的七层廉租楼前,楼层立面的众多铁栅栏小阳台皆堆满了废旧破烂,头一眼看上去,不觉担心它们会随时被重物压塌。
布罗德卡悄悄跟着诺拉进了门洞,大木门上的锁头早就不管用了。他听见二楼的一间房门被打开又合上,于是拾阶而上。
右手边的门牌上写着“玛寇维茨”。布罗德卡按下门铃,丁零零的铃声尖锐刺耳。似乎诺拉并没打算来开门,于是布罗德卡开始用力叩门。
终于他听到里面在问:“是谁呀?”
“布罗德卡!”他提高嗓门。
起初没有任何回音,静静地等了几分钟之后布罗德卡听到有钥匙在锁眼里转动,诺拉只开启出一道门缝,露出她那张浓妆艳抹的脸。
“您走开!”她尖叫着,“否则我叫警察了。”
布罗德卡用脚踹开门,将诺拉一把推开,冲到屋中央,这是一个大开间,一些笨重的旧家具将其隔成两间。
“我叫警察了!”诺拉激动地叫嚷,脸上满是惊恐的神情,她几近半裸,紫色紧身胸衣裹凸出一对****。
紫色,布罗德卡心里紧了一下,偏偏是紫色!
他对诺拉的警告不以为然,反而稳稳地站着打量起这个凌乱的居所来。
诺拉突然变得拘谨,她拽了一件花团锦簇的睡衣套在身上,叼着烟从兜里掏出打火机。她正要燃着,布罗德卡一把将香烟从她手中打掉。
“干什么?你究竟想怎么样?”诺拉尖叫着朝靠沙发的小桌子上的电话机走去。布罗德卡抢前一步,从她手里抄过电话,摔在地上。
“我还要问你哪,你到底准备对我干什么!”布罗德卡再也忍不住了,他奋力将诺拉推倒在沙发上,诺拉一声尖叫,用右胳膊肘护住脑袋。
布罗德卡紧逼上前,喝问:“你说,你到底对我有何企图?指使你的人是谁?快说!”
诺拉把胳膊放下来,她脸上的脂粉已经花了,头发乱蓬蓬的,全无丝毫魅力而言。布罗德卡不禁自问,自己怎么会一时昏了头被这样的女人迷得神魂颠倒。
诺拉结结巴巴地说出她是为了钱才干这事的,她急需要钱,他大概也能瞧得出来她现在的窘境。
“付你钱的人是谁?”
“两个男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是夫人介绍的……”
“夫人?”
“是的,就是奥斯登的老板娘。谁要是想赚点外快,而又像我一样没有皮条客帮衬,就会把电话留给夫人。那些想找乐子的男人反正会找她,全维也纳的人都知道。”
“于是那两人给了你钱?为此你要做什么?”
“让我去调查您,您的全部情况,大事小情,您整个的过去。
那些人先给我两万先令,只要我告诉他们我所探得的你的事情,明天我能再拿到两万,不过现在我对此已经不再指望了。”
“那你一定知道他们的名字。”
“相信我,我不知道!”诺拉绝望地叫喊。他俩的对话在静寂的夜里分外吵闹,隔壁邻居咚咚地砸墙抗议。“我真的是不知道。”诺拉压低嗓门又说,“我们约在歌剧院的咖啡馆,那两人问我想不想赚上两万先令,我要求四万,他们也答应了。我起初想,这些家伙指不定要在我身上玩什么花样呢。您能想象得出当我被告知我只需去摸您的底,其他什么都不必做时,我有多吃惊。之后他们给了我您的照片,告诉我您的名字还说您就住在大饭店,而我正是您喜欢的那种类型,跟您凑近乎套取真相该不会太难。”
“真相?什么真相?”布罗德卡眉头一紧,问道,“那些家伙没有说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的印象是那些人对您了解得相当多,可显然又不够多。我觉得那两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是什么呢?”布罗德卡朝窗边走了三步,窗帘遮住外面的视线。他转过身,重又回到诺拉面前问话,远没有先前粗暴:“明天你约好和他们会面?”
“是的……也就是今天,已经后半夜了。歌剧院咖啡馆,午后两点。”
布罗德卡点点头,“你打算见他们吗?”
“嗯,我过去把钱还给他们,告诉他们我没能如愿从您那儿套出什么,您喝得烂醉,一直在胡言乱语。”
“这样说不错,”布罗德卡若有所思地说,“不过不是最好的办法。”
诺拉盯着他问:“您这是什么意思?”
布罗德卡倒吸口气,说道:“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跟踪我们,我反正做梦都没料到在酒店被人盯上。你发现有人跟着我们吗?”
诺拉耸了耸肩膀摇摇头。
“好吧,你过去跟他们瞎说一通。谁能肯定我就一定会如实地把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讲给你,或许你的把戏早被我看穿,随便跟你编故事呢。”
“那倒是。”诺拉半信半疑地说。
布罗德卡紧接着说:“那两个家伙我很想看上一眼。你是说歌剧院咖啡馆?下午两点?”
“是的,不过我……我有点害怕。”
“别多想了。”布罗德卡朝门口走去,扭头又说,“对了,还有,电话机的事我很抱歉。”他从兜里掏出两张钞票放在饭桌上,“买个新的吧。这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变故太多了。”
等布罗德卡回到酒店,已经晨曦微见,也睡不了多长时间。反正他兴奋得很,睡是睡不着的。他冲个热水澡,让热水浇头而下,似乎这样做就可以驱散头脑里的所有困惑。
几天前他还认为他能逃开厄运,然而最近发生的事情却让他看清,实际上自己无处可逃,他别无选择,只能是接受他的命数,最终去迎战那个他一无所知的敌人。
布罗德卡叫了早餐到房间吃,这一反他平日的习惯,出于什么理由他也无从解释。他索然无味地拿着刀叉在炒蛋上拨拉来拨拉去,喝了一杯咖啡之后,他把餐盘搁在门前廊道上——像所有酒店一样,用完餐的托盘都是脏兮兮的。
后来他给朱丽埃特打电话,时间太早,画廊里没人接听。布罗德卡穿好衣服,在外衣里面又套了件毛线衫,外面还很冷,倒是个好天。
和诺拉的艳遇一直在他脑袋里转悠。她的色诱竟然让他欲念横生,毫无理智而言,布罗德卡晃了晃头。这种事竟然叫他撞上了,一个自以为历练世事的男人,一个在他这样年龄的男人。太可笑了!我亲爱的布罗德卡,他对自己说,你难道人老心还未老吗?
电话铃响,是朱丽埃特,她在电话那端送上一个香吻。
“我正要找你呢。”布罗德卡说。
“我还在家里,”朱丽埃特说,“我丈夫外出开会。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回来?我很想你,你不想早点儿回来啊?”
“你是知道的,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布罗德卡不得不撒了谎,“天气太坏了,我没法在露天拍。我……嗯,还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完工。”
接下来无话,双方都明显感觉出这沉默中的不安和为难。
“你出什么事了吧?”朱丽埃特终于说道,“你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
“你怎么会这样想?”布罗德卡佯装惊讶地说。其实他很清楚,他的演技根本骗不过朱丽埃特。他没打算把昨天发生的事在电话里讲给她听,诺拉一事让他深感愧疚。“你丈夫开多长时间的会啊?”
他岔开话题。
“三天,”朱丽埃特说,“你就快点回来吧,在我找其他帅哥之前。”她呵呵地乐。
他们聊了些无关紧要的事。布罗德卡心里一直记挂着歌剧院咖啡馆的见面。除此之外,他留意自己不要把这两天的事情说漏嘴,一定得等等再说。他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
布罗德卡答应朱丽埃特明天回去,他听到门口有轻微响动,有人把一张纸条塞进门缝。
布罗德卡挂好电话捡起纸条,是酒店服务中心的便筏:诺拉·玛寇维茨女士8点25分来电,请您速去她家。
布罗德卡看了下钟点:八点过五分。这个电话是什么意思?他一边穿大衣一边约好出租车。
他站在酒店前的凯特隆纳大街上,炫目的阳光照下来,双眼眯成一条线。出租车司机沉默寡言,正和布罗德卡的意,他现在真没有闲聊的心情。
早晨这一时段维也纳的交通就像意大利的政坛一样混乱无章,看来好像只有大动干戈才能重整次序,街道上的车辆走走停停,司机们忙于摇下车窗,高声呵斥前后左右慢吞吞行走的路人。还好,当地人早已习以为常,不过是挨顿骂,这种恶言恶语外地人反正也听不懂。
白天要比晚上热闹许多,熙来攘往的人们流连在市场的摊位和货架前,令布罗德卡难以找到诺拉住的那幢楼。到底让他发现了那个通道,车钱付给司机之后他下了车,穿过临街房,进入后面的住宅楼。
楼里面并不比外头暖和多少,布罗德卡踩着吱嘎作响的楼梯上了二楼。他抬头撞见一个正扶着栏杆探头探脑的老妇人,她眯起眼睛打量布罗德卡,然后歪着脑袋默默走开。
诺拉似乎正在等他,房门留着一道缝。
布罗德卡敲敲门后径直走了进去。
诺拉斜靠在饭桌后面的沙发上,她还穿着昨晚那件让布罗德卡厌恶的紫花睡衣,头耷拉着,双臂软绵绵地垂下,两条腿劈得很开,男人用不着付钱就可以看到她的****。
布罗德卡还以为诺拉喝醉了,房间里弥漫着酒精的味道。等他更靠近一些,才发现她的脖子两侧有深红色的淤痕,两只眼球空洞无光,宛若玻璃珠子,嘴唇青紫,嘴巴张开,能放进一根手指。
布罗德卡从未见识过这种场面,惊得他寒毛倒竖,不知任何是好。他拉了拉诺拉的左手,冰凉冰凉的,等他把手松开,她的胳膊也滑了下去。直到这时布罗德卡才切切实实地意识到,诺拉死了。
同一时刻他也明确地意识到,诺拉是被人杀死的。
他卷进了一起谋杀案。
毫无疑问,有人设计陷害他!
一种无以复加的恐惧向他袭来,他分明听见两侧的太阳穴在突突直跳。布罗德卡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里!
听到楼道里有动静,他走到门旁屏息静听,那声音惭行惭远,他小心翼翼地把门推开,探出头,外面没人。
布罗德卡决定马上离开。他站在门口,楼道里空空荡荡,不知从哪问房里传出收音机的嘈杂声。布罗德卡深吸口气,把房门从身后带匕。
下楼梯的时候他故作镇定,百般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慌手慌脚。
在步出楼门之前,他向外张望,没有旁人,布罗德卡快步穿过院子来到街上。
此时外界的喧闹对他有如背景音乐一般。他步行回酒店,无视那些迎面过来的路人。他越走越急,诺拉的惨状始终在他眼前浮现。等他过了环形路快到歌剧院时,他几乎是在小跑了。
回到自己的客房,他快速收拾好行李,结完帐后叫了辆出租车直奔机场。一路上司机跟他都说了些什么,布罗德卡一概没听见。
他的脑海里闪过太多念头,他在绝望中苦苦思索,自己如何能脱离险境。
他猛然恍悟,逃跑是最糟糕的选择。
出租车在驶向机场的中途折回,布罗德卡要求司机开往警署。
出租车司机乜眼看了他一下,端了端肩膀说:“先生,随便您好了。”
联邦警察署位于维也纳的一区,是一幢庞大的有无数窗户的老式楼房。玻璃隔窗后面有位警员坐在众多分机和监控器前。布罗德卡向他报案,他似乎没多大兴趣的样子,把布罗德卡交代给突发事件处理部门,事件处理部门又让布罗德卡去凶杀案科,负责人是瓦勒纳警长。
瓦勒纳警长专心致志地听完布罗德卡的讲述,时不时地还撇撇嘴巴,流露出厌恶和嫌气的情绪。之后他叫来一位警官助理,此人得有一百公斤,步履缓慢,蓄着茂密的大髭须,说话简练直接:“好的,这就走。”他转向布罗德卡礼貌地说:“请跟我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