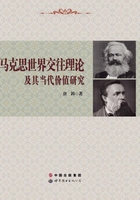我不能使信仰移动;也不能视若无睹,盲目地自投荒谬的深渊。
克尔凯郭尔
跟着约伯就会成为信仰之父亚伯拉罕及其可怕的牺牲品。《害怕与恐惧》的书名取自《圣经》,该书从头至尾阐述亚伯拉罕的思想。
评论约伯就已很难,我们还记得,克尔凯郭尔以极大的努力才敢于将约伯的眼泪和诅咒同黑格尔冷静清醒的思维对立起来。但对亚伯拉罕的要求则更高,比对约伯的要求要高得多。约伯所遭受的厄难是由外部旁力施予的,而亚伯拉罕则自己举刀对向他世上最亲爱的人。不仅人们,而且“伦理”都回避约伯,感到自己完全软弱无能。不知不觉地脱离了他。但人们不应回避亚伯拉罕,而应起来反对他,伦理不仅脱离了他,而且诅咒着他。在伦理的法庭上,亚伯拉罕是众皆唾弃的首恶:弑子犯。伦理不会帮助人,但我们知道,它有足够的手段折磨它所厌恶的人。亚伯拉罕同时又是最不幸的、罪孽最重的人:他失去了儿子、希望和晚年的依托,而且,像克尔凯郭尔一样,失去了荣誉和自豪。
这神秘的亚伯拉罕是何许人也?那本神秘的书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在这本书里,亚伯拉罕的案件不仅未罪有应得地遗臭万年,相反,却得到了吹捧并遗训后人。再引一次克尔凯郭尔的话:亚伯拉罕的行为已逾越伦理的界线,他的“目的”比伦理更高。为追求此目标,他“摆脱了伦理”。我们还记得,伦理掩护着能石化人的必然,如果人敢看它一眼的话。亚伯拉罕怎么敢于摆脱伦理呢?“当我想到亚伯拉罕时”,克尔凯郭尔写道,“我似乎变得渺小了。我时时刻刻看到他的一生充斥了极其荒唐的事情;时时刻刻都有什么东西使我厌恶它,我即使搜索枯肠,仍无法理喻他的荒唐。我寸步难进。我竭尽全力,但总感到力不从心。”他接着又说明:“我能够理解英雄,但却不能理解亚伯拉罕。只要我一想登上他的高度,我马上就会下跌,因为我看到的是荒唐。但我并不因此贬低信仰的意义,相反,信仰对于我是最高贵的,我认为,哲学用其他东西来取代信仰、嘲笑信仰是不正大光明的。
哲学不能也不该给人信仰,但它应知道自己的范围,它不应剥夺人的任何东西,更不能以胡言乱语使人失去自己的东西,尽管是不足挂齿的小东西。”这里,当然应停顿一下,提个问题:克尔凯郭尔何以断言信仰在哲学之外?能如此“轻易”地摆脱哲学的控制而成为“绝对的法官”吗?在这个法官面前,如黑格尔所说,也像所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宗教的内容应证明并解释自己”。从克尔凯郭尔有关亚伯拉罕的言论中已能部分地看到,克尔凯郭尔本人也知道面临的困难。他写道:“我面对恐惧,不害怕也不颤抖,但我知道,我如果有一点勇气反对恐惧,那我的勇气不是信仰的勇气,而是相比之下微不足道的东西。
我不能使信仰移动,也不能视若无睹,盲目地自投荒谬的深渊。”这样的话他不知说了多少遍:“是的,我不能移动。只要我一想这样做,周围的一切都会旋转起来”,或:“使信仰作最后的荒唐的移动于我是不可能的。我愿咽下顺从的苦果”。这些“不能”、“不可能”来自何方?谁或什么褫夺了克尔凯郭尔的意志,妨碍了他移动信仰并威严地把他投入顺从和无所作为的痛苦深渊?他对我们说,哲学,即理性哲学,无权用胡言乱语来剥夺人的信仰。但这里问题是在于权力吗?必然不也无权限制众神之父?虔诚的柏拉图和严肃的爱比克泰德也不得不开诚布公地承认万物之主宙斯尽管违心,仍顺从了必然并作了让步:他想还给人们身体及整个世界归人所有,但不得不又改为“借用”,并接受了随遇而安的劝告。不是吗?柏拉图,爱比克泰德及宙斯本人都不也不够勇敢,不能抗争必然,不也临阵脱逃,藏身于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顺从的痛苦深渊?如果我们向古希腊哲学家提这个问题,他们大概会愤怒地否定克尔凯郭尔的解释的。他们有足够的勇气,甚至更多的勇气,但问题不在于勇气,任何理智的人都知道,必然之所以是必然是因为它不可征服,顺从的痛苦是神在让凡人适应生存的环境后唯一能与人分享的生活乐趣。
克尔凯郭尔总是抬出柏拉图和爱比克泰德的导师苏格拉底,但苏格拉底有足够的勇气吗?克尔凯郭尔能假设苏格拉底站在约伯或亚伯拉罕的一边吗?苏格拉底一生嘲笑勇气,认为它不量力而行,莽撞冒险!
无疑,苏格拉底一定会尖刻讽刺咆哮如雷的约伯,而对盲目投入荒谬深渊的亚伯拉罕则更不留情。哲学无权剥夺人的信仰,无权嘲弄信仰!克尔凯郭尔的这个金科玉律又从何而来?莫非相反:哲学的基本任务不在于嘲笑信仰,使人重返真理的唯一源泉——理性?尤其是嘲笑克尔凯郭尔备加推崇的亚伯拉罕的信仰,在谈到约伯时事情就难办了:人除非丧失理智,愚昧无知,才能把自己的不幸,尽管十分巨大,归咎于世界。除非极其天真,像《约伯》一书佚名作者一样,才能相信上帝能归还约伯的牛羊、财富甚至死去的孩子。这一切显然是臆想,是童话,如果克尔凯郭尔依据自己通过书本了解到的约伯的生平宣称,从今往后哲学的起点不是回忆,如苏格拉底所说,而是重复,那么这只说明他的思维糟糕透顶,他不能像黑格尔要求的那样摆脱自己的主观愿望、深入事物本质,或者,他鄙视莱布尼茨的教诲,另寻真理,但又忘带了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它们对思想家十分重要,就像指南针、地图对于海员一样,克尔凯郭尔正是因此在刚出发寻找真理时迷失了方向。
再重复一遍,克尔凯郭尔对此十分清楚:如果他认为能如此轻易、简单地摆脱哲学,他就不会写两卷书《哲学的崩溃》,这本专门同思辨哲学分庭抗礼的书。信仰靠荒谬支撑,任何人对这个赤裸裸的论断都不会感到惊讶。如果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荒谬上,那么所有真理都将成为无稽之谈。对伦理亦是如此。只要想一下伦理是为何而被摆脱的。约伯摆脱它是为了收回自己的牛。苏格拉底会这样说,且苏格拉底的讽刺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克尔凯郭尔则是为了重获做丈夫的能力。应该认为,信仰之父亚伯拉罕也与约伯和《重复》的主人公大同小异……确实,亚伯拉罕敢于做令人惊异的事:杀死自己的独子,毁灭自己的希望和晚年的欣慰。当然,这样做需要巨大的力量。
无怪乎克尔凯郭尔对我们说亚伯拉罕摆脱了伦理,亚伯拉罕“有信仰”。他信仰什么?“甚至当匕首在他手中闪着寒光的那一瞬间,他都相信上帝不需要他的以撒。我们接着论述,假设他真的杀子燔祭,那他是有信仰的。他相信的不是在另一世界的某个地方寻求快乐。不,而是这里,在这个世界上。他仍将是幸福的。上帝会给他另一个以撒。上帝会让他的儿子死而复生。亚伯拉罕相信荒谬的力量:对它来说,人的计谋都不值一提”。为了不怀疑他理解亚伯拉罕的信仰及其行为的意义,他把自己的事业融合于圣经历史之中。当然,他不是直接地、公开地这样做的。我们已经知道,人们不公开地谈论这些事,而克尔凯郭尔更是如此,他就是为此而发明了间接表述的“理论”。其实。他偶然对我们这样说:“对别人来说,他的以撒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句话的意思和具体意义只能在听完他“编造”的一贫穷小伙子爱上皇帝女儿的故事后才能大致猜出。大家都十分清楚,小伙子不可能看到公主,就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一般的健全思维像人类最高级的智慧一样(在健全思维和智慧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别)劝告他对不可能的幻想和对可能的追求:酿酒师的富孀是他最合适的伴侣。但青年人像被什么螫了一下,失去了健全的思维和崇高的柏拉图突然像亚伯拉罕一样投入了荒谬的怀抱。理性拒绝给他皇帝的女儿,它认为她不应嫁给他,而应嫁给皇帝的儿子。小伙子摆脱了理性,想以荒谬碰碰运气。他知道,“日常生活中”隐藏着深刻的信念,皇帝的女儿是他永远不可企及的。“因为理性是正确的,在我们理性主宰的痛苦深渊中这过去是并仍将是不可能”。他还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神祗赋予人们的聪明建议的唯一出路是顺从必然。他甚至通过了这个顺从——在这个意义上;以人类灵魂所具有的明察对现实作了估计。克尔凯郭尔解释说,另一个人大概会放弃娶公主为妻的愿望。忍受这巨大的痛苦更富诱惑力。克尔凯郭尔称这样的人为顺从的骑士并侧以同情。但“娶公主为妻毕竟是美好的”,而“顺从的骑士,如果他否定这个,则是自欺欺人”。他的爱情也不是真正的爱情。克尔凯郭尔把顺从的骑士同信仰的骑士对立起来:“这个骑士自言自语说,通过信仰,依靠荒谬你将得到皇帝的女儿。”他还重复说:“娶皇帝女儿毕竟是美好的。信仰的骑士是唯一幸福的人:他统治了有限,而顺从的骑士在这里只是外来客。”但他立即又承认说:“但我是不能这样大胆地去做。当我想这样做时,我就头昏眼花,急于藏身于顺从的痛苦之中。我能游泳,但对这神秘的翱翔来说,我却太重了。”在他的日记里我们看到(而且不止一次):“如果我有信仰,丽琪娜就非我莫属了。”
为什么一个有着如此狂热、如此虔诚信仰的人却不能得到她?为什么他不能跟随亚伯拉罕和爱上皇帝女儿的小伙子?为什么他变得重了,不能翱翔?为什么他顺从了并拒绝最后一次铤而走险?
我们记得,在把多神教和基督教比较时,克尔凯郭尔曾说过,多神教不懂得罪是与人的意志顽固和僵化联系的。我们还记得,人们认为这个对立是不正确的:多神教一直视罪孽之源为恶意。但在克尔凯郭尔和信仰之间,恶意不是障碍。相反,人的所有意志——恶意和善意都极其狂热地寻觅信仰,但信仰却没有来,没有迈过顺从一步,实现顺从的理想。但在人的权力中,他内心中却找不到做这最后冒险的能力。“顺从使我意识自己的永恒;这是纯哲学的移动,我坚信,如果需要,我就会这样做,竭尽全力迫使自己服从精神的严格纪律……我将以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移动”。确实,克尔凯郭尔没有夸海口,他知道什么是精神的纪律,他毕竟受过苏格拉底学说的熏陶。如果事情只是自我牺牲或更恰当地说,是自我牺牲的功绩,那么克尔凯郭尔将是斗争的胜利者。但“意识自己永恒”是斯宾诺莎所说的“sentimus experimurque nos aetertlOS esse”(感情试验是永远的),这首先鼓舞了施莱尔马赫尔,但对克尔凯郭尔却效力甚微,因为这是“consolatio philosophiae”(安慰哲学)或思辨哲学,而这样的“安慰”无论对约伯,还是对亚伯拉罕都无济于事。克尔凯郭尔还解释说:“凭自己的努力我能拒绝一切。但我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获得属于有限世界的任何东西……凭自己的力量我能不娶皇帝的女儿并毫无怨言,愉快而平静地忍受心中的悲伤。但再娶皇帝的女儿吗?通过信仰,神奇的骑士对我们说,通过信仰,你能借助荒谬得到她。”现在可见,克尔凯郭尔意欲何为。苏格拉底是顺从的骑士,他留给人类的全部智慧是顺从的智慧(斯宾诺莎在永恒的观念下也步苏格拉底之后尘)。苏格拉底“知道”人凭自己的力量能拒绝皇帝的女儿,但要得到她是不可能的。他同样“知道”神的力量是有限的,不是他们主宰有限的世界,他们的权力中只有“永恒”,而且他们愿与凡人共享。因此,苏格拉底在那些满足于神祗有限惠赐并不愿再寻求快乐的人身上看到了摆脱有限、顽固不化、咎由自取并只配做“理性的仇敌”的罪人的平静,因为知性来自理性,推翻知性就是推翻理性——“a quam aram parabit sibi qui majes—tatem rationis laedit”(侮辱伟大理性的人为自己准备了什么样的祭坛)。侮辱他理性的人,像苏格拉底死后二千年斯宾诺莎说的,“socrates redlvlvus”(复活的苏格拉底)将在哪个祭坛上祈祷?
但约伯毕竟拒绝了“consolationes philosophiae”(安慰哲学)及人类智慧所有“虚假的安慰”,《圣经》的上帝不仅不视之为恶意,而且审判那些建议他用永恒的观念替代“有限”福禄的“安慰者”。亚伯拉罕在举起寒光闪闪的刀时甚至也未拒绝“有限”的以撒,于是他成了未来万代的信仰之父,克尔凯郭尔也找不到恰如其分的词语来宣扬他的敢作敢为。